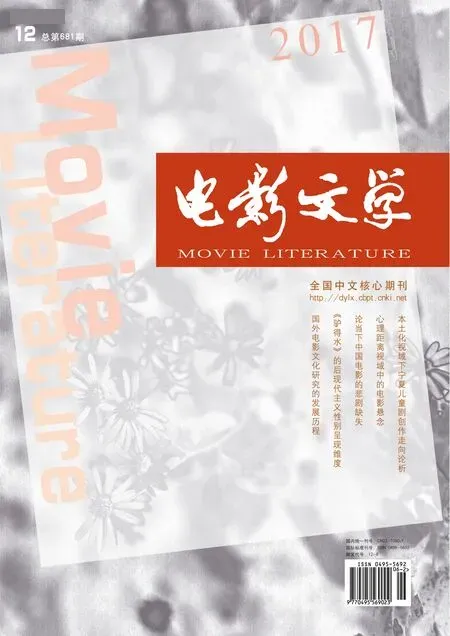淺談《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的敘事模式
支 瑾 (河北對外經貿職業學院,河北 秦皇島 066311)
一、個體視角對宏大敘事的消解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根據原著小說《漫長的中場休息》改編,以一個少年的視角,見證了世界最殘酷的游戲:伊拉克戰爭。以此為背景,電影涉及軍人群體、心理創傷,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反戰主題,也有不少觀眾認為導演李安是在探討英雄情結和美國夢,等等。如果結合導演風格,從更深層次的角度去分析,《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恰恰是對以上主題的顛覆與消解——從第一部電影《推手》開始,宏大敘事向來就不是李安所要渲染的:無論是代表東方精神的《臥虎藏龍》,還是隱藏在少年派內心中的“理查德·帕克”,抑或是每個男人內心中存在的那一座“斷臂山”,李安都在試圖挖掘人物的內心世界,探討每個存在的個體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在面對現實世界時,人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和各自的生存哲學。正因為強化個體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善于描寫人與社會的關系和對不同個體細膩情感的刻畫,在李安的電影中,強烈的主體意識和個體視角將宏大敘事消解,觀眾也能在觀影中體會到導演對片中人物的關懷,并體悟到李安作品所傳遞的普世哲學。
《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便是以比利·林恩的視角展開,采用倒敘的手法,透過一個19歲少年的眼睛看世界。林恩從代價慘重的伊拉克戰場中凱旋歸來,被奉為國家英雄,受邀參加超級碗感恩節大賽的中場表演。然而,導演在開篇交代的并非以戰爭為敘事背景,強化“英雄榮耀”,而是將焦點對準主人公參戰的原因:因為姐姐發生車禍被毀容,男友當即提出分手,林恩沖動之下砸了他的車。父親為他交了罰金 ,但條件是林恩必須參戰。一個家庭普通、荷爾蒙旺盛的年輕人,因為父命難違登上戰場,結果卻意外成為國家英雄,這本身就有點反諷意味。當中士在悍馬車里問他參戰原因時,他被迫說出實情。從他的回答來看,個體利益的原因的確存在——即使身為國家英雄,林恩和隊友們同樣會為每個人十萬美元的表演片酬所打動,這種內心世界與隨后賽場上的英雄榮耀形成極大反差,讓觀眾感到悲情和無奈。
隨后,導演將焦點對準林恩,通過他在準備中場表演時的幾次“分神”,回顧了戰場和家人。整場故事融合了家庭、隊友以及社會和國家輿論,在主人公的所思所想中,完成了對這一經歷中不同人物關系的反思。這其中涉及人物關系間的細膩刻畫,正是導演李安所擅長的主題。在回憶與現實的雙重敘事中,林恩表達了對軍隊生活的掙扎、對國家榮譽的認知和信仰的看法。當記者采訪林恩與敵人近距離搏斗時的感受,他回答道:“沒有感受,因為來不及想。”可見圍觀者都希望獲得戰爭的“正義意義”,而林恩卻認為,這感覺很荒誕,因為這輩子最糟糕的一天而得到表彰。在這一段對話和心理描寫中,導演用細膩的鏡頭語言將林恩的內心世界描繪得感染力十足,所謂星條旗所宣揚的“美國夢”以及“天命真女”高唱的英雄贊歌,在敏感的林恩面前被擊粉碎。
二、主觀敘事下的走神與不在場
事實上,在電影中作為背景的這場美式橄欖球賽真實存在。根據《漫長的中場休息》小說作者本·方登的回憶,這場比賽的中場演出無比瘋狂和荒誕:士兵們站在飄揚的星條旗下,賽場上由煙火、快餐音樂、色情舞蹈和閱兵儀式構成。正是在這超現實的愛國主義氛圍下,方登創作了這部小說。然而,這部小說并沒有太多關于伊拉克戰爭的正面描寫,只有林恩的回憶與當時和戰友間的零碎對話。
然而在這部電影中,導演增加了更多關于戰爭場景的正面描寫,這些描寫通過林恩在賽場上的頻繁“走神”體現出來。伊戰成為一條隱形線索,構成故事張力,推動著劇情發展。林恩的回憶從頭到尾穿插在影片中,并被具象化。導演將真實的戰爭場景與現實的美國日常生活平行剪輯,讓主人公在雙線敘事中來回切換。戰爭場面著力不多,但是激烈而緊張,也是該片技術實驗的重點(超高幀率、4K加持、3D攝影等),與主體場景的賽場表演形成鮮明反差。林恩在回憶與現實中的掙扎和壓抑的情感不斷被放大。
“走神”看似是主人公的一種心理狀態,實質是導演精心安排的一種敘事策略:主觀地讓時間和空間錯位,不斷地變換敘述主體,由某個很小的事件觸動主人公的思緒,從而轉向對潛在事件的敘述。此時觀眾會跟隨主人公的視角,在不自覺中形成時空漫游效應。 賽場上的林恩是一個客觀敘事主體,參與正在進行的現實生活;同時他又帶著濃厚的主觀敘事色彩,回憶著戰場上的痛苦與創傷。所以,在這部電影中,我們能多次看到林恩“看鏡頭”的動作,林恩在車廂里、在體育場看臺上、在賽前發布會上,屢次脫離現場看向鏡頭,這一動作構成了該片最顯著的鏡頭語言。
當林恩面對鏡頭時,他看到的不僅是自己的過去,也是另一個演員。觀眾此時會發現,自己已經被卷入導演的敘事中。這種“看鏡頭”的特寫鏡頭,實際上是一種“共情”企圖,觀眾無法拒絕,因為林恩的眼神過于誠摯和逼人。林恩的眼神只是一個橋梁,導演借助于此與觀眾進行互動:他在邀請觀眾暫時離開賽場,每個人都成為主人公比利·林恩,用他的視聽感官,去感受賽場/戰場上發生的一切。此時,觀眾和林恩是融為一體的,而這正是觀眾在場/不在場的一種游離狀態。
但這種代入感又不同于其他電影,因為主人公的特殊角色。林恩并無異于常人的特點,但電影中多次采用“走神”這一狀態,正是在強調這一人物的心理創傷。這一點我們是通過林恩姐姐預約的醫生留言得知的: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具體癥狀表現為:通過回憶和夢境,患者的思維會不自覺地浮現與創傷有關的場景,注意力不集中、高度警覺和情緒焦慮。在和隊友參加中場表演時,林恩全程頭疼,他不斷地向經紀人索要止疼藥。戰爭場景重復閃回,讓他感到眩暈。在這種極端敏感的心理狀態下,導演試圖將觀眾代入林恩的個人故事中,同時,林恩現實與幻覺中的視聽感受也被放大。它在這部作品中投射在多位隊友身上,并反復出現介入敘事,并成為敘事關節。
三、英雄見解與信仰議題
憑借在伊拉克戰場上的短暫勝利,林恩所在的B班一夜成名,成為美國英雄。在去參加超級碗中場表演的過程中,林恩遇到來自不同階層的人物,這包括他的家人、戰友、好萊塢制片人、球隊幕后老板、一見鐘情的拉拉隊員菲姍、場地工作人員、超級明星、虛偽的資本家,他們對這個國家和戰爭英雄有著不同的見解。雖然賽場和戰場是影片的主要場景,但因為這些人物關系的出現,導演用反諷的手法描繪出當代美國社會的眾生相。賽場上的美國強大、富有而充滿正義能量,人們在談論這些英雄時,滿帶敬意,也不時流露出國家自豪感,星條旗下的林恩熱淚盈眶,感染了在場無數觀眾。然而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此時他腦海里浮現的是和剛邂逅的女拉拉隊員激情親熱的場景。
在影片中,跟隨林恩的神游和戰友們在賽場上不同人物的對話,我們看到的卻是另一個美國,一個由戰爭夢魘構成的國度,他們闖入伊拉克普通民宅,與“恐怖分子”展開驚心動魄的戰斗,成為當地人的仇恨對象。當他們在吃自助餐時,一位富可敵國的能源商人告訴他們:“如果技術進一步提升,國家能源自給自足的話,你們就不用再去搶奪伊拉克的石油了。”中士當即反駁了他,為了讓商人難堪,回擊道:“我們享受戰爭,因為能夠殺人。你做你的能源,我殺我的人。”當商人識趣離開后,他又問林恩自己是不是一個混蛋。很顯然,能源商人代表這個國家的高級階層和精英意識,他們對戰爭的定義是資源掠奪,士兵被國家所利用。而中士的這番言論體現了軍人對于戰爭的看法。雖然這些軍人并非殺人機器,中士的措辭有點夸張,但顯然,他是一個心靈和精神都被戰爭異化的人物,同樣帶著戰后創傷的癥候。
在國家這種宏觀語境面前,林恩和他的隊友們雖然成為“英雄”符號,但英雄也只是一個泛指,民眾能接受這一泛指,但對個體英雄的所指意義不明。賽場上的觀眾熱情地與他們握手、索要簽名,對他們表達感恩及崇拜。但同時我們也看到,當林恩登上舞臺與超級明星同臺表演時,伴舞的黑人演員對他說了一句“Fuck you,大傻兵”,表演結束后立刻遭到工作人員的驅趕。林恩此時深深地感受到身邊人對他們的惡意——場前他們被宣傳為國家的榮耀,堅強且具有膽識,德行高尚,而場后卻受到種種非禮待遇。在B班與球場保安人員發生暴力沖突時,保安高喊:“我們的軍隊竟然是這樣的!”美國軍人的形象,只是國家輿論和政府、娛樂業聯手打造的美國夢,想把B班故事拍成電影的片方投資商,看到的是投資商機和票房回報。導演通過影像傳遞出一個殘酷的事實:沒人真正關心這些遭受戰爭創傷的軍人群體,大眾只是在消費他們的戰友情誼,盲目地意淫英雄主義和國家榮耀,甚至連林恩和戰友們的這次表演,都是為了滿足民眾的獵奇心和窺私欲望。
當林恩和菲姍再次相遇親吻時,
林恩:嘿,你知道嗎,我差點就帶你走了,我很想帶著你逃跑。
菲姍:你要去哪兒呢?你不是美國英雄嗎?
簡短的對話中,觀眾意識到,她愛的并不是作為個體英雄的林恩,而是代表“美國英雄”、帶有榮譽光環的比利·林恩們。
影片中的細節多次提到,林恩本身并不是一個戰爭支持者。相對于他略帶粗野的隊友,林恩的內心還是一個敏感的少年,天性善良而單純并充滿悲憫之情。他的腦海里反復浮現的是姐姐遭遇車禍后的瑕疵面容、執行任務時伊拉克孩子流淚的眼睛、敵人臨死前的頑強掙扎與堅毅眼神……然而他最終選擇了重回戰場,成為一名軍人。從主人公的性格塑造和全片敘事的情感需求來看,這一設計是導演有意為之,有一處鏡頭體現了林恩群體的困境:賽場休息間隙,一位黑人酒保帶著林恩和戰友Mango去VIP室抽大麻,酒保在告訴他們VIP區域位置昂貴的同時,也抱怨自己薪酬太低,生活很糟糕,為了養家糊口,能領到6000美元的入伍獎金和家庭保險,他也想去當兵。這也引發了林恩的思考,如果自己退伍回來,能做什么?快餐廳的服務生?林恩感到進退兩難,褪下英雄的光環,他同樣要面對殘酷的日常。這是一個年輕人的無奈與掙扎,他迷茫的實質是,究竟該如何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在電影的最后,林恩和戰友們回到悍馬車里,在經歷了一場幻象的破滅后,英雄們重返戰場。
值得一提的是,導演在敘述展開眾多人物關系的同時,影片中還隱藏著一條暗線,那便是已故長官“蘑菇”引領林恩心靈成長的線索。在林恩眼中,“蘑菇”是真正的英雄,并且是一個神秘角色。他信奉印度教教義,充滿智慧。片中有一幕他與林恩在綠色參天大樹下聊天的鏡頭,平和而雋永,與戰場上的殺掠場面形成鮮明反差,充滿了哲學寓意。“蘑菇”也對林恩表達了自己的人生哲學:無論是生在故土,還是客死他鄉,人的生命是命中注定,而意義在于你的認定,明確自己身在何處。不在于命運選擇,在經歷破滅之后認清自己的屬性和歸宿,坦然面對生活。“蘑菇”的生存觀多少也投射出導演李安的電影哲學,這是他對于生命的尊重,彰顯出對林恩這一人物形象的主觀關懷。如果說4年前的“少年派”講述的是一個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對自我意識的認知和內心世界的喚醒,那么《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則將少年成長的焦點對準外部世界,表達了一個年輕人觀察世界并試圖找到自己在這個世界的一席之地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