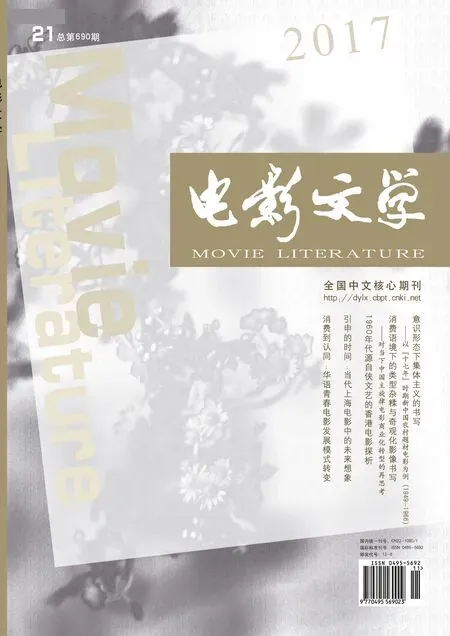由類型電影看當代美國審美文化取向
徐 梅(鄭州工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當代社會朝著多元化與現代化的方向高速發展著,而電影這一門現代藝術,便是這種發展下的產物與社會的一面鏡子。誕生于活動照相術與幻燈片放映術的電影藝術能夠以一種高密度的方式,對人們身邊的社會百態進行記錄,這也是電影越來越受到人們關注的原因。在電影之中,人們在獲得娛樂的同時,也得到了時代的縮影。而電影產業的發展,則促進了類型電影的產生。目前來說,擁有好萊塢的美國電影是類型電影的代表者。在美國的類型電影中,可以窺見美國觀眾的審美文化取向,它們的出現、變動乃至消亡,往往都體現在類型電影的出現、盛行和衰落中。這一點在電影井噴式發展的當代體現得尤為明顯。可以說,類型電影為電影藝術與電影產業注入了活力,也是人們把握特定時代或地域內人們審美文化取向的標本。
一、陌生化審美
觀眾的審美取向是始終處于一個變與不變的穩態中的,而對于商業片導演來說,最重要的便是巧妙地把握住變與不變間的平衡,顧及新的、前衛的口味與老的、廣泛的習慣,最終取得收益。而在這個穩態之中,有一個可謂“老調”的審美取向便是陌生化審美。陌生化審美文化可以說是自電影誕生后就一直存在于電影藝術中的,它體現著藝術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特質,也是電影藝術吸引受眾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人們的內心深處,有著對陌生事物的本能好奇。而對于觀影這一行為的認知,又使得觀眾在近距離體驗危險、刺激的場景時又確定自己是絕對安全的,因此觀眾可以放心地對脫離現實生活的事物進行窺探和賞玩。因此,制造陌生景象撞擊觀眾的心靈,就成為電影中一種普遍的創作思路。尤其是以造夢工廠自詡的好萊塢更是如此,用種種迥異于觀眾日常體驗的幻覺來給觀眾炮制一場美夢,讓觀眾進入幽暗的電影院中獲取一段時間內的新奇體驗,拋棄現實的煩惱,脫離現實的羈絆。
到了當代,隨著外部世界科技的突破以及電影內部技術的革新,這種陌生化審美被放大了,尤其是在商業化意味濃郁的好萊塢,陌生化審美幾乎成為“好萊塢大片”的標準配置。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類型片便是科幻電影。如表現星際旅程、拯救人類的《星際穿越》(Interstellar,2014),表現宇航員獨自一人從深邃浩瀚的外太空返回地球的《地心引力》(Gravity,2013)等,觀眾在觀影時仿佛置身于一個遙遠的空間。
但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科幻電影,在長期的發展之后,其表現的內容就具有重復性,已經不再是觀眾眼中的新異事物,尤其是在大量科學知識經由不同的媒介得到普及之后,科幻電影曾經的太空探索、大戰外星人等就已經不再如當年一樣吸引人們的注意了。因此,奇幻電影成為近年來逐漸興起,甚至對科幻電影有壓倒性勢頭的類型片。由于其相較于科幻電影來說有著更為廣闊的發揮空間,它也將陌生化審美發揮到了極致。如根據托爾金小說改編而成的《指環王》(TheLordoftheRings)三部曲、《饑餓游戲》(TheHungerGame)三部曲等。這兩部電影的背景都是一個架空的世界,其中人物的職業、種族等都是與現實社會有所區別的,觀眾能在其中看到令人眼花繚亂的場景和打斗場面。
除此之外,災難片也是陌生化審美的體現。如《泰坦尼克號》(Titanic,1997)、《后天》(TheDayAfterTomorrow,2004)等。在《泰坦尼克號》中,現代科技完美地還原了巨輪撞向冰山導致沉船,上千人在冰冷的海洋中喪命的慘狀,這是觀眾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可能感受到的。當設計師安德魯宣布巨輪很快就將徹底沉沒時,觀眾的心也與乘客一樣緊張。
二、多元性審美
從社會文化背景來看,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有“文化的熔爐”之稱,自詡在文化政策上采取較為包容、寬松的態度,WASP(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新教徒)之外的少數族裔、文化群體和社會階層的文化話語權以及政治主張往往得到人們的重視和宣揚,以實現最終的文化平等。而從電影藝術本身來說,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類型電影進入改革階段,這主要是與當時公眾在道德標準和價值觀上的變動息息相關的。當時美國因為肯尼迪與馬丁·路德·金的遇刺越南戰爭和“水門事件”等丑聞而遭遇了一場全國范圍內的在政治、社會乃至道德上的危機,而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變化,也最終形成了一種審美文化傾向,因為主流意識形態附著于觀眾已經熟知的電影類型上,而當這種意識形態的群眾基礎動搖時,人們也自然不再被所謂的經典電影所吸引。取而代之的審美傾向則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反類型”,即一種混雜式的、跨界式的、多元式的審美,顛覆舊有的類型片的“配方”,打破傳統類型片的程式,但并不完全否認傳統,而是選擇各類型片中的元素重新整合。這種審美文化一直延續至今。
以在黑幫片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教父》(TheGodfather,1972)為例,電影借用了黑幫片的外衣,但是表現的是劇情片和政治片的內核。早年的黑幫片有著直接而單純的對觀眾獵奇傾向的滿足,這主要體現在,道德主題較為單一,人物形象較為臉譜化,而敘事的重點則在犯罪行動上,早年黑幫片一般都體現的是黑幫與警方之間的斗智斗勇,黑幫的暴力血腥犯罪等。而自20世紀60年代之后,這種簡單模式已經無法撫慰觀眾混亂的心態。可以看到,在《教父》中,敘事線索并不是單一的,電影表現了一個龐大的西西里黑手黨家族,各人有各自的利益,有其現在的動作和對過去的追憶,而對這一批人,尤其是老教父柯里昂,電影并沒有對其進行簡單的道德評價,而是呈現給觀眾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他們既有黑幫身份這一體現陌生化審美的特征,如電影中有各種引發觀眾腎上腺素激增的如刺殺、毒品交易等情節,又有著能與觀眾產生共鳴的在家庭親情、社會宗教等問題上的煩惱,如即使是與黑幫毫無關聯的觀眾,也能理解教父的喪子之痛。
又如《芝加哥》(Chicago,2002)和《了不起的蓋茨比》(TheGreatGatsby,2013)等,則可以視作是歌舞片、犯罪片和劇情片的混合。或者可以說,歌舞只是電影的表現形式之一,它們被巧妙地編織在敘事中,如維爾瑪的夜總會女郎身份、蓋茨比家舉辦的舞會等,而犯罪只是一條線索,通過這條線索電影揭露的是人性與社會的種種不堪。兩部電影都以濃墨重彩的方式表現了城市中的歌舞升平、燈紅酒綠,但是與傳統歌舞片不同,這兩部電影的敘事氛圍都是極為壓抑的。維爾瑪和洛克茜都殺死了自己的丈夫或男友,然而她們的經歷被律師比利加以包裝,被媒體大肆渲染,事情的真相已經變味;而蓋茨比為黛西和湯姆頂罪,自己最終卻落得個被槍殺、家破人亡的下場。美國社會的虛情假意在電影中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三、個性化審美
崇尚個性的自由是美國的國民性格之一。個人英雄主義也是美國類型電影中長盛不衰的主題,如早年的戰爭電影中就充斥著無處不在的個人英雄主義情結。也正是在好萊塢類型電影的廣泛傳播下,這種對于個性的尊重正為全世界的人所接受和認同。而反映在審美上,則體現為一種個性化的審美文化,即作為審美對象之一的主人公是與眾不同的,即使他原本極為平凡,但是他一定會在電影中迸發出他超凡的一面。而在這種審美中,“我”與電影中的別人不同(但實際上與基數很大的觀眾有相當大的重合)的一面被放大,使觀眾感到故事既親切又真實可信。
這方面的正面例子當屬近年來興起的漫改電影,催生了一系列銀幕上超級英雄的漫改電影中的美國民族救星,如蜘蛛俠、蝙蝠俠、綠巨人、鋼鐵俠、金剛狼等基本上都有平凡人的一面,他們因為種種機遇,或利用高科技,或產生身體變異,獲得了超能力,從此除暴安良,叱咤風云。并且超級英雄之間也會因為誤會而起爭斗,如《蝙蝠俠大戰超人:正義黎明》(BatmanvSuperman:DawnofJustice,2016)等,可見超級英雄們盡管都擁有正義感,但他們并不是“高大全”的,他們有自己的個性,有各自的苦衷和對世界和平的不同理解。而反面例子則要屬曾經輝煌一時的類型片西部電影。西部電影的沒落除了因為西部地區已經失去了陌生化意義以外,還與它的極簡美學有關。在西部片中,警匪雙方的形象塑造都較為單一,觀眾對神秘的西部孤膽英雄已經失去了興趣。而較為成功的西部片如《被解救的姜戈》(DjangoUnchained,2012)則恰恰是一部“非典型”的西部片,而更應該視其為一部充斥了昆汀狡黠腔調的個性化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對個性化審美的把握也可以促進冷門類型片的復興。早年好萊塢的歌舞電影一度是極為受歡迎的類型電影之一,尤其是在百老匯音樂劇奠定的受眾基礎上,美國產生過《音樂之聲》(TheSoundofMusic,1965)、《雨中曲》(Singin'intheRain,1952)等經典之作。歌舞電影的類型主要在于,第一,擁有多元化的音樂元素;第二,擁有豐富的舞蹈元素;第三,音樂與舞蹈都是為敘事服務的,良好的故事底本是一部歌舞片成功的關鍵。在20世紀60年代,歌舞片達到了輝煌的頂點。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戰爭、科幻等類型片大量地分流了歌舞片的觀眾。然而攬獲多項奧斯卡獎的《愛樂之城》(LaLaLand,2016)則宣告了歌舞片的強勢回歸。就音樂而言,表現爵士樂的《愛樂之城》是傳統的,甚至可以說有致敬好萊塢歌舞片黃金時代的用意,電影成功的關鍵便在于緊扣了個性化審美這一點,通過表現在洛杉磯打拼的一對男女的悲歡離合,觸動了大批曾經陷入愛情與事業兩難抉擇的觀眾的情感。電影重復了《雨中曲》中女主人公自我奮斗的故事,但是安排男女主人公終于因為各自追求事業而分道揚鑣,突破好萊塢“男女主人公終成眷屬”的敘事窠臼,讓主人公在“實現人生夢想”(一個成為名演員,一個開了自己的爵士酒吧)的同時,又都錯過了自己的終身摯愛,愛樂之城成為兩人緣起緣滅之地。女主人公米婭之前屢次試鏡失敗,男主人公塞巴斯汀被酒吧開除,被迫搞自己不喜歡的音樂謀生等,這些都是能激起觀眾的情感投射的。而決不讓自己成為他人的附屬,寧可犧牲愛情也要實現自己的價值,就是電影傳遞出來的最強烈的個性審美。
從目前來看,無論是就電影制作的產業化、藝術性,抑或是電影與受眾之間的互動來看,美國類型片可以說是獨步世界的。大量類型電影的拍攝,是在深刻了解受眾的心理需要的基礎上,根據人在感知上的心理機制進行的創作。而在電影成功上映之后,又影響著觀眾的下一次審美期待,引發和感召著新的審美主體。可以說,美國當代的類型電影在形成一個個資金上的循環鏈的同時,也形成了一套套循環的觀影審美心理系統,反映著美國人在陌生化、多元性以及個性化等方面的審美文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