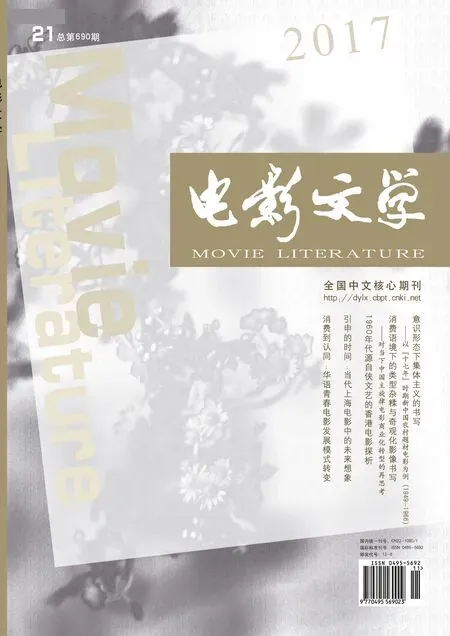《春夏秋冬又一春》的生命輪回敘事邏輯
顏小學(吉林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韓國電影以其獨特的人文觀察視角、異于他者的敘事手法、刁鉆取巧的敘事題材獨立于世界電影之林,洪尚秀、樸贊郁、李滄東等電影怪才不斷刷新世界對韓國電影的期待,在這些知名導演的電影中,觀眾可以看到一個或失序、或詭譎、或思辨、或蠻荒的人類世界。韓國影片的影片情緒、主旨和表現手法往往是相互聯動、相互作用的。金基德也不例外,只是在敘事的角度上,金基德的電影更加內傾,也更加溫柔緩和。《空房間》《悲夢》《呼吸》《圣殤》等影片都不外乎如此,金基德嘗試在統一的現實敘事立場之外,通過人與人之間的情緒交流,從而構造一個非現實的世界。《春夏秋冬又一春》則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一、借助東方禪意營造的脫離語言的敘事立場
《春夏秋冬又一春》的背景設置相當簡單,以一組長鏡頭開場。追隨著鏡頭,觀眾可以看到一座建立在湖心的小型佛教寺院。寺院內是作為主角的老和尚與小和尚。從影片開始,導演似乎就刻意地用做減法的方式讓影片元素簡單化。湖包圍著寺院,將寺院與四周的自然環境隔離,而在湖邊緣虛設的一扇門則是影片環境與世俗世界的簡單隔離。觀眾的視野也從這一虛設的門中進入,佛教的護法神韋陀菩薩嗔目怒斥的畫像被貼在門上,從一定意義上幾乎符號化地完成了觀眾對影片期待視野的預設。
影片結構從情節上看相當簡單。春天,七八歲的小和尚追隨老和尚去采藥,結果采回了一筐毒草。第二次離開寺院,小和尚殘忍地將小石頭用線拴在了魚、青蛙、蛇的身上,結果第二天被老和尚懲戒,老和尚在小和尚身上同樣綁上石頭,并且讓小和尚給他虐待過的動物松綁。魚和蛇都死了,青蛙活了下來,小和尚看著死掉的魚和蛇,哇哇大哭。
夏天,寺廟里迎來了一位女施主,女孩因為精神抑郁來寺院修養。這時十七八歲的小和尚對女孩暗生情愫,老和尚雖然屢次提醒小和尚,最終小和尚還是和女孩私奔了。
秋天,已經成為青年的小和尚,又一次回到了寺院,因為妻子出軌,小和尚最終殺死了妻子,想要進入寺院躲藏。最終被警察帶走,老和尚圓寂。
冬天,服刑出獄的小和尚已經人到中年,他又一次回到寺院,開始苦行修煉,可在一天晚上,一個婦女將孩子丟棄在寺院前,婦人匆忙逃走,掉進了湖上的冰窟窿里溺亡。
從劇情上看整個故事也就到此戛然而止。和金基德的傳統敘事邏輯相同,《春夏秋冬又一春》對語言的使用并不多,在導演自傳性質的影片《阿里郎》中,金基德認為語言并不能夠從事實本質上產生任何作用,人與人的交流更多地依靠行為而非語言。然而《春夏秋冬又一春》中對語言的使用又并不如同《空房間》中的絕對禁忌,整部電影沒有一句對白。《春夏秋冬又一春》的表達形態是東方式的,是脫離于世界表象之外的。在這種基礎之上,《春夏秋冬又一春》的靜默和非語言則更像是禪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從細節上看,這是一種東方審美特有的格調和氣質。因此對整部電影的分析部分也應該建立于東方佛教的文化根源上,進行跨文化的對比與解讀。
影片中首先出現的是幾組明顯的對比。小和尚和師父采藥,是作為影片的第一個情節出現的。兩人乘坐一艘畫著蓮花和菩薩的小船,跨過寺門,來到山外,一定程度上也離開了被提純的環境。小和尚采的一筐毒草和老和尚的草藥外觀相似,卻功能相反,也暗示著小和尚被“色”所迷惑的可能。果然,在隨后的情節中,小和尚又一次被寺外的世界所誘惑,偷偷地在山上虐待動物,認為動物掙扎的樣子有趣。乃至于小和尚和女孩的私奔都可以看成是他對表象世界的沉醉和迷戀。這種“色”“空”之間的對照在后文中更加明顯。老和尚告誡小和尚,愛戀中生出嫉妒,嫉妒則來帶死亡,果然最終應驗。小和尚跪在老和尚面前乞求寬恕,卻被老和尚在眼耳口鼻處貼上了紙條,以求“閉”和“空”。小和尚想要以閉氣的方式自殺,卻被老和尚狠狠教訓,與老和尚圓寂時自己給自己貼的紙條形成了對比。小和尚的閉氣只是一種情緒化的自我報復。“殺別人總是簡單的,自己殺自己卻并不容易。”這種自殺的方式只是另外一種方式的逃避。山寺、湖、高山、石雕的斑駁的菩薩像和金基德依靠鏡頭語言敘事的手法結合,形成了一個依靠影像構筑的東方式謎團,而這種內傾的情緒表達和符號運用也造就了整部影片的東方情緒。
二、隱喻——鏡頭之外導演個人情緒的表達與傳遞
雖然在《春夏秋冬又一春》中語言持續缺位,但是影片的文本內涵卻從來沒有失去效力。在影片中,大量的景物和道具成為敘事符號,伴隨著主線敘事,完成了影片的內涵表達。以影片中反復出現的蛇為例。在西方傳統中,蛇是罪惡的象征,意味著一種罪惡的引誘,是一種具象化的欲望反射。在小和尚上山采藥時,老和尚囑咐小和尚:“要小心,當心有蛇。”在其后,小和尚采藥的時候發現了蛇,然后輕松地將蛇抓住,掄了幾掄胳膊,將蛇扔到遠處。在鏡頭中,觀眾可以看到,對小和尚來說,蛇并不可怕,甚至蛇是可以玩弄的動物,第二次上山,小和尚抓蛇時毫無恐懼,并且在蛇的身上綁上了一塊石頭,最終蛇也因為被綁上石頭死亡。蛇在春天一節的時候是一個警醒卻沒有實際作用的符號。然而到了夏天,蛇的隱喻性也開始出現。小和尚去山外接女孩到寺廟前,看見山寺前有蛇在交媾,蛇成為淫欲的表現符號,暗示了人物的內心變化。在隨后的情節中,小和尚和少女的情愫萌動,老和尚發現寺中出現的蛇的痕跡,則暗示了兩人感情的發展逐漸明朗化,也從本意上提示觀眾,小和尚和少女結合的根源只是浮于表面的欲望影響。在冬天一節中,有蒙著面的婦人將嬰兒拋棄在寺院前,此時已經到了中年的小和尚,傾斜身體,想要看一看外面婦人的樣子。這時候出現了一段剪輯蒙太奇,一條盤起冬眠的蛇,突然游動。這也暗示了小和尚欲望的突然蘇生,然而這種基于好奇和情欲的行為,卻導致婦人倉皇而逃,最終喪命。
除卻蛇之外,連接寺院和山的小船也是一個十足明顯的隱喻。在影片中,幾乎每次有人渡船都會給船專門的特寫鏡頭。在影片開始處,觀眾可以看到,船上畫著蓮花、祥云以及觀世音菩薩。船既可以渡人,也可以自渡,而菩薩、蓮花等經典的佛教形象則暗示著道德意味和宗教意味的評判衡量。在第一次渡船時,是老和尚帶著年幼的小和尚,一路上,老和尚劃船、幫小和尚撥開樹枝等行為,是一種客觀的照拂和庇佑。而第二次小和尚劃船則是獨自出逃,去山上玩耍、戲弄動物,鏡頭對準的是小和尚逆水行舟的吃力表情;第三次小和尚劃船時,則背負著石塊,要去山上給昨天戲弄的動物放生,這時,鏡頭又給船上的菩薩、蓮花圖案以大特寫,暗示著小和尚行為的道德復歸。在秋季一節,船所包含的救贖意味更加明顯。殺妻逃逸的青年站在寺門口,老和尚看見小和尚之后,劃著船將青年從寺門口渡往寺內,這種救渡的意味直截了。青年懺悔后,被老和尚要求刻寫《心經》,《心經》中“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娑婆訶”的咒語,直譯即為“度度!度彼岸!彼岸竟度!成正覺!一切成就”。而青年也在刻寫完《心經》之后,最終伏法,跟隨追蹤前來的警察歸案。在警察與青年一起渡河時,老和尚以念力留住船,警察劃船卻不動,也暗示著苦海泛舟往來不斷。而最終老和尚選擇在蓮舟坐化,一條蛇從船上游向水中,仿佛也在提醒觀眾欲望的生滅,從未停息。
除此之外,夏天寺院蓄養的暗示著欲望的公雞,秋天寺院中象征著“我執”與“傲慢”的貓,意味著“蒙昧”和“癡愚”的金魚等符號意象也都建設于電影的佛教文化背景敘事系統本身。利用繁復的暗示手段,取代影片本身直抒胸臆的表達,是金基德影片的第二大特色,從這一角度來說,金基德的個人敘事策略表達往往展示出一種傳統東方的邏輯,在金基德影片充滿符號化的暗示之中,其影片敘事的幽深意味只能通過觀看者的審美背景和過往的審美經驗加以完成,從而也形成了影片和觀眾的被動互動。
三、互文式結構——借助于四季和生命循環的敘事邏輯
在《春夏秋冬又一春》的主題敘事中,往復回環,場景、情節重復出現的特征也十分顯著,這種表現手法同樣可以看成是導演的個人作品風格,也可以看成是完成敘事邏輯的必要手段。在《莫比烏斯》和《圣殤》中,可以看到金基德在同一主題不同敘事復調的重復與調度,從而構成整體敘事的邏輯倫理,但在《春夏秋冬又一春》中,這種作者電影的傾向還不明顯,此時,這種循環的復調展示的表達是基于審美傾向和宿命觀點的,也正是這種巧合,構成了《春夏秋冬又一春》獨特的互文式結構。
《春夏秋冬又一春》的故事發生在春天,小和尚的身世不明,老和尚的修行背景也沒有交代,故事的年代背景也被隱去。在群山環繞的環境中,山寺的平靜被外界所打破,換言之,影片的敘事圓融和戲劇情節都是通過外來因素構成的,僅僅是老和尚與小和尚的寺院生活并不構成敘事主題。春天,小和尚通過戲弄動物受到懲罰,從而實現“戒嗔”的目的,然而這種戒的實現手段也只能在山寺這種提純環境中完成。夏天,小和尚非但沒能“戒色”,反而被塵世吸引,追隨女孩而去。秋天,小和尚因愛生妒,嗔心復萌,進而殺死出軌妻子,鑄成大錯。冬天,白雪覆蓋山寺,服刑完畢的小和尚歸來,獨自開始修煉,在一個冬夜,又一個嬰兒被拋棄。小和尚的身份完成轉變,下一個輪回又將開始。
這種故事的循環邏輯既是佛教輪回觀念的一種簡化,同樣也是東方四季變化的一種認知手段。春天生發、夏天熾烈、秋天肅殺、冬天收藏,這種情節轉化進一步加深了影片所具備的潛在敘事背景,并且通過輪回式的重復,觀眾的疑惑也逐漸得到解答。在影片開始,小和尚和老和尚的來歷、身份,都通過一個輪回后的劇情得到闡釋。老和尚原來也可能是一個逃犯,而小和尚原本的身份則同樣可能是一個棄嬰。老和尚體驗過人生四季,想要從各方面幫助小和尚盡量無痛、無原則錯誤地完成生命歷程的轉變,其結果只能是徒勞的。又一春時,棄嬰已經長成了小和尚,而當初的小和尚又變成了老和尚,一段剪輯蒙太奇既無奈地說明了小和尚的未來命運,又將人生之煩展現給每一個觀眾。中景鏡頭中,老和尚在教小和尚讀書、學習,而下一個鏡頭中,小和尚則同第一個春天的主角一樣虐待動物,他將小石子強行塞進魚的嘴巴里。這種人類原始殺戮的展示也反映了影片終極的哲學性敘事命題,人生的輪回體驗是無價值的,同樣也是虛無的。對外界生命變化的冷靜與淡然處之,也正符合北傳佛教的部分思想,只是這種展示更加具象化——凡有所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輪回往復的敘事結構同樣也賦予了影片一種宏大的敘事主題,讓影片具有更多的余韻和更多的內容解讀。在過往《春夏秋冬又一春》的研究中,這一點也被反復提及,有研究者認為,《春夏秋冬又一春》中被群山包裹的山寺象征著人的本心,而山寺中的動物則象征著欲望的生發。影片似乎也暗合著這一理論,通過觀察可以看到影片中從未對出現的動物做出過任何解釋。寺院即人心,欲望的發生、熾盛再到爆發、消滅,看似是一條涅槃之路,然而欲望在蟄伏一冬之后,依舊會蘇生。正是因為影片的大量留白,也留下了后人對影片的諸多解讀。金基德獨特的互文式的敘事結構也從該片開始逐漸形成其傳統,在日后的作者電影敘事中,逐漸展示出其獨特的審美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