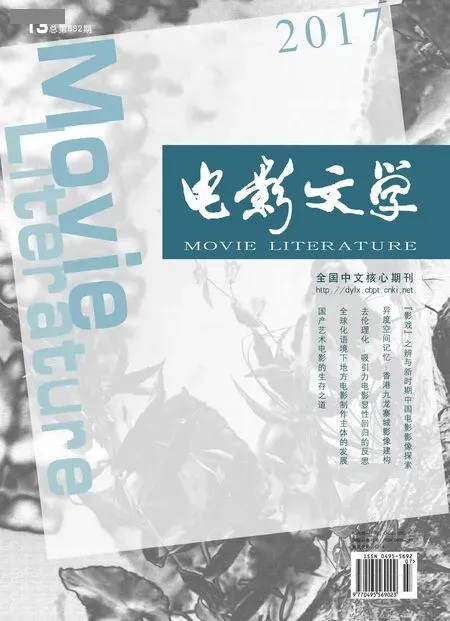紅色電影經典歌曲的時代精神與美學特征
楊 洲
(河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石家莊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河北 石家莊 050000)
紅色電影是指以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奮斗史為背景進行敘事的電影, 包括新中國成立后拍攝的電影,也包括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電影公司拍的一些電影。這些電影中的插曲或主題歌,隨著電影上映已經廣泛流行,在后世不斷被重播或唱起,可謂代代相傳,深入人心,成為經典。紅色電影中的歌曲往往比電影本身的傳播與流行更加廣泛久遠,之所以如此,不僅在于其反映了時代精神,也在于具有獨特的美學特征。
一、時代精神的藝術化體現
(一)保家衛國的犧牲精神與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
中華民族向來以愛國奉獻為人生最大價值取向,中華兒女用鮮血保衛了這片土地的和平與安寧,在世世代代的戰爭與和平的更替中,文藝中具有永恒性質的精神表達首推愛國主義。紅色經典電影主要描寫了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抗美援朝時期的英雄兒女,歌曲表達了對戰士們保家衛國的犧牲精神與崇高愛國主義情懷的高度贊揚。
論崇高的地位與影響力的強大,紅色電影中的歌曲首推《義勇軍進行曲》,這部作品是電影《風云兒女》的主題歌,聶耳譜曲、田漢作詞,于1935年由上海電通公司拍攝出品。電通公司是中共領導下的電影公司,這首歌曲風格慷慨悲壯,反映了不畏強暴、血戰到底的愛國犧牲精神。新中國成立后,《義勇軍進行曲》成為我國的國歌。
1964年上映電影《英雄兒女》中的插曲《英雄贊歌》(公木詞、劉熾曲)也是光輝名作,“為什么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是英雄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懷使山河大地更加美好,“敵人腐爛變泥土,勇士輝煌化金星”。以上兩首歌詞,即使放在白話詩歌史中,亦是佳作。烈士永恒的精神高于天際,敵人腐爛在泥土,歌詞回答了人生價值的終極追問。《英雄贊歌》集中反映了抗美援朝志愿軍戰士保家衛國的精神風貌,正如作家魏巍在報告文學《誰是最可愛的人》中熱情地贊美:“他們的品質是那樣的純潔和高尚,他們的意志是那樣的堅韌和剛強,他們的氣質是那樣的淳樸和謙遜,他們的胸懷是那樣的美麗和寬廣!”[1]
(二)建設新中國的自豪感與自信心、珍惜美好新中國的生活態度
新中國成立后最大的戰爭是1950年10月到1953年7月的抗美援朝。抗美援朝的勝利保衛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獨立,捍衛了新中國的安全,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打出了中國的國威和軍威,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以抗美援朝為題材的經典電影有拍攝于1956年的《上甘嶺》和拍攝于1964年的《英雄兒女》,兩部電影中的歌曲充分反映了這種時代精神。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稻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住,聽慣了艄公的號子,看慣了船上的白帆。這是美麗的祖國,是我生長的地方,在這片遼闊的土地上,到處都有明媚的風光。”(《我的祖國》,喬羽詞、劉熾曲)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新中國成立不久,建設新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漲情緒與人民當家做主的自豪感構成了時代精神的內涵,抗美援朝的勝利鼓舞了全國人民,《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風靡全中國。全篇歌詞洋溢著熱愛家鄉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保衛家鄉的愛國深情,反映了珍惜美好新中國的生活態度。《我的祖國》曲作者劉熾以“純潔、深情、火熱、優美”八個字作為這首歌的藍圖來發展旋律,在創作時著力追求兩點:民族風格和時代感情。[2]劉熾還為影片寫了主題歌《英雄頌》,劉熾曾說,將《我的祖國》當成柔美明媚的女兒,將《英雄頌》作為威武不屈的兒子,他倆各有風貌、性格,但共同點都是民族的,而不是俄羅斯的、法國的和德意志的,是新生的共和國的。可以說,為時代精神寫作,是詞曲作者共同的創作意圖。
二、美學特征
(一)以景起興,情景交融
《我的祖國》歌詞以景起興,敘述了大河兩岸,風吹稻花的魚米之鄉,一落筆就筆勢開闊,寫人、寫志、寫胸懷、寫友誼,做到了情景交融。景是山河遼闊、風光明媚的大景,情是開辟新天地、建設偉大祖國的壯志雄心與寬闊胸懷,對朋友我們真誠熱情,對敵人我們堅決抵抗,這是英雄的祖國、和平的祖國。文論家劉勰言:“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滿于海。”長江大河的臨岸遠眺,情思與旋律如大河一樣源遠流長,永遠向前,歌詞音韻上大多采用上揚的平聲ang韻,旋律音色明快高揚,充滿深情。
創作于1958年的《洪湖水浪打浪》是電影《洪湖赤衛隊》的主題歌,開篇以洪湖水波浪的景色起興,然后描寫漁民辛勤捕魚,晚上回來魚滿倉,四處野鴨和菱藕,秋收稻谷香,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色。“洪湖水呀長呀嘛長又長啊,太陽一出閃呀嘛閃金光啊,共產黨的恩情比那東海深,漁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強。”這首歌曲由梅少山、張敬安、梅會召、歐陽謙叔作詞,張敬安、歐陽謙叔作曲,歌詞以水之源遠流長和太陽金光閃耀之景來寫黨的恩情,漁民光景越來越好,運用了情景交融的藝術手法。歌詞音韻上大多采用上揚的平聲ang韻,旋律悠揚開闊而美好。
《英雄頌》(喬羽詞、劉熾曲)開篇就是“狂風呼嘯,大海翻騰,朝霞燃燒,山麓昂胸——硝煙滾滾,火勢熊熊,殺聲吶喊,鐵石飛崩”,以自然界具有宏偉壯麗氣質的事物和戰場中激烈的戰況來表現與烘托英雄舍生忘死的激情,從而形成巨大的震撼力。
清著名古文理論家姚鼐在《復魯絜非書》中,曾對詩文陽剛美和陰柔美的審美特征做了描述:“其得于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得于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云,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3]紅色經典電影中的歌曲,或以雷霆萬鈞之氣勢,磅礴而出如長江大河,或剛健清新明朗如初生之太陽,燦如云霞,具有鮮明的美學效果。
(二)幽默中的藝術浪漫性與歷史真實性
1940 年,電影《青年中國》以《游擊隊歌》(賀綠汀詞曲)作為插曲:“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歌曲顯示了一種幽默與樂觀,類似的精神氣質在1956年的電影《鐵道游擊隊》插曲中也可以看到:“爬上飛快的火車,像騎上奔馳的駿馬,車站和鐵道線上,是我們殺敵的好戰場,我們爬飛車那個搞機槍,闖火車那個炸橋梁,就像鋼刀插入敵胸膛,打得鬼子魂飛膽喪……”(蘆芒、何彬詞,呂其明曲)快速的音符跳躍著,顯示了鐵道游擊隊的英勇、敏捷、機智頑強。
拍攝于1962年的《地道戰》則以幽默的筆調敘寫華北平原樸實的莊稼漢們巨大的戰斗能量:“莊稼漢嘿莊稼漢,武裝起來千千萬,嘿武裝起來千千萬,一手拿鋤頭一手拿槍桿,英勇頑強神出鬼沒展開了地道戰。”(傅庚辰詞曲)
幽默是一種智慧,是對事物發展方向與前途盡在掌控中的一種自信。這兩類歌曲,一是反映了游擊戰的用兵如神與靈活性、主動性、進攻性與速決性,特別是游擊戰對敵人強大的打擊力量;二是反映了人民戰爭戰勝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性。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動員與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和支持,是反侵略戰爭勝利的根本保障。當組織武裝起來的農民去抗擊日本侵略者時,他們的力量是無限巨大的,足以形成陷敵人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這類歌曲藝術浪漫性與歷史真實性的結合,使得歌曲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
(三)原型意象的使用
紅色電影歌曲之所以成為經典,與歌詞中使用文化原型有一定關系,文化原型是民族歷史文化的記憶聯想群,屬于“集體無意識心理領域”,常常伴隨著大量的已知聯想物,因此特定文化中的大多數人都很熟悉它們。中國歷史文化在五千年的發展中形成了很多具有特定內涵的原型意象,例如,“長城”是一個重要的原型,長城是抵御外敵入侵的屏障,無數次被寫進詩詞歌賦,特別是邊塞詩。長城是一個與戰爭、戍邊、愛國、思鄉、英雄相關的詞語,與蒼茫無極、烽火落日、悠悠邊愁、鐵騎雄風等意象融合在一起,是國家民族的象征,是反抗入侵、保家衛國的文化意象。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越是悠久,原型就越有豐富的價值與內涵,越對后世有心理上的聯系與凝聚力量。例如《長城謠》,潘孑農作詞、劉雪庵作曲,原本是潘孑農編劇的電影《關山萬里》中的插曲,青年歌唱家周小燕在武漢合唱團領唱這首歌曲,1938年在新加坡應百代唱片公司邀請灌制了《長城謠》唱片,這首歌曲成為激勵海外華僑支持抗戰的精神力量。“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歌詞通俗易懂,寫的是最普遍的愛國之心,廣受歡迎與傳唱。
1937年的老電影《馬路天使》的插曲是田漢作詞、賀綠汀作曲、周璇原唱的《四季歌》:“血肉筑出長城長,儂愿做當年小孟姜。”《義勇軍進行曲》 也使用了長城意象:“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上述歌曲成為傳遍國內外的名曲,與歌詞中的原型意象有一定關系。
《我的祖國》使用了“大河”的原型意象,賀錫德的文章《從“一條大河”到“我的祖國”》記載了沙蒙導演就《我的祖國》首句和詞作者喬羽商量的舊事:沙導演問能否將“一條大河波浪寬”改為“萬里長江波浪寬”,喬羽忙說:“這可不行!這首詩是寫家鄉、寫祖國的。我想,很多人家門口會有一條小河,特別是當他小的時候看到那小河,哪怕是門前流過的一條小水溝,在他的心目中,也算是一條大河了。人們長大后思念起故鄉,會自然地想起那條河來,這樣,后面的詞‘我家就在岸上住’才能接得上去,使更多的人感到親切。”[2]不是哪條特定的大河,卻因此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可以是長江,可以是黃河,是歌者或聽眾家鄉門前的任意一條河。世界上各種文明的發源地一般都在大河流域,河流文明承載了人類繁衍生息的歷史印記,是人類情感與心理的重要依托。長江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大地山河是中國文化的血脈。河流文化承載了祖先昔日的光榮與輝煌,是激勵后人克服困難前進的精神動力。因此,愛國主義首先是熱愛自己國家的大好河山。南宋名將岳飛曾手書“還我河山”,書法蒼勁俊逸,洋溢著岳飛對收復失地的壯志豪情,令后人敬仰;中國萬里長城四大關口之一的大境門匾額題字是“大好河山”,雄渾壯觀,令觀者油然而生家國意識;抗日戰爭期間,一寸山河一寸血,山河之情凝聚人心,光未然作詞、冼星海作曲的《黃河大合唱》令無數炎黃子孫動容。1949年以后,新中國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用辛勤與智慧改天換地,使祖國山河煥然一新,這是作為中國人的國家自豪感。《我的祖國》中“山河”之感受已遠非昔日“東亞病夫”時可比。
總之,優秀的歌曲內容與文辭上都要有自己的特征,古代文論有風骨概念,指的是鮮明、生動、凝練、雄壯有力的風格,凡有“風骨”之作,往往是詩文名篇,“風骨”用來比喻近現代以來紅色電影中的經典歌曲也很恰當。特殊的時代造就了特殊的文藝,有些紅色電影故事的情節,隨著時間流逝,人們會有所淡忘,但是電影中的歌曲仿佛其靈魂,由于人民群眾共同的需要與心理,由于傳唱的方式更容易普及和復制,這些歌曲在生活中總是不斷被唱起,從而形成游離于電影之外的一種文化現象,以其無私的家國情懷深化為民族集體的記憶,流傳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