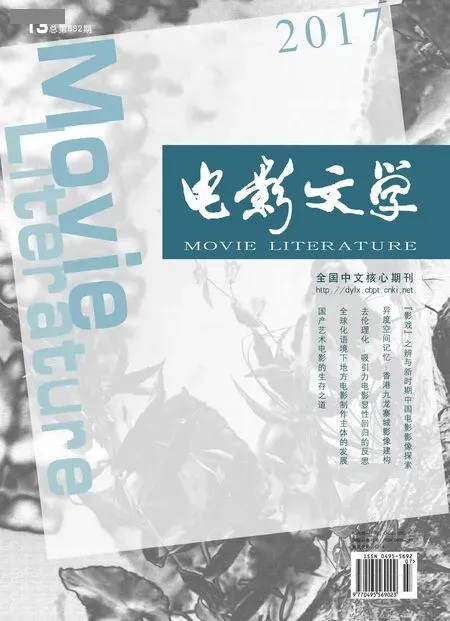方圓中的“共同體”與“社會”
白 蔚
(沈陽航空航天大學,遼寧 沈陽 110136)
工業化以來的社會變遷引發了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現代性轉型,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自外于這一現代化浪潮。這一現代化浪潮帶來人類生活方式的巨大變革,德國社會思想家騰尼斯用“共同體”與“社會”命名人類的兩種主要的生活形式,即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或者稱為“禮俗社會”與“法理社會”的生活方式。類似的表述在韋伯、迪爾凱姆的著作中也有所論及(比如,迪爾凱姆的“有機團結”與“機械團結”)。概而言之,“共同體”憑借血緣或地緣的紐帶,依靠共同的價值觀和傳統倫理將群體成員組合在一起,人們彼此守望互助、親密無間,“共同體”將群體內外邊界加以明確地區隔,一方面為個體提供了穩定的歸屬感和溫暖的精神依托,使個體獲得明確的身份認同,同時也強化了個體對群體的依附,弱化了個體的獨立性。馬克思說:“我們越往前追溯歷史,個人,從而也是進行生產的個人,就越表現為不獨立,從屬于一個較大的整體。”①按照馬克思的論述,在前現代社會,是沒有真正的個體存在的。現代社會的顯著特征即個體的生成與個人意識的覺醒。工業化打破了傳統社會共同體的封閉結構,加速了傳統共同體的式微,促進了現代社會的形成,迫使走出“共同體”庇佑的人們組成了“社會”。“社會”即原子化的個人相互訂立契約而結合在一起的。在滕尼斯等社會學家的論述中,鄉鎮與城市分別被看作是代表著“共同體”與“社會”的生存空間。
電影《我不是潘金蓮》中,主人公李雪蓮就是生活在一個鄉鎮的“共同體”中,這一生存空間在電影中被以圓鏡頭的形象化語言加以表達。李雪蓮試圖用與前夫假離婚的方式謀求個人私利或家族利益(不論是房子還是二胎指標),說明她不是一個尊重契約精神、具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執法人員將她視為法盲加刁民并不為過。“所謂契約精神,就是導源于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所派生的契約關系及其內在原則,是基于契約關系的一般要求而煥發出的一種平等、自由精神和尚法、守信品格。法治和信用是現代社會保障契約實現的基本機制,因此,尚法、守信品格是契約原則的內在要求,也是契約精神的重要內容。”②婚姻是什么?是契約,定約就須遵守,李雪蓮卻公然在法院踐踏了婚姻契約的神圣性與法律的尊嚴。電影中,不僅李雪蓮不尊重婚姻契約,前夫不遵守夫妻的私下契約,趙大頭也不遵守對李雪蓮的愛情盟約,法院小庭長也不遵守與趙大頭的私下契約……所有人都懂得利用契約這個手段來爭取自己的最大權利,但都不具備現代契約精神,所有人都不是習慣于法治化生存的現代公民。李雪蓮假離婚的初衷因為履行了正常的法律程序變成了真離婚,在王公道等法院人員看來完全是合法的,但在李雪蓮心里,合法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合情合理。因為在一個“共同體”中,規范人們行為的不僅僅是法律,而是情理,倫理規范甚至強過法律規范。而這個“共同體”早已不是純粹的封閉的生存空間,是一個飽受工業化、城市化浪潮沖擊的鄉鎮,所以身處其中的李雪蓮不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農村婦女,而是既具有現代公民的權利意識,同時又囿限于傳統社會思維方式的矛盾統一體。在她身上,體現了“共同體”與“社會”兩種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悖謬。而這種充滿張力的悖謬正是處在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中國人普遍共同的生存體驗,是避免不了的人格分裂式的現代性陣痛。從這個撕裂性的陣痛中,將誕生現代性的中國公民,將生產現代性的市民社會空間。
在電影中,李雪蓮的矛盾最初是統一在她的“共同體”的生活方式上。李雪蓮具有權利意識,并且希望通過法律保護自己的個體權利,但她的法律觀是倫理取向的法律觀,她的告狀訴求不是尋求司法公正,而是法律本不應承擔的道德訴求。她告狀的目的不是為了與前夫破鏡重圓,而是為了討回一個離婚是假的說法。當前夫在人前公然指責她是潘金蓮之后,這種訴求上升為更高的倫理取向——不僅要判定離婚是假,更要判定“我不是潘金蓮”這句否定判斷是個事實。在鄉鎮這個小小的“共同體”中,大家低頭不見抬頭見,眾人的唾沫星子能夠淹死人,無法道明卻也無須言明的善與惡的默契——公眾輿論,無形中制約著人們的行為和身份。在李雪蓮看來,自己婚前有過性行為和潘金蓮的婚后出軌,是斷然不同的。在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中,潘金蓮是一個多么丑陋的價值符號!幾個人聽到她被諷為潘金蓮,熟人口口相傳,馬上所有人都將知道她是“潘金蓮”。這簡直是奇恥大辱!李雪蓮怎能安于這樣的身份定位,她覺得自己就是含冤的竇娥。如果是在中國傳統的“共同體”中,她大可以去找家長、族長伸冤,在倫理本位、家丑不外揚的思想影響下,傳統的民間糾紛往往不是通過訴訟方式而是在法庭之外解決。“共同體”賴以維系的倫理道德規范,往往借助于族權,在宗族共同體內加以落實。但今天的鄉鎮畢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共同體”了,家族共同體的威權效應已式微,所以悲憤的李雪蓮勇敢地扛起法律這面大旗來捍衛自己的名節,她企盼一個包青天式的法官給她正名,最好當堂抬出個狗頭鍘將現代陳世美鍘掉方解心頭大恨(在電影中,李雪蓮屢次稱前夫為“禽獸”,并試圖雇人懲治前夫暴露了她非理性的情緒宣泄)。已退休的老院長對新任法院院長的告誡“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也反映了傳統社會的清官意識在現代司法人員頭腦中的遺留,呼應了李雪蓮對法律的倫理訴求。
從李雪蓮的告狀方式來看,她采取的也是“共同體”而不是“社會”的行動方式——她不是向上一級法院提起申訴履行正常的司法程序,而是找縣長、市長、省長,乃至首長,企盼清官出頭為民做主,即使走入北京這個非“熟人”“社會”(此時電影轉換成了方鏡頭),她依然習慣于尋找“熟人”(親戚或同學)——歸根到底是“共同體”的行動方式。在電影中,李雪蓮頭頂“冤”字攔轎喊冤的畫面很容易喚醒中國人曾經非常熟悉的集體記憶——秦香蓮跪下攔了包青天的轎子,民有冤情,請青天大老爺為民做主!
從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鍘美案”中,我們看到,在中國傳統社會,清官斷案帶有鮮明的倫理立場,審判的過程是對“共同體”的倫理秩序進行一次重新整飭的過程,對群體成員起到道德懲戒和倫理示范的作用。但在依法治國的現代社會,司法判決是一個事實認定和法理推演的嚴格的司法程序,本身不承擔價值擔當,它解決的只能是形式公正,而不是實質公正。法律本身應有獨立的尊嚴和地位,不再與公序良俗、宗法倫理混淆不清。李雪蓮向法律討要一個“我不是潘金蓮”的“說法”,她不能理解,一個簡單的“說法”竟然需要這樣煩瑣的過程才能確立。她不明白,她向法律訴求的是法律本身不應當承擔的任務,她解決問題的方式——尋求“熟人”幫助或者借助上級官員壓服下級,都不是法治社會的正當方式。各級政府官員可以在組織上追究下級官員工作不力、不關心群眾,卻不能直接干涉司法獨立,更改法院的判決,所以李雪蓮的告狀從法律上看注定是沒有結果的,但在客觀效果上,卻改變了相關法院和政府機關人員的仕途命運。因而在電影中出現了這樣具有吊詭意味的結果:李雪蓮好像告倒了法院院長和縣長,她的案子卻沒有翻案,她沒有得到她想要的“說法”,所以她持續幾年不屈不撓地告狀上訪。
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因為李雪蓮的案子涉及的各級組織雖然是借鑒現代科層制的形式建立起來的,卻沒有繼承現代科層制的內在精神,仍然沿襲著傳統社會的家長制組織管理模式,重“人情”輕“法理”,重“關系”輕“規則”,與現代科層制所要求的破除個人情感喜好、嚴格按照統一的規章制度管理和任免干部的原則相違背。“現代科層制最進步的地方就在于它以理性的非人格化為基礎,組織成員的一切行為都要以規章制度為導向。而中國傳統的制度中‘人情’在很多時候可以超越‘法理’,這一價值觀念至今存在于很多人的頭腦中,這使得現代科層制在組織管理上的優勢不能完全發揮,進而呈現出的是人格化與非人格化并存的‘中國式的科層制’。”③這就決定了法院和政府機關人員也是按照“共同體”的思維方式和行動方式應對李雪蓮的告狀上訪:李雪蓮為了告狀主動和法院人員拉近關系,攀親戚送特產,而當上法院院長的王公道竟然為了阻止李雪蓮上訪也憑借著莫須有的親戚關系稱呼李雪蓮“表姐”;張譯扮演的小庭長為了升職和趙大頭達成了見不得光的私下交易,用不光彩的手段算計李雪蓮,不是在正常的工作業績上下功夫,而是希圖通過“為領導分憂”來博取上級青睞。法院院長和縣長乃至市長、省長,都害怕因為李雪蓮上訪觸怒了上級領導而“帽子”不保。當這些執法人員和政府工作人員習慣于憑借“關系”“人情”,而不是通過正式的組織渠道、按照正常組織規章解決問題時,說明他們與現代科層制的精神是漸行漸遠了。他們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貪官,但也絕不是秉承依法行政的現代行政理念、熟諳科層制管理的現代公務員。
與其把《我不是潘金蓮》看作是一部隱喻的“官場現形記”,毋寧說它以方圓的鏡頭轉換形象化地展示了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從“共同體”向“社會”的變遷。與其說它因為觸碰了所謂敏感題材(上訪)而樹立了在電影史上的意義,毋寧說電影本身為我們提供了一個中國社會現代性轉型的典型文本。滕尼斯的“共同體”指的是小群體,馬克思拓展了滕尼斯的“共同體”的思想,把東方的傳統“亞細亞的”國家與社會都看作巨大的“共同體”。中國傳統社會正是有著“身份社會和倫理法律”(梁治平語)特征的巨大“共同體”。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現代性轉型過程中,由于其獨具深厚的傳統社會根基與底蘊,這一現代性轉型尤其艱難。在依法治國的現代性語境下,這個現代社會只能是法治社會。對作為個體的中國人來說,這一現代性轉型將意味著從身份到契約、從“共同體”到“社會”的生活方式的革命,它召喚著中國人的契約精神和法治觀念。電影中,當李雪蓮發現因為前夫意外去世,自己再也不能在原有的“共同體”中獲得重新身份認同了,她在“共同體”中的精神依托崩塌了,因而要自殺;最終她走進北京,選擇留在北京不再還鄉,脫離熟人世界,脫離“共同體”中的眾人視線,成為“社會”中的原子化個人,反而使她卸脫了加諸自己身上的“潘金蓮”抑或“小白菜”的身份命名,走出了生存困境。這不僅是李雪蓮的結局,從“共同體”走向“社會”,這也將是所有中國人的必經之路。這一條中國人走過的道路,將為人類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一條有別于西方模式的現代化道路。這一“社會”,是一個講道德、重倫理的禮法并治的現代社會,這一“社會”的構建,絕不是以西方現代社會為唯一參照系統與坐標的,而是既整合了中國傳統“共同體”的倫理價值,又注入了現代文明的新鮮血液的“社會”,其中,還包含著一種以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為目的的全球價值觀——習近平同志倡導的超越國族界限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這一“社會”,是具有中國特色與中國風格的現代性。它的未來指向,“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人既擺脫了自然經濟條件下對人的依賴性,也擺脫了商品經濟條件下對物的依賴性,“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④。
注釋:
①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頁。
② 周裕坤:《契約精神與社會和諧——和諧社會的法理建構》,《湖北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
③ 金輝、陶建平、金鈴:《現代科層制在中國:困境及其破解》,《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2012 年第5期。
④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