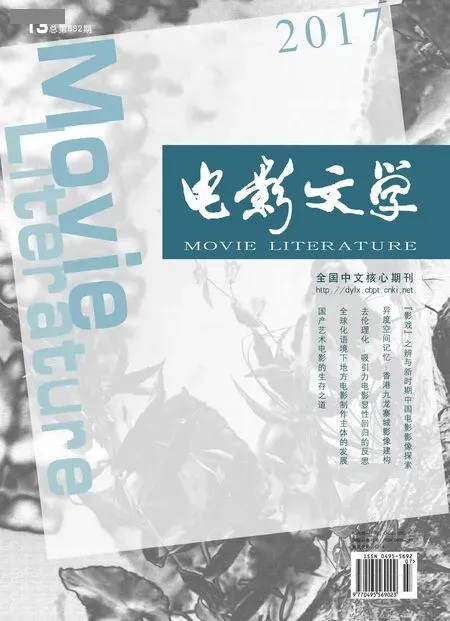文學敘事與電影敘事的沖撞與交流
王經緯
(吉林警察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近年來,基于文學文本改編的影片逐漸成為好萊塢類型片發展的一種勢頭。其原因在于流行文學改編電影既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證影片的票房,又能夠保證影片故事情節的質量。而電影的媒介效力和票房號召,又能夠從進一步擴大原作小說的讀者閱讀群體,提高小說的讀者覆蓋面,提升作者的名氣,電影和文學同時收獲雙贏。《卡羅爾》《布魯克林》《我和厄爾以及將死的女孩 》就同屬此類。但在傳統的文學改編影片之外,也出現了一部分“異類”,這一類影片對文本敘事的線路加以改造,對文本的人物塑造元素加以抽離和挑選,通過電影畫面的呈現方式,突破了原有文本的局限,僅僅以原有文本的故事架構作為創作元素加以利用。在近年來的好萊塢類型片中,大衛·芬奇的《消失的愛人》屬于其典型代表。
《消失的愛人》影片的同名小說曾經連續八周位居《紐約時報》精裝小說暢銷排行榜第一名,小說采取的是多線程、多角度的敘事策略,女主角艾米的失蹤是整個故事的主線,但這場有意識的失蹤背后,本質上還是“婚姻之難”的另一種敘事強調。在大衛·芬奇的改編中,角色塑造的縱深和立體有所削弱,故事的背景也有調整,但影片呈現了另一個面貌的故事結構。在大衛·芬奇影片版《消失的愛人》中,女主角艾米既是一個掌控者,同樣也是婚姻這場無奈博弈的一環;她既掌握了丈夫尼克的命運,同樣也失去了實質上的婚姻生活。而大衛·芬奇一貫擅長的情節翻轉、人物敘事變換、草蛇灰線的隱喻與伏筆、習以為常的對媒介和現代媒體的批評和審視在該片中也能看出端倪。作為文學敘事與電影敘事的沖撞與交流的好萊塢影片的典型樣本,對《消失的愛人》的分析也有助于對未來同類型影片建立研究范式,有利于未來研究者在此基礎上做出更具代表性和創見性的研究成果。
一、文學的定調——《消失的愛人》的敘事基礎
《消失的愛人》描述了一個現代性十足的故事。一對讓人稱羨的夫婦在結婚的第五個年頭遭遇了七年之癢,丈夫尼克來自美國的中部小鎮,大學畢業后以專欄作家的身份活躍在紐約,也借此認識了學歷、才情、容貌都十分出色的艾米。然而婚后的問題也逐漸出現,兩個人生長環境、價值觀念非但沒有磨合,還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差異。尼克自暴自棄,和女學生發生婚外情,而艾米則策劃了一場“意外”,或挽回或結束這場婚姻。
小說《消失的愛人》的敘事內容是以多視角展開的。小說的敘事中尼克以自白的方式敘述了和艾米的婚姻,在接近于疲倦和無聊的坦白中,已經可以看到尼克對婚姻表現的態度。在前半段尼克自述的氛圍表現上,很容易讓讀者聯想到另一部著名的推理小說《羅杰疑案》的敘事性詭計:描述者即犯罪者。但在后半段艾米的篇章中,讀者的心理預期被層層打破。這就形成了文本和讀者間的思維互動,甚至是智力比賽。在影片中,大衛·芬奇幾乎重現了這種敘事邏輯。在影片最初的20分鐘內,觀眾可以在尼克和瑪戈的對話中看到尼克對婚姻幾乎疲倦的態度。尼克對艾米的嘲笑,在回家后發現艾米失蹤表現的失常;女警察的懷疑等都加重了尼克殺妻的嫌疑。在影片的前一個小時內,雖然也有艾米的敘述片段,但可以看到這些片段幾乎都是中性的,不管是艾米書寫日記還是尼克追問艾米:“你在想些什么呢?”都很難讓觀眾意識到艾米本身可能存在的問題。在影片的前半段,觀眾和影片里將艾米視為“美國甜心”的普通大眾一樣,是被導演刻意誤導的。這種敘事邏輯一直到艾米的敘事角度打破整體的敘事僵局。在影片敘事和文本敘事互動上,兩者互為表和里。
在大衛·芬奇過去的導演作品中,這種對原作進行小幅度改動的現象是不多見的。這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消失的愛人》和導演風格的契合。作為敘事的底本,《消失的愛人》并不容易在畫面上呈現,其敘事的要素過分冗雜,視角限定也會導致敘事的困難,因此也使改編形成了難度。遵循原著事實上是反其道行之的改編策略之一,而原作的敘事基礎也帶給了與傳統懸疑類型片不一樣的觀感。
二、影片的敘事變革——遵循原著與挑戰原著之辨
雖然小說《消失的愛人》作為影片的內容基礎,但大衛·芬奇已經在原有基礎上做出了相對的刪改。從影片最終拍攝的效果來看,這種刪改可能出于兩種考量:其一在于避免旁白敘事的冗雜。在小說中,艾米和尼克二人互生罅隙的原因很多:尼克的不思進取、沒有商量就帶艾米回到密蘇里州的鄉下老家,尼克婚后的拈花惹草、移情別戀;艾米的苛刻要求,對尼克若有若無的輕蔑等,都是引發兩人婚姻戰爭的原因。但在影片中這些因素并沒有完全呈現。導演只是有機地選擇了幾個具有代表性的來作為二人戰爭的原因,有效地避免了電影的無用敘事。其二在于影片的篇幅限制與畫面表達的難度。影片的敘事表達很大程度上依靠畫面和對白,而《消失的愛人》中,偏偏對話和畫面都不是最重要的表達因素。如果單純只是依靠原作小說作為具體劇本,那么影片很容易徒留其形,喪失其意。
在刪改原作篇幅之外,大衛·芬奇并沒有浪費原本的敘事空間,反而嘗試用特寫和長鏡頭來表現影片的人物心緒。例如,在影片開始不久處,尼克撫摸艾米的長發,并問:“你在想些什么呢?”以及在艾米發現尼克與女學生的婚外情時,尼克對女學生的吻手禮。這些細節拼湊出了兩個人之間感情的動搖。事實上也形成了和艾米失蹤后,一系列戲劇化故事的反差。動搖婚姻的基礎本來就是細小而難以發覺的。在刪去多余旁白等之后,影片的故事呈現也更為立體和準確。
與此同時,大衛·芬奇對原作小說的改編,特別是刪減也導致了一些敘事層面的問題。對原作不甚了解的觀眾可能會在影片理解上出現偏差。例如在小說中,花了相當篇幅敘述尼克父親的背景。尼克父親是一個典型的低收入的粗暴男人。他暴躁、厭女,使妻子和孩子都生活得相當痛苦。在小說中,尼克曾經反復表示自己不要成為和父親一樣的男人。但是影片中關于尼克父親的描述則消失了,只是簡單地交代了尼克父親住在養老院。這種敘事也造成了后文敘事的倒錯。尼克的孿生妹妹瑪戈在得知尼克的婚外情事實時,情緒比艾米當時的反應更激動,她痛哭甚至表示要和尼克決裂。這種不合時宜的表現導致觀眾的聯想走進歧途。不少觀眾在觀影后,甚至猜測尼克和妹妹瑪戈之間是否存在非正常情感。事實上,瑪戈的表現在小說里描述得很清楚,她憤怒于哥哥尼克最終還是變成了他們都恐懼的父親的樣子。對尼克父親描述的忽略也影響了電影結尾時觀眾的理解。結尾時,尼克得知艾米算計他的真相,想要離婚并公之于眾,但艾米輕松地就化解了危機,艾米坦誠自己懷孕了,并且威脅尼克,她會教育她的孩子憎恨他的父親。這一點正好戳中了尼克害怕重蹈父親覆轍的心理,在這種威脅之下,尼克只能默默地繼續承受這種扭曲的婚姻。但沒有尼克父親相關的補敘,尼克的反應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就被削弱了。這種設置也導致了故事在影片整體表現上的不完整。
同樣的敘事問題還存在于敘事對象的模糊,在影片開始時,敘事是以尼克的視角展開的,觀眾對尼克的婚姻困局的感受既在戲外,也在戲內。然而在影片進行到一半時,其關注的焦點又集中在艾米身上。這種焦點的來回切換容易使觀眾的感受聚焦出現問題。在這種來回切換焦點的影響下,觀眾對尼克的好感逐層打破,而艾米的行為又很難讓觀眾產生認同,集中影響下,這種安排容易讓觀眾感到疏離。
三、超脫于敘事之外——影片與文學敘事形態的共融
在好萊塢的商業類型片導演中,大衛·芬奇一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既遵循商業影片成功的規律,努力使影片情節飽滿、劇情敘事流暢、劇本結構高潮迭起,但他也保留了自我的意識思考和獨特的自我風格。仔細觀察近年來大衛·芬奇的影片不難發現,其關注點始終集中于媒介和人的關系。不管是《十二宮殺手》《龍紋身的女孩》還是《社交網絡》《消失的愛人》,媒介或言之“新型媒介”始終是劇情敘事中的“隱形焦點”。這也提供給觀影者另一重研究《消失的愛人》的視角。觀眾既可以將《消失的愛人》看成是一場資本主義文明下的婚姻變奏曲;也可以將《消失的愛人》看成是獨屬于大衛·芬奇的媒介與人類生活情境的獨立探索。
在《消失的愛人》中媒介是無處不在的。艾米的父母是一對兒童文學暢銷書作家,艾米的童年是被“打包展示出售”的,而外界媒介對艾米的關注也造就了艾米對人在鏡頭前虛偽表象的反感;在艾米失蹤后,尼克成為媒介長槍短炮下的眾矢之的。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鏡頭中,有人對尼克喊了一聲“smile”,尼克便下意識地微笑。這一微笑也引發了近乎全劇的大眾猜測尼克殺妻的嫌疑。人在媒介之前是扭曲的、虛假的、不由自主的,甚至是無意識的。這種哈耶克式的批判在尼克登上新聞專訪節目澄清自己殺妻嫌疑時達到了頂峰。因為應對媒體的表現不佳,尼克殺妻的嫌疑陡然上升;又因為經過著名律師的指點,尼克良好的鏡頭表現又為尼克贏得了大量的同情觀眾。《消失的愛人》中,這種類似的橋段比比皆是。除了負責調查案件的女警之外,幾乎沒有人關心整個事件的真相是什么。大家都在不斷從發酵的媒介信息中追尋著虛假的真相,而相關人員則在媒介鏡頭之下不斷失真。
對媒介的嘲諷在艾米殺死前男友德西的時候達到高潮。艾米用酒瓶碎片將德西割喉。鏡頭故意放慢,血慢慢地噴濺而出,德西的表情緩慢地發生變化。觀眾作為觀看主體可以看到德西的死亡過程,但特別的是大衛·芬奇對鏡頭的選擇。在這組故事中,觀眾聚焦的重點在于艾米會不會和德西在一起,艾米會不會成功逃離德西的家。然而艾米直接將德西殺死是超脫于觀眾預想之外的。德西死亡的片段使用俯拍的手法,觀眾幾乎直面德西的死亡,但每個觀眾的情緒上都對德西的死亡感到無動于衷,有的只是困惑于未來故事的發展,這種潛在意味的嘲諷呼之欲出。不論是在影片內關注艾米失蹤的觀眾還是影片外觀看影片的觀眾,其功能都是一個不了解事實真相的“旁觀者”。而艾米的最終回歸結局也十分辛辣。在媒體的大肆宣傳下,本來意欲嫁禍丈夫行兇的艾米成為一個楚楚可憐的受害者,她謊稱自己被德西綁架,最終逃出的經歷為其“美國甜心”的形象附加了堅強的標志。在媒介刻板印象的影響下,幾乎沒有人敢公開提出艾米失蹤事件中的疑點。媒介對人形成了潛在的約束和規訓。真相如何并沒有人好奇,大眾只是在意媒體告訴了人們什么。媒介對信息的扭曲最終也暗示了尼克婚姻生活的無解——拋棄了大眾眼中善良、柔弱、堅強的受害者艾米,尼克的人生將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尼克的人品將受到徹底的質疑。這種對媒體的批駁態度也拔高了《消失的愛人》的敘事價值,完成了電影理性敘事與文化敘事的功能,促使其超脫于原始的文本之上,完成了導演的敘事目的。這種敘事邏輯也超越了普通的好萊塢劇情片,間接地使《消失的愛人》成為當代后現代敘事的改編影片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