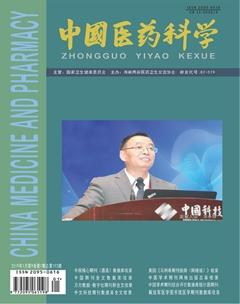PDCA管理模式在精神科急診護理管理中的應用
丁玲


[摘要]目的探討PDCA管理模式在精神科急診護理管理中的應用效果。方法選擇2016年1月- 2017年12月急診的精神障礙患者,隨機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對照組采用精神患者常規護理,研究組實施PDCA循環管理模式,找出事件危險度及可干預性措施條目,確定干預措施及實施方法。統計全部不良事件發生率,進行風險等級評估。結果實施PDCA管理后研究組患者不良事件共3件,發生率為0.02%,明顯低于對照組(11件,0.09%),嚴重不良事件無,兩組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經護士預檢分診,研究組中風險患者占比低于對照組(P<0.05),高風險患者占比高于對照組(P<0.05);急診科護士對風險等級的評估能力與干預能力提高,評分準確性由96.99a-/o提高至98.99%,評分時間縮短為(9.89+2.04)mm,前后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017年列入提前干預措施人數4406例,約占總就診人數的35.48%。結論精神科急診護理管理工作中應用PDCA循環管理,有利于提高護理人員的專業評估素養,可以有效的防范風險及降低不良事件的發生率。
[關鍵詞] PDCA循環管理;精神科急診;護理管理;不良事件
[中圖分類號] R473.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0616( 2019) 01-169-04
PDCA是一種新型管理模式,能準確分析管理程序中的不安全因素,同時采取相應的安全防范措施[1]。通過PDCA,降低不良事件的發生率,提高護患關系,同時還可減少護理風險事件。精神科患者病情特殊,行為具有危險性,可能造成傷人等攻擊性行為[2],因此,精神科護理是一種高風險工作,為了最大限度降低精神科急診護理不良事件發生率,保障急診護理質量和安全,就必須對不安全隱患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我院針對2016年1月- 2017年12月收治的精神障礙患者進行相應研究,旨在探討PDCA管理模式在精神科急診護理應用中的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6年1月- 2017年12月急診的精神障礙患者,隨機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對照組男6592例,女5843例,年齡21 - 50歲,平均為(35.3±4.9)歲;研究組男6549例,女5870例;年齡21 - 50歲,平均(35.5±5.0)歲。入組標準:(1)有肇事肇禍、擅自離院、自殺自傷的患者;(2)診斷為各類精神疾病患者。排除標準:(1)有嚴重軀體疾病轉院的患者;(2)預檢分診轉普通門診的患者。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疾病類型等方面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常規護理對照組采用精神患者常規護理,包括就醫指導、對癥處理、辦理手續,護送入院等。
1.2.2 PDCA管理模式研究組實施PDCA循環管理模式,聯合科室主任、主治醫師、護士長、護理組長等組建PDCA循環管理團隊,護士長擔任組長,指導組員進行PDCA循環管理各個項目的實施,具體干預方法如下。
1.2.2.1 計劃(P)由于神經功能紊亂,精神病患者發生狂躁、焦慮、抑郁等情感障礙時,易出現無法控制的異常行動,缺乏自主意識而引發不良事件[3]。急診患者病情重、急,而醫護人員工作比較繁重,當患者過多時,看護及巡視工作不能到位,因此會忽略部分患者的情緒及行為改變,不能完全預防或及時阻止不良事件的發生。小組分析不良事件形成的各因素,對患者進行不良事件分析、討論、總結,通過預檢分診時進行高風險項目風險評估,密切關注患者病情,給以對應的護理管理措施,加強急診安全管理。
1.2.2.2 實施(D)修訂分診登記表:在登記單背面增加目前病房在使用的風險評估表,包括肇事肇禍、自傷自殺、擅自離院[4]三項內容。(1)肇事肇禍評估:共分為6個條目,評分0-5級,數值越高代表暴力攻擊風險越大,風險評估級別達到3級及以上者屬于高風險患者[5]。(2)自殺自傷評估:共分為6個條目,評分1- 33分,數值越高代表患者自殺自傷的風險越高,總分1-5分為低風險,6-9分為中度風險,≥10分為高風險。(3)擅自離院評估:共分為5個條目,評分1 - 10分,數值越高代表患者擅自離院的風險越高,評分≤2分為低風險,3-4分為中風險,≥5分為高風險[6-7]。表格簡單易操作,重點突出易評估,分診護士可以通過三個表對就診患者進行高風險篩查并給予對應的護理措施,另外,在原有的信息登記表中增加二次分診一欄,便于患者在候診期間病情變化護士需再次評估分診。通過2周的時間對全體護士進行分診登記表、風險評估的使用進行培訓、考核。制定急診高風險患者定位管理制度[8]、巡視制度,護士長、組長抓制度的落實,尤其是重點人群如新人職、執行力弱的人員;重點時間段如繁忙時間段、晚夜間、節假日等,科學排班,加強人力資源搭配;重點環節如外帶檢查、護送入院等,按照制度執行預檢分診、風險評估、定位管理,將患者安置在指定房間,留陪護看護,護士定時巡視,對潛在暴力傾向患者采取言語安慰、心理疏導、藥物治療、保護性約束等辦法,以降低風險事件的發生。另外加快急診處置,督促醫生對高風險患者盡快處置,減少在急診滯留時間。根據精神科特點將就診患者分為3級[9-10],I級患者:危及生命或重要器官功能的,如果不采取搶救措施,有致死殘危險。如各種意識障礙、休克、心梗、藥物中毒等嚴重軀體情況需要立即搶救患者。護士通知醫生立即接診。Ⅱ級患者:明確短時間內無危及生命或嚴重致殘的征象,但需盡快處置的患者。如110/120送診、有傷害自身或危害他人的行為或風險(自殺風險評估表,評分≥6分、重性精神患者危險性行為評估表,評級為3-5級)、有明顯的并發癥或藥物不良反應患者。護士通知醫生在lOmin內接診。Ⅲ級患者:無上述兩種情況的其他急診患者。護士通知醫生在30min內接診。
1.2.2.3 檢查(C)當班護士每班自查分診是否正確、高風險評估是否與醫生的結果一致、高風險患者是否按制度要求及時處置、定位管理;組長每天檢查各班的分診記錄是否準確規范、風險評估內容是否與病歷相符、就診和急診停留時間是否按要求執行;護士長每周查監控看高風險患者的定位管理、巡視時間是否嚴格執行。及時發現問題及時糾正,從問題中找管理的漏洞,進行針對性的控制與改進。
1.2.2.4 處理(A)對科內的改進措施實施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再進行效果追蹤和評價,針對普遍存在的問題和新出現的問題,擬定持續改進策略,并作為下一循環的監控管理目標[11]。
1.3 觀察指標
對PDCA循環管理項目質量指標進行分析對比,觀察比較實行PDCA循環管理前后患者的不良事件發生率及護士對兩組患者風險等級評估,評估結果以管床醫師診斷為標準,統計護理人員風險等級評估準確性及評估時間。
1.4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20.0統計軟件分析統計數據,計數資料用率表示,進行X2檢驗,計量資料用(n+s)表示,進行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不良事件發生率
研究組不良事件總發生率為0.02%,對照組為0.09%,研究組不良事件總發生率明顯低于對照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2.2 護士預檢分診風險等級評估
經護士預檢分診,研究組低風險患者占比28.41%,中風險患者占比36.11%,高風險患者占比35.48%,與對照組28.57%、37.44%、33.73%相比,低風險指標兩組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中風險、高風險指標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3 護士風險評估準確率
護士對研究組低、中、高風險等級評估的正確率分別為99.54%、98.59%及98.83%,對照組準確率分別為98.40%、95.82%、96.75%,研究組均高于對照組(P<0.05),X2=3.874、2.369、3.018,對比有統計學意義,見表3。
2.4 評估時間
研究組評估時間明顯短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3 討論
PDCA循環管理通過四個步驟不斷循環操作,在實施過程中反復尋找問題并解決問題,根據情況做出相應調整改進,最終形成持續質量改善的護理模式[12]。在管理過程中重視監控作用,提高護理人員的嚴謹性及專業性,從而提高病房安全管理質量。PDCA循環管理對提高精神科護理安全有確切效果,有效防范護理風險[13],降低不良事件的發生率。本研究以1年收治的患者為基礎進行研究,研究數據表明實行PDCA的患者不良行為事件發生率以及等級風險評估數值明顯優于普通護理患者,評估的準確率也較高,由此可見經PDCA循環管理已見成效,經過1年的實施,精神科急診護士對患者就診風險評估、干預、防范形成固化的流程,短時間內盡早對患者的護理風險進行評估和預判,并針對性性進行防范措施,結果顯示進行PDCA循環管理后患者不良事件的發生率明顯降低,護理人員對風險等級評估的準確率明顯升高,評估時間縮短。PDCA循環管理通過提高護理人員綜合能力,使護理人員短時間內做出準確風險評估,迅速篩查出的高風險患者,不僅可節約患者候診時間,優化診治流程,同時利于提前處置、盡快處置等措施的施行以及個體化護理模式的制定,達到有效降低風險事件發生率的目的。所以將PDCA循環管理合理應用到精神科的護理工作中具有重要意義。通過識別風險因素和制定相關PDCA循環管理制度,不僅可以顯著提高護理人員的護理質量,而且可以確保精神科患者的生命安全[14-16]。同時,也要不斷的積累經驗,持續改進,提高精神科急診護理風險管理水平。
[參考文獻]
[1]周如女,羅玲,周嫣,等.應用PDCA循環管理提高護理滿意度的效果[J].解放軍護理雜志,2013,30 (11):48-51.
[2]畢翠云.精神科臨床護理風險管理研究進展[J].齊魯護理雜志,2015,21( 1): 55-58。
[3]王新婷,楊潔.PDCA護理模式改善精神科患者睡眠質量的效果觀察[J].海南醫學,2014,25( 5): 779-780.
[4]屈邦容,吳琳娜,陳姚,等.PDCA循環管理法對精神分裂癥的療效分析[J].國際精神病學雜志,2017,44(3):528-531.
[5]王威,潘軼竹,馬征,等.精神科急診患者攻擊行為危險因素的初步研究[J].精神醫學雜志,2016,29(3):170-173.
[6]袁建華.長期住院精神科患者跌倒風險的護理干預措施[J].中外醫學研究,2018,16( 12):108-109.
[7]祁玲.PDCA循環在精神科護理不良事件管理中的應用[J].青海醫藥雜志,2017,44 (4): 28-29.
[8]趙億群.精神科實施預警護理管理對不良事件發生率和護理滿意度的影響叨.中醫藥管理雜志,2018,26( 7): 14-15.
[9]李秀麗,張崇麗,董荷白,等.PDCA循環模式在精神科長期住院患者風險管理中的應用分析[J].現代實用醫學,2016,28( 12):1670-1671.
[10]葉慧麗.PDCA循環法在急診護理安全管理實施中的作用[J] .臨床醫學工程,2018,24 (2): 227-228.
[11]甘露,李秀娥,李華.PDCA循環在口腔專科醫院護理不良事件管理中的應用[J].護士進修雜志,2013,28( 13):1199-1200.
[12]王培.PDCA循環在口腔專科醫院護理不良事件管理中的應用叨.江蘇衛生事業管理,2015,26 (3): 57-58.
[13]曾勇.PDCA循環對提高臨床手術室護理質量的效果分析[J].當代醫學,2018,24( 18):66-68.
[14]高秀君,王建女,王穎,等.PDCA護理模式在改善抑郁癥患者不良情緒及心境狀態中的效果[J].中華現代護理雜志,2016,22 (4): 490-492.
[15]李斌斌.PDCA循環管理措施在急診急救中的應用效果研究[J].實用臨床醫藥雜志,2018,22( 10):94-96.
[16]蔣冬華,陳娜,劉易鳳.“精益生產”理論在精神科護理安全質量管理中的應用研究[J].中國當代醫藥,2017,24( 34):16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