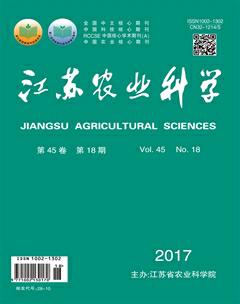生物炭對土壤磷素循環影響機制研究進展
于姣妲+殷丹陽+李瑩+周垂帆
摘要:土壤全磷含量較高而有效磷含量不足,是限制全球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生物炭作為一種新型的土壤改良劑,成為近年來研究的熱點,是由于生物炭具備特殊的性質,施入土壤后會對土壤中磷的化學行為產生重要影響。鑒于此,結合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最新的進展,從不同條件下制備生物炭的磷素特征及其對土壤磷素吸附解吸、土壤酸堿度、磷素形態轉化、土壤磷酸酶及微生物等的影響機制幾個方面綜述了國內外對生物炭影響土壤磷素有效性的研究現狀,提出了目前在生物炭對土壤磷素影響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及今后研究的熱點,以期為增加土壤磷素的有效性、提高農作物的生產力、減少土壤中磷素流失對環境的污染,以及為生物炭在土壤環境中的管理應用提供理論資料,對解決世界農業生產中所引起的資源、環境和經濟問題具有一定意義。
關鍵詞:生物炭;吸附解吸;酸堿度;磷酸酶;微生物;磷素有效性
中圖分類號: S156.2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18-0017-04
收稿日期:2017-02-22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編號:31400465);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編號:2015M570550);福建省自然科學基金(編號:2015J05050)。
作者簡介:于姣妲(1993—),女,湖南永州人,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磷素形態轉化及流失控制研究。E-mail:1036983589@qq.com。
通信作者:周垂帆,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人工林土壤改良研究。E-mail:zhouchuifan@163.com。 磷(P)是植物生長發育的必需元素,由于土壤對磷的強烈化學固定作用,致使土壤磷素多以鐵磷酸鹽(Fe-P)、鋁磷酸鹽(Al-P)和閉蓄態磷(O-P)等難溶態存在,即使土壤全磷含量高,而植物可吸收利用的有效磷含量低,因此,土壤有效磷不足一直是限制全球農業產量的重要因素。為提高地力、增加作物生產量,農業上常通過施用大量磷肥以滿足作物對磷素的需求,而由此導致的積累態磷會通過地表徑流、土體淋失進入水環境,造成水體富營養化等嚴重的環境問題,近年來日益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同時,由于自然界中磷是不可再生資源,充分合理地利用現有磷素資源對保持磷素循環平衡具有重要意義。因此,如何減緩地力衰退,特別是解決磷素有效性低下,維持作物長期生產力問題,減少磷素流失,成為當今世界農業科學最為關注的問題。近年來,眾多的研究表明,生物炭(biochar)的出現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策略。
生物炭是黑炭(black carbon)的一種類型,是由生物質在限氧條件下經300~700 ℃熱解,使木質素、纖維素和半纖維素中的短鏈含碳物質逐漸發生脫氨、脫氧作用而產生的一類高度芳香化富碳物質[1],其原料主要來源于城市、農業和林業廢棄物。生物炭比表面積大、孔隙多、穩定性強,施入土壤后可提高對養分的吸附,增加土壤碳匯,延長肥效和固持營養元素[2-3]。由于生物炭在土壤改良、肥效增加及污染修復等方面前景良好而在農業上引起廣泛關注[4-5]。特別是近幾年來,國內外眾多研究證實,向土壤中施加生物炭可減少對土壤中磷素的固定,促進土壤中難溶態磷的活化作用,影響土壤中磷素的形態分級。這些都使得生物炭在土壤磷素改善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潛力。鑒于此,本研究對生物炭自身的磷素特征、對土壤磷素有效性的影響機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旨在為有效提高植物對土壤磷素的利用效率、提高植物生產量提供理論依據,同時也能為減少大量施用磷肥造成的環境問題提供借鑒,這對解決世界農業生產中所引起的資源、環境和經濟問題具有一定意義。
1 不同條件制備的生物炭磷素特征
通常來說,制備生物炭的原材料(木屑、秸稈、禽畜糞便和其他廢料)以及溫度不同,對生物炭中磷素特征的影響很大。高溫熱解會破壞生物炭中的長鏈有機物,使其向形成短鏈有機物的方向發展,同時該過程必然會改變存在于長鏈有機物中的磷素形態[6]。Uchimiya等對不同熱解溫度(350、500、650、800 ℃)下棉花籽殼和禽糞生物炭進行研究表明,棉花籽殼、禽糞中的肌醇六磷酸鹽在350 ℃時開始向形成正磷酸鹽、焦磷酸鹽的方向轉變;當熱解溫度≥500 ℃時,禽糞生物炭中焦磷酸鹽逐漸消失,正磷酸鹽成為唯一的磷素形態;而棉花籽殼生物炭中的正磷酸鹽、焦磷酸鹽在整個熱解過程中始終存在[7]。金熠等研究發現,當熱解溫度為25~300 ℃時,豬糞生物炭中磷酸單酯區域的磷化合物迅速減少,肌醇六磷酸鹽向焦磷酸鹽方向轉變;當熱解溫度為300~600 ℃時,只存在正磷酸鹽、焦磷酸鹽;當溫度達到700 ℃時,只剩下正磷酸鹽,可能以Ca-P的形式成為唯一的磷素形態[1]。武玉研究發現,隨著熱解溫度的升高,生物炭中水洗磷(H2O-Pi)含量先增加后減少,活性無機磷(NaHCO3-Pi)含量在300 ℃或400 ℃時最高,中等活性無機磷 (NaOH-Pi)、活性有機磷(NaHCO3-Po)、中等活性有機磷(NaOH-Po)含量減少、磷灰石型磷(HCl- Pi)含量增加,正磷酸鹽先增加后減少,焦磷酸鹽減少,有機磷的含量急劇下降,說明隨著炭化溫度的升高,生物炭中易被植物吸收利用的磷素向難以被利用的磷素轉化,低溫裂解的生物炭有利于增加磷素的有效性[8]。小麥中有機磷成分因熱解而逐漸消失,正磷酸鹽和焦磷酸鹽含量卻增加,說明在熱裂解過程中生物質中有機磷主要向正磷酸鹽和焦磷酸鹽方向轉化;隨著熱解溫度的升高,花生、玉米生物炭中正磷酸鹽含量下降,有機磷單酯、焦磷酸鹽含量上升,可能是由于低溫使得含磷的復雜有機物分解出有機磷,而正磷酸鹽脫水使得焦磷酸鹽含量增加[8]。從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制備生物炭的原材料以及溫度的不同,對生物炭中磷素特征的影響很大。
2 生物炭對土壤磷素吸附解吸的影響機制
生物炭影響磷素的循環和有效性可以通過改變土壤中磷素的吸附和解吸來實現,但是研究結果存在差異性。Hale等研究發現,生物炭對磷素沒有吸附能力[9],而Chintala等的研究結果[10]卻相反。施于土壤的生物炭由于比表面積大、孔隙多,對土壤的理化性質影響較大,可顯著影響土壤的空間結構、通透性、孔隙度、呼吸作用、保持水肥的能力、微生物及養分含量等。生物炭通過比表面積、陽離子交換量和吸附作用向植物提供養分,以滿足其生長發育。研究證明,生物炭對土壤磷素的吸附能力因生物質原材料、炭化溫度和時間、粒徑與pH值等條件的不同而不同。在一定溫度范圍內,隨著炭化溫度的升高以及土壤中生物炭施加量的增加,土壤對磷素的吸附能力提高[11]。馬鋒鋒等研究發現,在中性偏酸性環境中,隨著pH值升高,牛糞生物炭對土壤磷素的吸附量增加,當pH值為7~10時相反,pH值>10時對磷素的吸附量又緩慢增加[12]。代銀分等研究發現,在堿性環境中生物炭對磷素的吸附率與pH值具有相同的變化趨勢[13]。郎印海等研究發現,施加柚皮生物炭能有效抑制土壤對磷的吸附,可能是因為施加柚皮生物炭能促進土壤中磷的活化,降低有效磷的淋失,此外生物炭還能通過影響土壤中陽離子活性或者改變微生物的活性間接影響磷素的有效性和吸附[11]。endprint
向土壤中施加生物炭后,吸附在水鐵礦上的磷解吸能力增強,從而使得氧化鐵上磷的吸附減少[14]。由于生物炭對磷素進行的是物理吸附,被吸附的磷容易被淋溶損失,所以其吸附的磷在連續4次浸提解吸后,解吸磷濃度趨于0[13]。葛順峰等研究發現,施加玉米秸稈生物炭能明顯降低土壤磷素的淋溶損失[15]。李江舟等認為,添加生物炭有效抑制了植煙土壤磷素的淋溶損失,可能是由于向植煙土壤添加生物炭后其pH值升高,促進了土壤磷素的固定,說明生物炭對土壤中磷酸鹽及可溶性有機磷具有強烈的吸附、固定作用[16]。施入改性生物炭后,潮褐土有效磷的淋失量顯著降低[17];與此相反,Doydora等研究發現,酸化的松木屑和花生殼生物炭對土壤中磷素的淋溶損失無影響[18]。土壤中施用生物炭后,紅壤、水稻土對磷素的吸附無明顯影響,可能是由于固持在土壤中的磷素被釋放,而施加的生物炭所含的磷素被土壤吸附;潮褐土、潮土在不同比例的生物炭處理條件下對磷素的吸附作用具有不同的影響,可能是因為生物炭的存在能促進弱堿性土壤對磷素的吸附,同時生物炭的灰分能降低弱堿性土壤對磷素的吸附能力[19]。綜上所述,不同類型的生物炭對不同類型土壤中磷素的吸附解吸影響具有較大差異。
3 生物炭對土壤酸堿度的影響機制
一般而言,土壤磷的有效性受pH值影響,土壤pH值低是有效磷含量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酸性土壤pH值升高或者堿性土壤pH值降低都會提高土壤磷素的有效性[16]。土壤和生物炭本身的理化性質影響了施加生物炭的土壤的pH值,使其pH值升高或降低均有可能[20],進而影響土壤中磷素的有效性。大量研究表明,生物炭可以提高酸性土壤的pH值,相反,關于生物炭降低堿性土壤的pH值則很少有研究證明[21]。武玉研究發現,施加生物炭對酸性土壤、堿性土壤pH值變化的影響均不明顯[8]。朱盼等認為,可能是因為生物炭呈堿性,施入酸性紅壤后有利于提高其pH值而降低酸度[22]。Masulili等推測,由于生物炭灰分中所含的元素如鉀(K)、鈣(Ca)、鎂(Mg)等多呈可溶態,使得酸性土壤的鹽基飽和度提高,從而使得土壤中H+和交換性Al3+的水平降低,土壤pH值升高[23]。高溫裂解產生的生物炭的灰分高,能有效抑制生物炭中的酸性物質揮發,使得其pH值更高,施入土壤能提高土壤的pH值[24]。才吉卓瑪研究發現,在生物炭處理條件下,紅壤的pH值增加 0.11~0.74,水稻土的pH值增加 0.43~1.20,但是潮褐土、潮土的pH值變化相對較小[19]。雷海迪等研究發現,添加生物炭使得土壤pH值提高了9.4%~127%[25],劉玉學等同樣發現,向土壤中添加生物炭能使土壤pH值顯著提高,這些研究均表明生物炭可以提高酸性土壤的pH值[26-27]。由于熱裂解溫度越高,產生的生物炭pH值越大,施入酸性土壤對其改良效果越好[28-29],而酸性土壤中pH值增加,使得吸附在鐵鋁氧化物上的磷素溶解,從而減少了磷素在土壤中的固定[19],所以在改良酸性土壤、提高土壤磷素有效性中,高溫生產的生物炭比低溫生產的生物炭效果更佳。由上述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生物炭能有效解決土壤酸化、鹽基離子損失等問題,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土壤磷素的有效性。
4 生物炭對土壤磷素轉化的影響機制
土壤中的磷素主要有無機磷和有機磷2種,水溶態的無機磷可以直接被植物吸收利用,而有機磷則需要礦化后才能被吸收利用。土壤有機態磷主要包括植素類、核酸類、磷酯類和其他有機磷化合物,如磷酸肌醇、磷脂、核酸、少量的磷蛋白和磷酸糖及微生物態磷等;土壤無機磷主要包括原生含磷礦物、次生無機磷酸鹽和磷酸根離子,有礦物態(磷酸鈣鹽:Ca-P,磷酸鐵鹽:Fe-P,磷酸鋁鹽:Al-P和閉蓄態磷:O-P)、水溶態和吸附態(以H2PO4-和HPO42-為主,PO43-很少)3種形態[30]。而Hedley等直接將土壤中的磷素分為植物可以利用的磷(H2O或NaHCO3提取態)、鈣結合態無機磷(HCl提取態)、鐵鋁氧化物結合態無機磷 (NaOH 提取態)以及不穩定和穩定的有機磷[31]。
研究發現,土壤中磷素主要通過沉淀和溶解、吸附和解吸、礦化和固定來轉化[21]。土壤磷素的有效性及形態轉化受生物炭的類型、添加量以及土壤類型等的影響,總體來說,向土壤中施加生物炭會不同程度地提高土壤磷素的有效性。由于向土壤中施加生物炭影響土壤中磷素的有效性及形態轉化,而生物炭對土壤磷素轉化影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1)生物炭灰分中的Mg、Ca、P、硫(S)、K在土壤中以鹽基離子的形態存在,能影響土壤中有效態磷素的轉化;(2)生物炭能提高酸性土壤的pH值,而pH值對土壤溶液中離子強度、種類有影響,因此決定了土壤固相中的磷素形態;(3)生物炭能夠結合有效磷含量低的土壤中的Al3+、Fe3+,使土壤中閉蓄態磷向有效態磷方向轉化[19,32]。才吉卓瑪等研究發現,施用生物炭能促進土壤中有效態磷的轉化,使得土壤中閉蓄態磷(Olsen-P)含量顯著增加,可能是生物炭制備過程中灰分中含有磷素造成的[19,33]。倪杰強發現,棉花秸稈、玉米穗軸和雞糞生物炭均可提高土壤全磷、有效磷和水溶性磷含量,其中對水溶性磷含量提高最明顯[21]。金熠向水稻土中施加豬糞生物炭,發現增施1.5%豬糞生物炭的2種水稻土中,正磷酸鹽、焦磷酸鹽的含量均增加,而磷酸單酯的含量卻降低[1]。
大量的研究發現,向土壤中施加生物炭對土壤不同磷素形態含量的影響與生物炭和土壤種類有很大關系。Deluca等發現,生物炭加劇了土壤難溶性鈣磷酸鹽(Ca-P)的形成,使得酸性土壤磷素有效性提高,但對中性或堿性土壤磷素的有效性基本無影響[32]。在堿性土壤中施加綠肥生物炭使得其有效磷含量顯著增加[34]。Hass等發現,雞糞生物炭施入土壤能夠增加酸性土壤中溶解性PO43-含量[35]。武玉向酸性土壤中施加生物炭表明,培養初期能增加除NaHCO3-Pi外各形態磷的含量,培養后期生物炭加強了對H2O-Pi、NaOH-Pi的正激發效應,減弱了NaHCO3-Pi的負激發效應,對NaHCO3-Po的激發效應由正轉為負,說明施加生物炭促進酸性土壤中 H2O-Pi、NaOH-Pi、NaHCO3-Pi的生成,促使NaHCO3-Po轉化為無機磷;向堿性土壤中施加生物炭,培養初期對除NaHCO3-Pi、HCl-Pi之外的各形態磷大致有個負激發作用,培養后期生物炭對H2O-Pi、NaOH-Po的負激發效應轉化為正激發效應,對NaHCO3-Po的負激發效應減弱,對NaOH-Pi的負激發作用增強,對HCl-Pi的正激發效應減弱,說明施加生物炭有利于土壤中H2O-Pi、NaOH-Po、NaHCO3-Po的生成,促進堿性土壤中的NaOH-Pi、HCl-Pi向其他形態磷轉化[8]。Mukherjee等推測,生物炭可能通過其中的陽離子橋鍵作用來影響土壤磷素的有效性[36]。此外,生物炭還可通過吸附一些螯合劑(酚酸、氨基酸、蛋白質、碳水化合物等)間接影響土壤磷素的有效性。除此之外,生物炭既可以作為外源添加物提高土壤有效態磷素含量,也能夠促進酸性土壤中外源磷的有效性[19]。endprint
5 生物炭對土壤磷酸酶及微生物的影響機制
土壤中許多微生物包括細菌、真菌和放線菌等,這些具有解磷能力的微生物能夠通過產生質子和有機酸溶解土壤不溶態無機磷,或通過分泌磷酸酶水解有機磷,將土壤中的難溶態磷轉化為有效態磷,向土壤中施加生物炭可以通過影響微生物多樣性和活性從而改變質子和有機酸的分泌,擾動土壤磷酸酶活性等,從而影響土壤磷素的轉化。土壤磷酸酶是一種適應性酶,是土壤質量的生物學指標,主要作用是催化土壤中有機磷的礦化,其活性因土壤理化性質的不同而不同,而生物炭在很大程度上能改善土壤理化性質。目前普遍認為,植物根際區微生物及土壤原生動物主要分泌酸性磷酸單酯酶;而土壤細菌、真菌及其他區系微生物只分泌堿性磷酸單酯酶[37]。才吉卓瑪研究發現,生物炭能抑制紅壤、水稻土、潮褐土和潮土的土壤磷酸酶活性,特別是對南方酸性土壤中磷酸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較明顯,可能與其施用過程中帶入土壤中的灰分有關,當與外源磷配施時抑制作用降低[19]。金熠等研究表明,增施豬糞生物炭對水稻土壤的酸性磷酸單酯酶活性有抑制作用,同時也能改變堿性磷酸單酯酶活性[1]。Zhang等發現,增施生物炭可提高土壤酸性磷酸酶活性[38]。由于pH值對土壤磷酸酶活性有很大影響[39],而將生物炭施入土壤后導致土壤pH值升高,從而改變土壤磷酸酶活性[40]。
生物炭能有效促進土壤微生物對土壤磷素的溶解、礦化以及固持作用,從而提高土壤有效態磷的含量[41]。向土壤中施加生物炭對微生物生存環境有影響,生物炭中的孔隙為土壤微生物提供充足的棲息場所,進而使得微生物數量及活性增加[42]。生物炭的吸附特性能將細菌吸附到其表面,使細菌避免受到土壤淋洗的影響[43]。除此之外,生物炭還能為微生物提供其所需要的養分[44]。因此,向土壤中施加生物炭能增加土壤微生物活性,使土壤中細菌、真菌、放線菌等微生物的磷脂脂肪酸(PLFA)含量增加[45],改變微生物種群結構。金熠研究發現,向水稻田土壤中增施1.5%豬糞生物炭顯著改變了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結構,增加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復雜程度,水稻田中細菌、真菌的磷脂脂肪酸含量以及革蘭氏陰性菌、好氧細菌的含量均增加,可能與增施生物炭會增加土壤孔隙度從而提高土壤富氧能力有關[1]。有研究表明,生物炭對不同微生物群的影響不同,玉米稈生物炭使得土壤中的微生物群落減少[46]。雷海迪等研究發現,添加杉木凋落物生物炭使得土壤中革蘭氏陽性細菌和放線菌數量增加,而革蘭氏陰性細菌數量減少[25]。
綜上所述,生物炭通過影響土壤磷酸酶活性以及微生物的群落結構進而影響土壤中磷素的有效性,對磷素循環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生物炭在調控生態系統中養分循環方面具有良好的應用前景。
6 展望
近年來,生物炭成為農業與環境科學領域的研究熱點。向土壤中施加的生物炭能通過對自身有機磷的礦化作用來提高土壤磷素的有效性,促進土壤中的難溶態磷轉化成植物可利用的可溶態磷,提高植物對土壤磷素的吸收利用效率。目前國內外學者主要圍繞生物炭本身的特性、改善土壤理化性質、促進土壤磷素的有效性、提高作物產量、減少環境污染、減輕溫室效應等方面開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一些進展,豐富了在該領域的研究。但是,今后在很多方面還需要進行更加廣泛和深入研究,例如,關于生物炭對土壤磷素有效性和流失風險的影響和作用機制缺乏全面系統的理論體系,生物炭對外源磷在不同類型土壤中磷素有效性和流失風險的影響研究不夠深入。同時,雖然大多數研究證明生物炭在土壤改良、增加土壤磷素有效性、提高植物對土壤磷素的利用率方面有積極作用,但是由于生物炭在土壤中的殘留時間較長,關于生物炭對生態環境的長期影響研究不足,理論體系不夠完善,今后應更多地研究施加生物炭對土壤中磷素循環的長期影響,同時需要對以上多個方面進行深入研究和詳盡的探討。
由于生物炭自身的特性、土壤理化性質以及各種環境因素和人為因素的不同,向土壤中施加生物炭,使得生物炭對土壤中磷素產生影響過程十分復雜。目前主要是在酸性土壤上進行生物炭對土壤磷素有效性方面的研究,而對堿性土壤的研究報道很少,研究結果也不一致,缺少大規模試驗和統計數據來支撐,亟待加強生物炭對不同類型土壤中磷素有效性及形態轉化作用機制方面的理論和技術研究。
參考文獻:
[1]金 熠. 增施豬糞及豬糞生物炭對稻田土壤磷素遷移轉化的影響[D]. 杭州:浙江大學,2016.
[2]Sohi S P,Krull E,Lopez- Capel E,et al. Chapter 2-A review of biochar and its use and function in soil[J]. Advances in Agronomy,2010,105:47- 82.
[3]Lehmann J. A handful of carbon[J]. Nature,2007,447(7141):143-144.
[4]黃 劍,張慶忠,杜章留,等. 施用生物炭對農田生態系統影響的研究進展[J]. 中國農業氣象,2012,33(2):232-239.
[5]Zhang Q Z,Wang Y D,Wu Y F,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amendment on soil thermal conductivity,reflectance,and temperature[J].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2013,77(5):1478-1487.
[6]Cimò G,Kucerik J,Berns A E,et al. Effect of heating time and temperature on the 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iochar from poultry manure[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2014,62(8):1912-1918.endprint
[7]Uchimiya M,Hiradate S. Pyrolysis temperature-dependent changes in dissolved phosphorus speciation of plant and manure biochar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2014,62(8):1802-1809.
[8]武 玉. 生物炭對土壤中磷的形態轉化以及有效性的影響[D]. 北京:中國科學院大學,2015.
[9]Hale S E,Alling V,Martinsen V,et al. The sorption and desorption of phosphate-P,ammonium-N and nitrate-N in cacao shell and corn cob biochars[J]. Chemosphere,2013,91(11):1612-1619.
[10]Chintala R,Schumacher T E,Mcdonald L M,et al. Phosphorus sorption and availability from biochars and soil/biochar mixtures[J]. Clean-Soil Air Water,2014,42(5):626-634.
[11]郎印海,王 慧,劉 偉. 柚皮生物炭對土壤中磷吸附能力的影響[J]. 中國海洋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45(4):78-84.
[12]馬鋒鋒,趙保衛,鐘金魁,等. 牛糞生物炭對磷的吸附特性及其影響因素研究[J]. 中國環境科學,2015,35(4):1156-1163.
[13]代銀分,李永梅,范茂攀,等. 不同原料生物炭對磷的吸附——解吸能力及其對土壤磷吸附解析的影響[J]. 山西農業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6,36(5):345-351.
[14]Cui H J,Wang M K,Fu M L,et al. Enhancing phosphorus availability in phosphorus-fertilized zones by reducing phosphate adsorbed on ferrihydrite using rice straw-derived biochar[J].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2011,11(7):1135-1141.
[15]葛順峰,周 樂,門永閣,等. 添加不同碳源對蘋果園土壤氮磷淋溶損失的影響[J]. 水土保持學報,2013,27(2):31-35.
[16]李江舟,婁翼來,張立猛,等. 不同生物炭添加量下植煙土壤養分的淋失[J]. 植物營養與肥料學報,2015,21(4):1075-1080.
[17]李際會,呂國華,白文波,等. 改性生物炭的吸附作用及其對土壤硝態氮和有效磷淋失的影響[J]. 中國農業氣象,2012,33(2):220-225.
[18]Doydora S A,Cabrera M L,Das K C,et al. Release of nitrogen and phosphorus from poultry litter amended with acidified biocha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2011,8(5):1491-1502.
[19]才吉卓瑪. 生物炭對不同類型土壤中磷有效性的影響研究[D]. 北京:中國農業科學院,2013.
[20]饒 霜,盧 陽,黃 飛,等. 生物炭對土壤微生物的影響研究進展[J]. 生態與農村環境學報,2016,32(1):53-59.
[21]倪杰強. 不同生物碳對滴灌棉田土壤磷素及磷肥利用率影響[D]. 石河子:石河子大學,2015.
[22]朱 盼,應介官,彭抒昂,等. 模擬降水條件下生物炭對酸性紅壤理化性質的影響[J]. 中國農業科學,2015,48(5):1035-1040.
[23]Masulili A,Utomo W H,Ms S. Rice husk biochar for rice based cropping system in acid soil 1.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ce husk biochar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properties of acid sulfate soils and rice growth in West Kalimantan,Indonesia[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cience,2010,2(1):39.
[24]Yip K,Tian F J,Hayashi J I,et al. Effect of alkali and alkaline earth metallic species on biochar reactivity and syngas compositions during steam gasification[J]. Energy & Fuels,2010,24(1):173-181.
[25]雷海迪,尹云鋒,劉 巖,等. 杉木凋落物及其生物炭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的影響[J]. 土壤學報,2016,53(3):790-799.
[26]劉玉學,王耀鋒,呂豪豪,等. 生物質炭化還田對稻田溫室氣體排放及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J]. 應用生態學報,2013,24(8):2166-2172.endprint
[27]Prayogo C,Jones J E,Baeyens J,et al. Impact of biochar on mineralisation of C and N from soil and willow litter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microbial community biomass and structure[J]. Biology and Fertility of Soils,2014,50(4):695-702.
[28]Yuan J H,Xu R K,Zhang H. The forms of alkalis in the biochar produced from crop residues at different temperatures[J]. Bioresource Technology,2011,102(3):3488-3497.
[29]Novak J M,Frederick J R,Bauer P J,et al. Rebuilding organic carbon contents in coastal plain soils using conservation tillage systems[J].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2009,73(2):622-629.
[30]孫桂芳,金繼運,石元亮. 土壤磷素形態及其生物有效性研究進展[J]. 中國土壤與肥料,2011(2):1-9.
[31]Hedley M J,Stewart J,Chauhan B. Changes in inorganic and organic soil phosphorus fractions induced by cultivation practices and by laboratory incubations[J].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1982,46(5):970-976.
[32]Deluca T H,Gundale M J,MacKenzie M D,et al. Biochar effects on soil nutrient transformations[J]. Biochar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Science,technology and implementation,2015,2:421-454.
[33]Uzoma K C,Inoue M,Andry H,et al. Effect of cow manure biochar on maize productivity under sandy soil condition[J]. Soil Use and Management,2011,27(2):205-212.
[34]Galvez A,Sinicco T,Cayuela M L,et al. Short term effects of bioenergy by-products on soil C and N dynamics,nutrient availability and biochemical properties[J]. Agriculture Ecosystems & Environment,2012,160(SI):3-14.
[35]Hass A,Gonzalez J M,Lima I M,et al. Chicken manure biochar a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ming and nutrient source for acid Appalachian soil[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2012,41(4):1096-1106.
[36]Mukherjee A,Zimmerman A R,Harris W. Surface chemistry variations among a series of laboratory-produced biochars[J]. Geoderma,2011,163(3/4):247-255.
[37]Zhang A M,Chen Z H,Zhang G N,et al. Soil phosphorus composition determined by P-31 NMR spectroscopy and relative phosphatase activities influenced by land use[J]. 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Biology,2012,52:73-77.
[38]Zhang Y,Chen L,Zhang Y,et al.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biochar application on soil phosphorus levels and phosphatase activities with visible and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J]. Spectrosc Spect Anal,2016,36(7):2325- 2329.
[39]Colvan S,Syers J,ODonnell A. Effect of long-term fertiliser use on acid and alkaline phosphomonoesterase and phosphodiesterase activities in managed grassland[J]. Biology and Fertility of Soils,2001,34(4):258-263.endprint
[40]趙 軍,耿增超,張 雯,等. 生物炭及炭基硝酸銨肥料對土壤酶活性的影響[J].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43(9):123-130.
[41]王 寧,焦曉燕,武愛蓮,等. 生物炭對土壤磷、鉀養分影響研究進展[J]. 山西農業科學,2016,44(9):1402-1405,1420.
[42]Quilliam R S,Glanville H C,Wade S C,et al. Life in the ‘charosphere-does biochar in agricultural soil provide a significant habitat for microorganisms?[J]. Soil Biology & Biochemistry,2013,65(6):287-293.
[43]Pietikinen J,Kiikkil O,Fritze H. Charcoal as a habitat for microbes and its effect on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of the underlying humus[J]. Oikos,2000,89(2):231-242.
[44]Farrell M,Kuhn T K,Macdonald L M,et al. Microbial utilisation of biochar-derived carbon[J]. The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13,465(6):288-297.
[45]Muhammad N,Dai Z M,Xiao K C,et al. Changes in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due to biochars generated from different feedstocks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J]. Geoderma,2014,226-227(1):270-278.
[46]郝 艷. 生物炭對農田土壤微生物生態的影響分析[J]. 南方農業,2016,10(17):91,94.徐繼法,徐 艷,趙吉強,等. CRISPR/Cas9系統及其在單子葉植物中的應用[J]. 江蘇農業科學,2017,45(18):21-2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