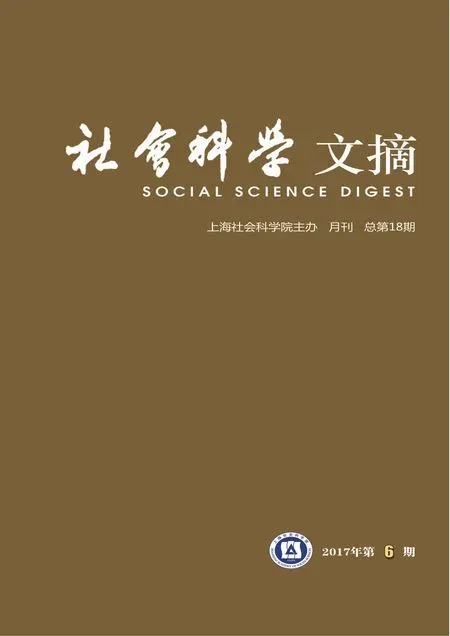論《江南三部曲》的“烏托邦”反思
文/姬志海
論《江南三部曲》的“烏托邦”反思
文/姬志海
時至今日,潛藏在《江南三部曲》三個小說文本內(nèi)部的本質(zhì)聯(lián)系并沒有得到切中肯綮的剖析與解讀。論者以為,《人面桃花》中的那個由張季元們前赴、陸秀米們后繼但建設(shè)無果的“現(xiàn)代性啟蒙烏托邦”在各種烏/惡托邦居于統(tǒng)攝全局的核心地位。四代烏托邦/惡托邦故事,正是在與這一“烏托邦”的對照聯(lián)系中才被激活自身存在的全部意義。它是其他三者共同指向的聯(lián)系樞紐和輻射中心,其所寄寓的理想矚望至今仍然是一個未竟的事業(yè)。
《江南三部曲》的反烏托邦主題考辯
在《人面桃花》發(fā)表后,格非曾說道:“我所關(guān)注的正是這些東西——佛教稱之為‘彼岸’、馬克思稱之為‘共產(chǎn)主義’的完全平等自由的烏托邦,《人面桃花》中講到的桃花源也是這么一個存在于想象之中的所在。”此后,不管有意無意,批評界關(guān)于《人面桃花》(連帶“三部曲”后續(xù)的《山河入夢》《春盡江南》)的評論重心,很多一部分都集中在對其烏托邦/反烏托邦言說的解讀上。
“烏托邦”一詞,隨著英國政治家和小說家托馬斯·莫爾爵士于1516年發(fā)表用拉丁語創(chuàng)作的小說《烏托邦》而遐邇聞名,流傳開來。“烏托邦”(Utopia)這個詞包括兩個希臘語的詞根,即,“沒有”(ou)和“地方”“處所”(topos),在拉丁文中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同時,因為諧音的緣故,這個詞就兼有“理想”“美好”和“虛幻”“縹緲”等附加涵義。
其實,在這個詞的誕生之先,烏托邦思想就已源遠(yuǎn)流長。關(guān)于烏托邦的思想起源和最早的系統(tǒng)闡述,學(xué)界普遍認(rèn)為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xué)家柏拉圖的《理想國》,也有人將之追溯到更早的希伯來先知。后來,許多國家和民族中更是都出現(xiàn)過有關(guān)烏托邦的論述,涉及宗教、哲學(xué)、政治、經(jīng)濟(jì)、社會、人文、科技等各個領(lǐng)域。作為文學(xué)的烏托邦作品是“關(guān)于一種完美的社會和政治秩序的空想描述,它表達(dá)了人們對美好世界的夢想。烏托邦……是對能夠保證每個人都過上值得一過的生活,并擺脫了匱乏和痛苦的理想社會的重建”。
就這種小說類型的寫作范式而言,是遠(yuǎn)在托馬斯·莫爾的第一部近代烏托邦小說中就奠定了的。后來的烏托邦小說創(chuàng)作者,無不沿襲著莫爾的創(chuàng)作心路,即不斷地在追求“進(jìn)步”的誘使下,創(chuàng)設(shè)和構(gòu)想著新的理想社會的完美運(yùn)行模式,并據(jù)此構(gòu)想了許多關(guān)乎人類未來發(fā)展前景的設(shè)計方案。作為“經(jīng)典烏托邦小說”殊異面目出現(xiàn)的“反烏托邦小說”事實上不過是前者在現(xiàn)當(dāng)代的發(fā)展余緒和新變而已。無論是在經(jīng)典烏托邦小說,還是在對前者進(jìn)行救弊補(bǔ)缺、反思揚(yáng)棄的“反烏托邦小說”里,烏托邦這一概念在學(xué)界是有其約定俗成的確定性內(nèi)涵的,即它的基本著眼點(diǎn)在于建立一個穩(wěn)定、統(tǒng)一的理想社會——凸出的是人的集體存在的社會構(gòu)想模式。
當(dāng)然,作為格非創(chuàng)作成熟期的巔峰作品,《江南三部曲》理所當(dāng)然地包容著多方面可供發(fā)掘的復(fù)雜內(nèi)蘊(yùn),但不可否認(rèn),對“烏托邦”的企盼、反思和袪魅是這諸多復(fù)雜內(nèi)蘊(yùn)中的基本主題之一。倘以西方小說范疇中的“烏托邦”和“反烏托邦”為參照坐標(biāo),結(jié)合特殊的漢民族文化傳統(tǒng)和中國百年歷史實際進(jìn)程中現(xiàn)代化烏托邦情結(jié)的曲折滄桑,就不難發(fā)現(xiàn),貫穿三部曲的主題紅線是格非對烏托邦的不斷建構(gòu)、反思、解構(gòu)和袪魅。其中的烏托邦包括:《人面桃花》《山河入夢》中分別以花家舍、普濟(jì)和梅城等為“載體”的“前現(xiàn)代古典烏托邦”、啟蒙色彩頗濃的“現(xiàn)代性啟蒙烏托邦”“反現(xiàn)代‘共產(chǎn)主義’烏托邦”,以及《春盡江南》中以荒誕和悖謬的方式兌現(xiàn)了的、頗具后現(xiàn)代色彩的“偽現(xiàn)代烏托邦”。在這種主要以反思和抗辯的“反烏托邦”視界的觀照下,格非在深刻內(nèi)省的基礎(chǔ)上,聲討和詰問這種種沾染著中國文化歷史境遇特殊色調(diào)的烏托邦神話所折射出來的嚴(yán)重弊害和社會恐怖圖景,消解和反叛其所各自宣稱代表的終極“真理”“正義”“自由”“善良”“幸福”等,質(zhì)疑、批判和顛覆其“企圖一勞永逸地永久性解決全部社會矛盾”的許諾。
概而觀之,格非在《江南三部曲》中關(guān)于“烏托邦”的反思,基本上是以否定性極強(qiáng)的反烏托邦形式呈現(xiàn)的。他對各種許諾給人們帶來終極解放的烏托邦都持有很大的戒心和質(zhì)疑,認(rèn)為其可能事與愿違地產(chǎn)生更大的集權(quán)、專制、奴役、剝削和壓迫等。
四代“烏托邦世界”的追求與反思
具體而微,格非在《江南三部曲》里,統(tǒng)共寫了四代烏托邦/惡托邦故事。
表面看來,仕途蹭蹬、罷官回籍的陸侃企圖“將整個村子用一條沒有間斷的風(fēng)雨長廊連起來”的烏托邦追求,似乎緣起于一幅“桃花源”圖,而實際上作者在文本中著意映射的是在前現(xiàn)代中國社會綿延已久的“大同情結(jié)”。這種情結(jié)是社會矛盾普遍化、尖銳化、深刻化的結(jié)果;是政治黑暗、人欲肆虐、災(zāi)難四伏、人類群體存在環(huán)境惡化時,具有高度社會責(zé)任感的中國古代的往圣先賢對深重災(zāi)難普遍表現(xiàn)出的“救世”愿望的縮影;是由孔子和墨翟理想世界中的堯舜時代、道家理想世界中的黃帝時代、許行理想世界中的神農(nóng)時代,共同雜糅疊加而成的陶潛的世外桃源。格非有意地將陸侃的這種人人看來無異于瘋狂的追求和抱負(fù)通過其女兒秀米之眼,在秀米慘遭蹂躪的土匪窩花家舍那里化為“現(xiàn)實”。花家舍的“總設(shè)計師”是同樣飽讀詩書、立志獨(dú)與天地之大美相往來的王觀澄,和同氣相求的陸侃一樣,他立志使其輾轉(zhuǎn)尋訪到的祥和、僻靜的花家舍在自己手里實現(xiàn)“大同世界化”,“要花家舍人人衣食豐足,謙讓有禮,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成為天臺桃源”。然而這種理想最終在一場火并中毀于一旦,花家舍成了血腥之地。這驗證了貌似保守昏聵的丁樹則的那句“桃源勝景,天上或有,人間所無”的讖言。
與對陸、王的前現(xiàn)代古典理想烏托邦的單純批判視角不同,對于張季元、陸秀米二人醉心其中的、彰顯著濃厚啟蒙色彩的現(xiàn)代文明式烏托邦,格非顯然在質(zhì)疑其非理性的同時,給予了其較多有保留的肯定。在感情和精神上雙重背負(fù)著張季元遺志的秀米,自日本接受了現(xiàn)代西方思想浸潤后重回家鄉(xiāng),領(lǐng)導(dǎo)成立了普濟(jì)地方自治會,在一間寺廟里設(shè)立了育嬰堂、書籍室、療病所、養(yǎng)老院和普濟(jì)學(xué)堂,以知行合一、積極介入的入世情懷,從啟蒙新民和革命救國兩個向度,祈求能在普濟(jì)一帶乃至整個中國建立理性、科學(xué)、民主和人道主義的人間天堂。為此她寧可放棄基本的親情倫理(這間接造成了母親的過早離世和兒子的不幸罹難),而最終只是落得個身陷囹圄、家破人亡的悲慘結(jié)局。革命失敗后秀米的閉門禁語,拒絕小驢子的來訪。這暗示了在時代多種殘酷力量和內(nèi)部變節(jié)行為的各種因素的聯(lián)合壓迫、絞殺和掣肘之下,在風(fēng)刀霜劍中苦苦搖曳支撐著的烏托邦暗火最終只能走向徹底寂滅的歸宿。區(qū)別于《江南三部曲》中其他類型的“烏托邦/惡托邦世界”,唯有這一注定在中國幾千年來長期積聚的歷史惰性和文化矢量的雙重吊詭下似乎永遠(yuǎn)也無法實現(xiàn)的現(xiàn)代性啟蒙烏托邦,才真正居于其他三種烏托邦/惡托邦類型邏輯內(nèi)聚力指向的中心,意義非凡。
《山河入夢》的故事把《人面桃花》的歷史語境從清末民初拉近到新中國建立后的20世紀(jì)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干天斗地的“大躍進(jìn)”精神的催生下,陸秀米之子譚功達(dá)終于未能走出母親精神基因暗中昭示的烏托邦幻想的宿命式老路,無可逃遁地一頭扎進(jìn)新一輪天下大同、山河都入夢中的桃源幻景中。在自己雄心勃勃的梅城規(guī)劃成為泡影之后,他卻在郭從年領(lǐng)導(dǎo)和主宰著的花家舍人民公社里,和自己苦苦尋繹的理想國猝然相遇。但是,直到得知姚佩佩的來信早已被當(dāng)局監(jiān)視和掌控,他才對自己苦苦執(zhí)著的“共產(chǎn)主義”烏托邦的荒謬性算是有了徹底反省,才看清了貌似道不拾遺、秩序井然的花家舍人民公社絕非什么烏托邦理想天堂!
與《人面桃花》和《山河入夢》兩部反烏托邦小說不同,格非在《春盡江南》中的反烏托邦故事不再是對消失遠(yuǎn)遁于某個特定時空的“過去時”陳述,而是將小說的取景框直接對準(zhǔn)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之交直至21世紀(jì)以來的世態(tài)眾生。較之前兩部小說中三個烏托邦建構(gòu)各自濃淡不勻的歷史“漫漶”色彩,格非明顯地在《春盡江南》里植入很多真實的時代符碼。可以說,以現(xiàn)實日常生活為依托,直接描摹百年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上幾代人為之上下求索奮斗的“現(xiàn)代化”訴求——這一集體烏托邦理想——終于在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開啟的新一輪時代轉(zhuǎn)型中,以悖論方式兌現(xiàn)后的全部荒誕和困境,正是《春盡江南》這部反烏托邦小說的最大主題。在格非看來,這種終于擺脫了前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文明的現(xiàn)代化烏托邦理想帶來的中國經(jīng)濟(jì)社會轉(zhuǎn)型,不僅沒有“畢其功于一役”,完成百年中國烏托邦進(jìn)程終點(diǎn)的歷史夙愿,而且還導(dǎo)致了諸如精英精神的淪陷、道德人性的喪失、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污染、個人主體性的異化乃至整個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等更加惡劣的負(fù)面惡果。現(xiàn)今的中國現(xiàn)實本身已經(jīng)發(fā)展到令人震驚的荒誕程度。王德威曾頗有見地地指出,《春盡江南》這部小說似乎因為單一刻板的現(xiàn)實主義手法而略顯辭氣浮露。但也許在格非看來恰恰相反,他的《春盡江南》這部反烏托邦小說根本不再需要什么特別的先鋒小說藝術(shù)手法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相對而言,《人面桃花》和《山河入夢》兩部都還有共同的“逃亡”和“宿命”的神秘主義色彩),只需要對這個處處流溢著丑陋和罪惡的現(xiàn)實本身進(jìn)行稍事剪裁、略微濃縮的寫實性勾勒即可。正基于此,格非才以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中塑造“典型環(huán)境”“典型人物”的主要結(jié)構(gòu)技法,將他對當(dāng)下社會的痼疾、當(dāng)代人精神困局的思考,在《春盡江南》中,通過詩人譚端午的憂時傷世、頹廢放逐和律師龐家玉不斷追趕時代節(jié)拍、最終幻滅的人生軌跡,盤根錯節(jié)的其他故事人物升降沉浮不同運(yùn)命的各色表演,一一揮灑投映在時代轉(zhuǎn)型期千秋盛世虛幻外衣的掩蓋下的、由種種丑陋和罪惡交相輝映共同織就的世紀(jì)末的斑駁圖卷中。
《江南三部曲》的邏輯內(nèi)聚性
論者以為:《人面桃花》中的“現(xiàn)代性啟蒙烏托邦”在上述的各種烏/惡托邦中居于統(tǒng)攝全局的核心地位。
首先,陸、王心儀的前現(xiàn)代古典桃花源式烏托邦和張季元、陸秀米努力建設(shè)的頗具啟蒙色彩的現(xiàn)代文明烏托邦,實際上象征著格非對于古典中國在現(xiàn)代化嬗變過程中的分娩陣痛!正如陳獨(dú)秀在其《吾人最后之覺悟》一文中振聾發(fā)聵地指出的那樣:“儒者三綱之說, 為吾倫理政治之大原,共貫同條, 莫可偏廢。三綱之根本義, 階級制度是也。所謂名教, 所謂禮教,皆以擁護(hù)此別尊卑、明貴賤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獨(dú)立之說為大原,與階級制度極端相反。此東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嶺也……”由此來看,《人面桃花》中的兩種烏托邦分明就是中西倫理政治分別在封建禮教三綱和啟蒙自由平等兩種截然不同的本原下(這二者之價值沖突不可調(diào)和)各自設(shè)計的烏托邦規(guī)劃藍(lán)圖而已。王觀澄踐行的一廂情愿的古典浪漫主義桃花源式烏托邦方案失效的原因恰恰在于其內(nèi)部現(xiàn)代性因素的匱乏,這種烏托邦載體的放大版,充其量也就是類似“太平天國”天朝迷夢那樣的在歷史上循環(huán)不止卻又始終因為誕生不了現(xiàn)代性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而終究停滯不前的歷代農(nóng)民起義。
其次,在晚清之際由張季元們前赴、陸秀米們后繼的彰顯著科學(xué)、民主、自由、幸福啟蒙色彩的現(xiàn)代性烏托邦版本,雖然難免有矯枉過正的非理性弱點(diǎn),但是這種方案畢竟是傳統(tǒng)中國由封閉的老大帝國向世界現(xiàn)代文明的一次悲壯嘗試。這種烏托邦的多舛運(yùn)命,早已由中國近現(xiàn)代啟蒙和救亡的兩大時代主題力量懸殊的博弈所預(yù)設(shè)和譜就:由于封建主義加上危亡局勢,陸秀米們經(jīng)營的現(xiàn)代性文明烏托邦不可能得到穩(wěn)步發(fā)展的空間,在各種反動勢力的反復(fù)碾壓和掣肘下,最后只能夭折飄零。這就預(yù)示著:由于啟蒙理想被擠壓,老大帝國幾千年的封建余毒并沒有隨著共和國的建立而得到“徹底之解決”。共和國前三十年在郭從年們假共產(chǎn)主義的旗號下,打倒所謂資本主義的同時,走向比之更加野蠻落后的封閉保守、高度集權(quán)、以平均主義為核心特征、缺乏民主意識的反現(xiàn)代烏托邦。
郭從年們致力建構(gòu)的“反現(xiàn)代‘共產(chǎn)主義’烏托邦”與張、陸向往的“現(xiàn)代性啟蒙烏托邦”之間的承續(xù)與變異邏輯說明:本來應(yīng)該在現(xiàn)代性啟蒙和民主革命充分展開后,才可能得以完全清洗的封建主義余毒,但是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發(fā)展中,這個過程由于太過短暫即告夭折。在這樣的情況下,“共產(chǎn)主義”烏托邦的種種設(shè)想就很有可能使“封建主義”借尸還魂。
復(fù)次,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的中國,經(jīng)過了一個多世紀(jì)艱難曲折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終于從呼喚現(xiàn)代化的思想憧憬全面進(jìn)入到接軌全球經(jīng)濟(jì)“一體化”的現(xiàn)代化烏托邦理想的實踐操作階段。但是,在西方由法國資產(chǎn)階級大革命和英國工業(yè)革命兩個引擎開啟的世界“現(xiàn)代性”潮流被引進(jìn)以后,基于歷史的重負(fù)、現(xiàn)實的國情等復(fù)雜因素的制約,“去政治化”的中國并沒有得到一勞永逸的療愈。在貌似千秋盛世的虛幻外衣的掩蓋下,格非看到了這一烏托邦寓言在現(xiàn)實中國真正得以以其反面的“惡托邦”形式兌現(xiàn)以后更加荒誕和悖論的一面。“市場化”所帶來的也不僅僅是文化的商品化,還有權(quán)力與資本在各個領(lǐng)域的合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格非在《春盡江南》中承續(xù)了前兩部小說中的反烏托邦主題的基本文意和主題內(nèi)蘊(yùn),自覺對照與張、陸理想中的“現(xiàn)代性啟蒙烏托邦”,將這種“惡托邦”的全部荒誕與困境視覺化為一幅世紀(jì)末的浮世繪。
比及王觀澄建構(gòu)的“前現(xiàn)代古典烏托邦”和郭從年建構(gòu)的“反現(xiàn)代共產(chǎn)主義烏托邦”,《春盡江南》中的這幅“惡托邦”無意流溢出更多的后現(xiàn)代主義的狂歡化色彩。在端午夫婦犒勞“國舅”一行的答謝晚宴上,我們看到:資本家在讀馬克思,黑社會老大感慨中國沒有法律,被酒色掏空的投機(jī)文人在呼吁重建社會道德。這群本屬于巴赫金狂歡理論中的“小丑”角色,現(xiàn)在卻儼然被“加冕”成為社會正義的引領(lǐng)者。在堪稱“溫柔富貴鄉(xiāng)、人間銷金窟”的花家舍旅游勝地舉行的詩歌學(xué)術(shù)研討會上,我們更是看到高貴純潔的詩歌和污濁不堪的會所沆瀣一氣、革命追緬的情懷和妓女文化的情趣攜手共舞——什么高貴與卑賤、什么莊重與調(diào)侃、什么偉大與渺小、什么意義和荒誕,都已再難分清彼此之間的絕對界限,所有的一切不過是洋溢著后現(xiàn)代狂歡色彩的大雜燴而已!這是一個一切高度都被鏟平的社會,這是一個一切深度都被填埋的當(dāng)代。隨著生活、生命中應(yīng)有高度和深度的被解構(gòu),包括犧牲、獻(xiàn)身這樣往昔充滿神圣光輝的意象也被完全袪魅,變得荒唐可笑。正如格非借助故事敘述人端午在一首詩歌中對“犧牲”的解讀中詮釋的那樣:“犧牲,本來就是歷史的一部分,或者說,是文明的一部分……而在今天,犧牲者將注定要湮沒無聞。沒有紀(jì)念、沒有追悼、沒有緬懷、沒有身份、沒有目的和意義!”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xué)中國新文學(xué)研究中心;摘自《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