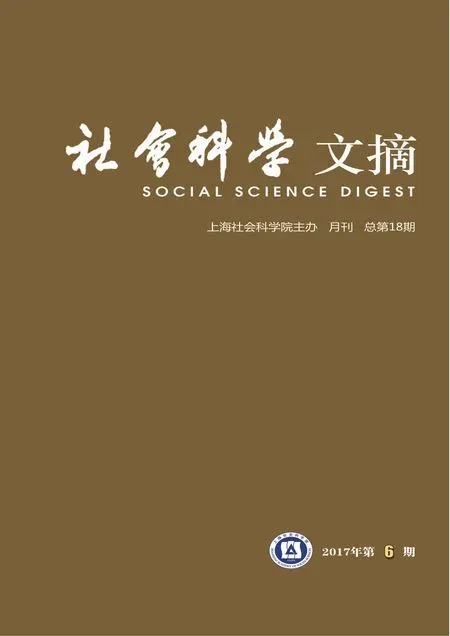國外智庫恐怖主義概念界定及其數據庫建設的評析
文/章遠
國外智庫恐怖主義概念界定及其數據庫建設的評析
文/章遠
恐怖主義對國內和國際安全具有重要地位和不容忽視的影響力。早期恐怖主義研究多使用小規模樣本分析或者少量案例比較的研究方法。時至今日,恐怖主義事件數量大幅攀升,同時數據的搜集和統計分析技術也不斷提升,使得更為成熟的統計研究和指數分析具備了可能性。恐怖主義研究經歷了從以詮釋性的小樣本分析為主,發展到多個恐怖主義數據庫良性競爭,再基于全面型數據庫建立起恐怖主義指數三個階段。其數據庫的構成往往體現著評估主體的恐怖主義治理理念。指數報告為指標體系使用者提供明晰的序列參考。大規模樣本統計分析的優點在于通過數據控制評估競爭性解釋,但也面臨著涉及客觀性、科學性、有效性、學界認可度等技術標準的質疑。本文認為量化分析恐怖主義,在質性意義上,將恐怖主義轉化為操作性定義的概念化過程貫徹著量化分析者和目標受眾的政治指向以及價值偏好,在完善和擴充我國立場的反恐數據庫時需要予以辨析。
“恐怖主義”概念的兩種界定
目前國際上比較公認的、對研究者開放的知名恐怖主義數據庫主要有“蘭德公司世界恐怖主義事件數據庫”(Rand Database of Worldwide Terrorism Incidents/RDWTI)、“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GTD)、“國際恐怖主義:恐怖事件屬性的數據集合”(International Terrorism:Attributes of Terrorist Events dataset/ITERATE)、“世界事件跟蹤系統”(Worldwide Incident Tracking System/WITS)、“恐怖主義在西歐:事件數據庫”(Terrorism in Western Europe:Events Data/TWEED)。這5個數據庫基本都是從以新聞報道為主的敘事記錄文獻中,通過計數和建立索引將描述性文字轉化為數字。總的來看,這些數據庫主要基于結果或者基于過程來界定恐怖主義現象,前者有倫理判定的色彩,后者更具有法理性特質。
(一)基于結果的恐怖主義概念定義
基于結果的恐怖主義概念定義具有一定的倫理層面特質,定義的特點是集中于強調恐怖主義造成的后果,通過評判恐怖暴力的直接目的和影響后果來否定恐怖主義在道德上的正當性。
其中,“蘭德公司世界恐怖主義事件數據庫”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參考了布魯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的恐怖主義概念,將恐怖主義概括為“有計劃地用暴力制造恐怖環境氣氛,并且脅迫他者不得不做出特定的行動,否則不放棄或者不會克制使用暴力。恐怖主義行為一般直接攻擊非軍事目標。所有恐怖主義者的動機都是政治的,恐怖主義行動方式普遍是為了實現宣傳最大化”。蘭德公司所分析的恐怖主義核心要素分別是:使用暴力或暴力威脅、計劃制造恐懼和預警、具有脅迫對方實施特定行為的意圖、動機必須包含一個政治性目標、一般直接攻擊平民目標、暴力主體既可以是群體也可以是個人。
“國際恐怖主義:恐怖事件屬性的數據集合”對恐怖主義概念的定義與蘭德公司相似,即“個人或者團體通過使用嚴重暴力或者威脅使用暴力讓對方感受到對暴力的恐懼,從而影響對方的觀點和行為。暴力的目的是政治性的,反對既有政府的權威并不是唯一的目的,而且這類事件的目標群體比直接受害者要大得多”。顯然,“國際恐怖主義:恐怖事件屬性的數據集合”對恐怖主義屬性的衡量是暴力行為的后果。
(二)基于過程的恐怖主義概念定義
在國外智庫中,主流數據庫將恐怖主義概念化的另一個取向是重視恐怖主義事件過程,基于過程,側重法理學或者直接借用現成的國內法律。這類定義強調恐怖主義代理人“非國家行為體”的政治身份地位以及暴力行為的內涵和細節,定義的重點在于否定恐怖主義的合法性。
“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是“平克頓全球情報局”(Pinkerton Global Intelligence Service/PGIS)所編輯的恐怖主義數據庫。它覆蓋了1970~1997年全球范圍內的恐怖主義數據。“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將恐怖主義定義為“非國家行為者通過制造恐懼、威脅或恐嚇的形式,威脅或實際使用非法武力和暴力,以期實現政治、經濟、宗教或社會目標”。“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所認定的恐怖主義襲擊的主體必須是非國家行為體,而且暴力行為或威脅本身必須是蓄意的。不僅如此,一個事件要被認定為恐怖主義襲擊,還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中的兩個:其一,該行為旨在實現政治、經濟、宗教或社會目標;其二,有證據表明該行為除了傷害直接受害者之外,還有計劃向更大規模的受眾發起脅迫、恐嚇或傳遞某種威脅性信號;其三,該行為不符合常規的軍事戰爭內涵。
“世界事件跟蹤系統”對恐怖主義的定義則借用了《美國法典》第22編第2656f(d)(2)節的恐怖主義定義,即“次國家/地方團體或秘密特工有預謀地、政治驅動地對非武裝人員目標犯下的暴力罪行”。相比之下,“恐怖主義在西歐:事件數據庫”在判定恐怖主義事件時注重暴力行為的細節。因此,該數據庫認定的恐怖主義暴行主體是非政府權威,是排除了國家執政當局、警察、秘密部門、軍事機構的行為者,也正因此,該數據庫并不把政變性質的恐怖事件納入其整理的數據范圍。
(三)兩種恐怖主義概念界定的異同
雖然主流恐怖主義數據庫對恐怖主義概念的定義取向不同,有基于結果的倫理向度與基于過程的法律向度的分野,但在對恐怖主義認定時至少都包含了三個要素:一是尚未到達戰爭級別的暴力或者威脅使用該級別的暴力;二是恐怖主義行使暴力所預期的影響力輻射受眾的規模要比暴行直接受害者的規模大得多;三是恐怖主義的最終目的是政治性的。
不同數據庫的主要區別在于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基于法律性恐怖主義定義的數據庫將次國家行為體和個人視為恐怖主義主體,排除了將政府以及國家機器視為恐怖分子,但基于倫理性恐怖主義的數據庫則涵蓋了國家支持的恐怖主義。二是各個數據庫對暴恐行為的測量邊界不一致。除了“造成人身傷害”這一點,各個數據庫對何種形式、何種規模或造成多大傷害的事件可定性為恐怖主義事件,并沒有達成統一的標準。相比之下,在界定恐怖主義具體行為方面,基于法律性定義的恐怖主義數據庫規范性更強。三是有數據庫強調政治性是恐怖主義目標的唯一性質,也有數據庫在政治性之外,兼容宗教性、社會性和經濟性。這就造成了不同數據庫收集和采納恐怖事件的標準不一,造成了數據規模和結構的差異。
從理論上看,只有當主要恐怖主義數據庫使用統一的恐怖主義概念,才能實現數據的有效集中,并在分析比較的過程中減少辨析理念分歧的時間消耗。現有恐怖主義數據庫所使用的恐怖主義概念仍然需要研究人員在采用不同的數據集時,規整不同的概念和認知差異,用更為接近的共識去避免對象和結果的過大偏差。
恐怖主義數據庫建設的客觀度
恐怖主義的研究設計在實現定量分析之前,多數情況下是詮釋主義的定性分析。以往的恐怖主義研究者總被認為是從自己的價值觀出發來分析少量的恐怖主義案例,他們往往被視為建構主義者或后實證主義者。小樣本的質性數據標準讓他們的研究成果被認為缺少客觀性、受主觀影響大。為了應對這些指責,定性研究者不斷修正自己研究引據的評價標準,在保證信息對象的效度和信度的同時,也權衡信息對象的權威性、透明性、普遍性和獨立性。
(一)恐怖主義量化分析的客觀性與競爭性
當代恐怖主義研究大量地使用定量分析。量化研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數據來源透明、可靠、有效,同時強調數據的完整性和經驗研究的可復制性。在恐怖主義研究中,學者通過建立、運行和測試統計模型,比較不同時間和空間背景下的恐怖主義事件,分析恐怖主義現象的特點,尋找恐怖主義產生的緣由和條件,探討恐怖主義的組織和實施過程,探討恐怖主義事件與其他社會現象的關聯性,評估反恐策略的有效性,預測恐怖主義的未來發展趨勢。
在美國學界看來,由于現有主流恐怖主義數據并不是在嚴格的學術環境下產生的,那些構建起恐怖主義分析報告的恐怖主義事件數據庫的收集方法和編碼手段都并不完全遵守科學規范。因此,從操作上看,恐怖主義事件的發生是即時的,事件的真實幕后信息也有一定的模糊性。恐怖主義數據庫的信息來源往往只能是公開媒體的實時報道。鑒于此,恐怖主義數據與其他學科領域的數據相比,不僅兼容性、客觀性和權威性較弱,而且缺乏完備性。
此外,由于數據庫開發人員使用的定義有差別,編碼也并沒有統一規則,因此哪怕對于同一件恐怖主義事件,不同數據庫的記錄也存在競爭性觀點。
造成此類差異的合理解釋是因為恐怖主義數據采集受到媒體導向的影響。具體而言,只有造成較大傷亡的事件才有可能被不同的數據庫所采納。另一方面,公共媒體對新聞事件的采編原則也缺乏統一的標準,那些沒有獲得足夠報道的恐怖事件會輕易地被數據庫所忽視。盡管如此,樂觀地看,正是因為對事件細節性質認知上的不同,數據庫之間才有了各自的特質,避免了重復建設和同質化,便于使用者根據需求作出選擇。
(二)恐怖主義量化分析與數據庫的局限性
幾乎在任何情況下,科學的指數體系都需要提高來源引用的透明度。提高來源背景材料和引用文獻的透明度也將增加恐怖主義數據的可信度,也便于用戶自主通過回查檢驗原始引文。現有的“全球恐怖主義數據庫”等主流數據庫也幾乎都認識到提高數據引據透明度的重要性,并在最新的報告中增加了對數據實際來源的明確說明和標示。恐怖主義數據庫透明度的另一個重要內涵是確認數據編輯和發布者的研究資金來源。研究者有責任了解自己所使用的數據和分析報告究竟是由誰提供和評估的,那些數字表達背后的真正主導者的利益要求是什么,他們的利益沖突方又是誰。
近年來,恐怖主義與宗教極端主義有合流之勢,這使得原本就難于客觀描述的恐怖主義現象因為增加了神秘且不容褻瀆的宗教信仰因素而更加難以準確計量。從20世紀90年代起,非世俗的恐怖主義組織在恐怖組織中所占的比例在顯著上升。這個時間節點與蘇東劇變和宗教在全世界的復興的發生時間吻合。宗教性的突發性恐怖事件總是能夠激起政府的謹慎而又快速的應對。宗教與恐怖主義并不必然相關,甚至宗教極端主義也并不必然與恐怖主義相聯系。但是,宗教精神卻能夠被用來為藐視死亡、美化暴力的恐怖主義進行辯護,為通過恐怖主義實現政治爭權提供類意識形態的合法性。針對具有宗教內核或者宗教外衣的恐怖主義,數據庫制作者會發現很難給虔誠度、宗教性、神圣性等詮釋主義色彩濃厚的象征性元素賦值,并且會在實質操作中受到教會等信仰團體的掣肘。
數據庫的差異其實暗含的是學術界和政府對恐怖主義本身理解的差異。只要這種差異存在,數據庫就很難整齊劃一。從經驗上講,如果某個命題得到不同數據庫的證實,那往往被認為是真的。
恐怖主義數據庫的應用:指數設計
規范和成熟的恐怖主義數據庫實現了恐怖主義概念和事件操作化,并以此為基礎,定序測量恐怖主義現象的相關指標,從而優化和整合關于恐怖主義的信息。這就為恐怖主義數據的指數化提供了條件。所謂恐怖主義指數,是在客觀的大樣本數據基礎上,對特定時間區間里恐怖主義現象的特點以及恐怖主義活動與其他政治、社會和經濟要素的關系所作的量化呈現,其目的是為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數據分析產品。理想的恐怖主義指數研究應將基于恐怖主義數據庫的大樣本研究方法和基于恐怖主義事件的過程詮釋有機地結合起來。
只用易統計的事件數量、傷亡人數、損失財物金額等恐怖主義結果作為指標項目,并不一定意味著恐怖主義指數分析無視恐怖主義的根源。
需要說明的是,恐怖主義指數只是反映全球安全形勢的一種指標。與此同時,評估一個國家的綜合安全形勢還要參考暴力犯罪率、軍備擴張程度、暴力示威、難民數和國內流離失所人員數等其他多個指標。
恐怖主義指數體系的結構設計也涉及數據庫建設的標準化問題。數據使用者更希望不同的數據庫遵循普遍化的編輯規則,而不是在研發伊始就分道揚鑣。這個標準框架應當包括數據規模、來源和特性的規定。有研究者為此提出“數據提供鏈”這個因素。具體而言,就是使用數據的質性分析者應以批判的眼光來辨析繁雜的數據庫,客觀地回答數據庫背后的問題,包括誰開發了這些數據、為什么要創建這個測量體系、創建者的動機和能力如何、發行機構是獨立部門還是有其他的背后影響勢力等。盡管當前的恐怖主義量化研究在恐怖主義數據的建設和可用性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仍有改進的余地,隨著數據庫的完善和擴充,恐怖主義指數可拓展的空間也將增大。
總的來說,恐怖主義數據庫和恐怖主義指數的開發機構需要更好地說明恐怖主義的定義,為指標體系制定可以抽取數據條目的工作定義,由此來消除模棱兩可和不確定的表述,讓編碼規則的描述更明確。雖然從立場不同、重點不同的恐怖主義事件描述中提取偏好關鍵字段的隨意性較大,但是應該說,數據庫開發者深化和細化恐怖主義概念的過程,也是幫助學界政界豐富對恐怖主義認知和理解的過程。
結語
在全球交往日益深化的年代,恐怖主義的變化對國家安全、叛亂應對、地區沖突、制度法律規章調整等眾多領域產生著巨大的影響,而準確定義恐怖主義是建設恐怖主義數據庫和實現恐怖主義動態監控的前提。恐怖主義數據庫必須基于對恐怖主義的科學分類,指標體系必須覆蓋恐怖主義事件的范圍、嚴重程度和頻率,同時滿足透明、客觀、有效和中立的量化等要求,并保證數據的開放性。唯有如此,恐怖主義數據庫才能夠為恐怖主義研究和反恐實踐提供堅實的經驗基礎。
建設恐怖主義數據庫的目的就是通過編年搜集全球范圍內的恐怖主義信息,探討恐怖主義的起因、組織過程和后果,揭示恐怖主義的傳播趨勢,繼而為抑制恐怖主義提供理論和經驗支持。我國學者在建設恐怖主義數據庫上還暫時落后,相關反恐數據庫還非常少。為此,我們需要在教學機構、學術研究機構、安全部門之間開展通力合作,既要官民結合又要兼顧中立性和權威性,同時保證數據制作團隊的人員規模、經費支持和可持續性。智庫正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高效途徑。正如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公布的《全球治理指數報告(2016)》所強調的那樣,中國在反恐領域也應有自己的話語權,反恐問題的全球治理缺少了中國的參與是不可想象的。這不僅是說21世紀以來在中國境內數次發生恐怖主義攻擊事件,也是說中國方案對全球反恐的未來將有所作為。
(作者系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副研究員;摘自《探索》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