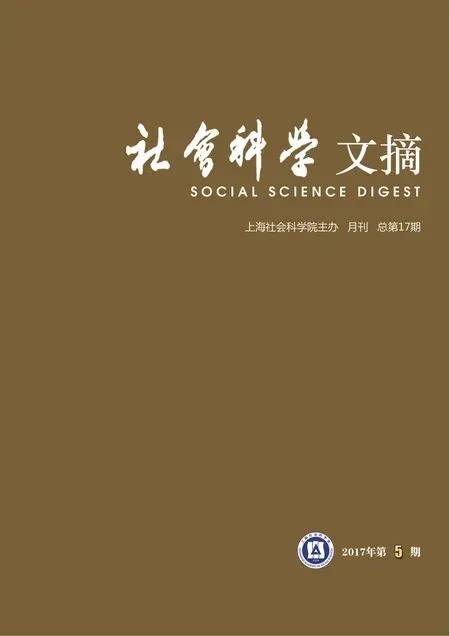從中國出發的世界政治體系與建構自主性中國社會科學的起點
文/楊光斌
從中國出發的世界政治體系與建構自主性中國社會科學的起點
文/楊光斌
工業革命開啟了現代性世界政治。資本主義是現代性世界政治的最核心要素。18~19世紀,西方國家在完成國內政治資本主義化的同時,開始了全球政治的資本主義化,即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進程。伴隨這一過程,19世紀出現了為論證殖民統治合法性的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即白人優越性。20世紀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論的實質依然是以一種文明取代其他文明。其間,雖遭遇到社會主義和民族自決權的反向運動,但由資本主義和白人優越論構成的過程性結構所演繹的結果,便是不平等性、霸權性的現狀結構,即所謂的國際制度。戰后西方社會科學基本上是在以學術形式論證當前西方主導的現狀性結構的政治合法性。而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則把美國式學術當成了學問。中國的崛起將形成從中國出發的世界政治體系,相應,這種從中國出發的過程性結構也正是建構自主性中國社會科學的歷史邏輯起點。
從中國出發的世界政治體系,首先要論述的是中國。
第一,要從歷史文化上的“文明基因共同體”的視角觀察當代中國。在日本學者溝口雄三看來,中國由中國獨自的現實和歷史而展開,這體現于漫長的不同時代種種現象的緩慢而連續性的變化,所以應該在現代、近代、前近代的關聯中來把握中國的現代。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支撐連續性的因素即基因有哪些?在筆者看來,中華民族的基因至少包括:不變的語言文字,國家大一統思想和治國的民本思想,行政體制的郡縣制、官僚制和選賢任能取向,文化上的包容與中庸之道,社會生活的自由與自治,以及家庭倫理本位,等等。這些基因代代相傳于、內化于生活在固定疆域內的中華民族的血脈中,因而構成了綿延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共同體,從而可以稱中國為中華文明基體,即由文明基因而構成的一個共同體。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未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強大文明,由此可見其生命力之旺盛及對現時代中國的影響。
第二,要理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資源。中國成為一個現代國家,是由政黨來領導完成的。孫中山創建的國民黨并未完成“以黨領軍、以黨建國”的歷史使命,是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建立現代國家的歷史任務。現代社會科學的基本脈絡來自各主要國家的現代國家建設道路,因而才有了以英國-美國經驗為基礎的社會中心主義、以法國-德國經驗為基礎的國家中心主義。這兩個主義顯然不能解釋中國等很多后發國家的現代化歷程。中國和蘇俄的經驗給了我們一個政黨中心主義的歷史版本。當然,中國政黨也不同于俄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以自己的民本主義為血脈的一種新型政治集團。顯然,很難以社會中心主義或個人權利標準來衡量中國的現代國家建設。
第三,要認識中國的治理模式。中國發展到今天,其制度必然有著世界性政治意義。但是, 對中國治理模式到底為何的問題,有不小的爭論。筆者認為就是有將近百年歷史的民主集中制政體,其中也可以分為革命時期的1.0版、計劃經濟時期的2.0版和改革開放以來的3.0版。
這些都是理解新世界政治體系的原點。從原點出發,中國影響世界的經濟主義方式就是列寧主張的國家資本主義或者今天學術界所用的詞“發展型國家”,其核心就是國家主義。沒有國家主義支配的產業政策,后發國家很難指望擺脫依附國的地位。沒有舉國體制,中國就不可能有高鐵網和各種領先世界的高科技項目,也不可能建成國際金融市場上的獨立的結算系統,而這只能依靠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這樣的國有企業去不計成本地在各國建立網點。這與歐美的基于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形成了雙向運動。中國的舉國體制在科技發展以及由此而推動的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需要得到學術界的重視。
與白人優越論的種族主義的排斥性文化不同,中國奉行的是天下觀之下的和而不同。這又與300年來的白人優越論和事實上的白人至上主義形成雙向運動,實質上是民本主義的儒家文明與個人主義的基督教文明之間的雙向運動,超越了表面上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雙向運動。
以國家為中心的經濟主義和天下體系的文化主義所塑造的世界政治主題,必然是以治理為核心的合作主義,這又與300年來流行的西方擴張主義形成了雙向運動。
上述三重雙向運動,最終的走向可能是新現狀性結構的新型國際制度,但不再是那一種單一種族和文化所主導的國際制度,而是由重大利益攸關方共同主導的國際秩序(包括國際制度和國際政治結構),或許就是中國人所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于西方在“蠻荒之地”之上的擴張性進取而建立的世界政治體系,中國人必須從既定的世界政治結構和世界政治體系出發,因而其建立過程性結構的方式與西方的經歷完全不同,必然具有漸進性的和平主義、合作主義,而不是革命性的替換戰略,因此我們才屢次強調不挑戰現存秩序。但是,結果性結構很可能是替代性的,對此西方人并不傻。
這樣,建構新世界政治體系的中國方案一開始就面臨重重挑戰。西方到20世紀才遭遇到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自決權的重大對沖,而從中國出發的世界政治體系一開始就遭遇阻擊戰,比如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當然更重大的限制性因素還是西方人主導的國際法、國際規范、國際制度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約束機制。對此,中國人絕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樣魯莽地開疆拓土。如何在既定的結構中搏出位,既需要政治勇氣(戰略決斷性行動),也需要政治藝術(策略性行動), 還需要政治定力。新世界政治體系非一代人乃至兩代人可以成就的功業,是一個積量變為質變的長周期。而中國規模意味著量變就有質變的性質。
在走向新世界政治體系的進程中,中國社會科學應該設置自己的研究議程即研究主題。就國際關系理論而言,為了維護二戰之后的格局——依然是資本主義經濟和西方白人主導的世界政治結構,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國際制度,為此在國際關系理論上演繹出所謂的新范式: 結構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和建構主義。但是,當“中國人來了”之后,這些范式的價值就應該得到反省,中國人不應該止步于這些所謂的科學范式。一個可能性假設是,以中國人為主導的或者合作博弈而形成的新國際秩序(國際制度),其過程性結構的性質與過去300年的過程性結構有著很大的不同。這是中國人建構中國學派的國際關系理論的出發點。
就政治學理論而言,冷戰時期的世界政治,說到底就是兩大制度之爭——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結果西方“打贏了沒有硝煙的戰爭”。為了這個主題,西方社會科學(不單單是政治學)的研究范式是轉型學——非西方國家如何轉型為自由主義民主的研究路徑。但是,“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以及自由民主在很多非西方國家的失敗,比如其導致的烏克蘭式的國家分裂和很多國家的長期動蕩與無效治理,迫使美國主流學者宣布“轉型范式的終結”。
西方贏得了與蘇聯的制度競爭,但效仿西方制度的非西方國家并沒有因此而走向善治:西方國家在治理上麻煩重重,出現了否決型政體。制度重要,但到底什么制度有助于治理?治理關乎政治的本質,政治形式固然重要,但那更多是讀書人的焦點,而百姓關注的是政治的實質——良善的治理,這是自政治學誕生之后便不變的使命。誰實現善治,誰才能最終贏得制度之爭。西方的治理理論基本上都是社會中心主義的,所以其治理方案在非西方國家處處碰壁,因為很多非西方國家本身都是“強社會中的弱國家”,去國家化的治理方案根本行不通。所以說,國際社會科學中并不存在統一性的治理理論。比較而言,在諸多主題中,中國最有可能在治理問題上提供研究范式,這一則是因為現在還沒有統一性的治理理論,二則是因為中國歷史文化擁有豐富的治理思想。治理理論的核心是國家治理能力問題,所以中國提出“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國家治理現代化應該成為引領世界政治話語權的學術概念。根據中國的治理經驗而建構一般性的國家治理能力理論,其中至少包括關于國家-社會關系的體制吸納力、關于國家權力各部分之間關系的制度整合能力,以及作為政治產品的政策的執行力,據此可以比較研究不同國家的治理能力,為比較政治學貢獻中國的研究視角乃至研究范式。
社會科學是特定國家特定歷史的經驗總結,其理論邏輯必須符合歷史邏輯。研究發現,二戰之后流行的國際社會科學,尤其是美國政治學流行的實證主義,不但掩蓋了應有的歷史邏輯即過程性結構——實證的都是既定的現狀性結構下的政治關系,而且其對現狀性結構的認知本身就存在選擇性偏差。這樣的實證主義研究勢必距離作為實存的真相越來越遠,因此二戰后70多年來美國比較政治學的主宰性范式才一次又一次失效,教訓不可謂不深刻。政治學基礎理論的關鍵詞,比如自由、民主、法治、公民社會、合法性,都需要在過程性結構的研究中被重新認識,即重述,重述后其意義將會完全不一樣。更重要的是,現狀性結構正在發生變化。“中國人來了”,那些為現狀性結構量身定做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的適用性也必須受到質疑。這樣說不武斷:善于學習的中國人從“拿來”各種主義和概念,再到今天“拿來”各種實證主義方法,很多都是步人后塵的非自主性行為,并不清楚為何而“主義”,為何而“實證”。學習是重要的,但是前提錯位下的學習必然產生南橘北枳的效果。中國社會科學需要從新的歷史邏輯出發,即以“從中國出發的世界政治體系”為起點,建構一套反映新的過程性結構和現狀性結構的學說。這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世代工程。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摘自《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1期;原題為《論世界政治體系——兼論建構自主性中國社會科學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