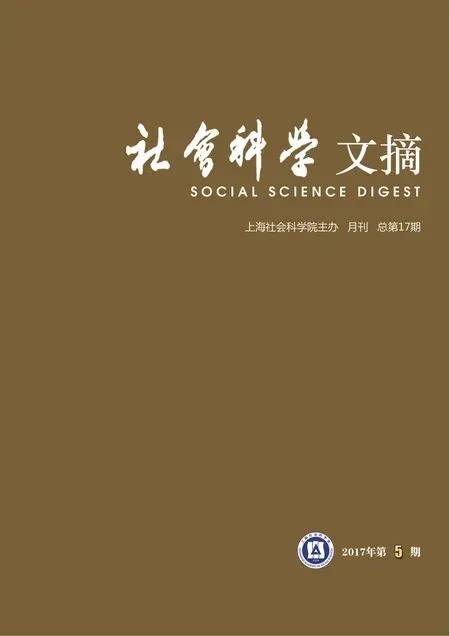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若干爭議問題
文/陳瑞華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若干爭議問題
文/陳瑞華
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在全國18個城市進行為期兩年的“刑事速裁程序”試點工作。2016年,在刑事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結束之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再次授權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在同樣的18個城市進行為期兩年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工作。
根據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報送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總結》,刑事速裁程序的試點取得了積極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在試點過程中,一些基層法官、檢察官基于實踐中所取得的積極效果,提出了一些具有超前性的改革建議。例如,有人認為刑事速裁程序沒有必要保持開庭審理的方式,而可以實行書面審理;刑事速裁程序沒有必要繼續維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最高證明標準,而可以降低這一標準;刑事速裁程序沒有必要保留兩審終審制,而可以像民事訴訟中小額訴訟程序那樣,實行一審終審制。與此同時,刑事速裁程序的試點也使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一些固有局限性得到一定的暴露。例如,目前實行的值班律師制度無法保證嫌疑人、被告人獲得真正有效的辯護,法律援助律師難以對公訴方的指控給予有力的制衡;各地在試點刑事速裁程序過程中已經引入“控辯協商”的成分,但在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情況下,這種控辯協商已經變成被告人與檢察官之間進行的不平等協商;迄今為止,所有的簡化訴訟程序的改革努力都是圍繞著簡化法庭審判環節所進行的,但這些改革努力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假如不對審判前程序進行真正的簡化,假如不對公檢法三機關的內部審批環節進行徹底的改革,那么,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改革將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
在法學界過去已對認罪認罰從寬程序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討論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對這些新出現的理論問題作出新的分析。
認罪認罰案件的審理方式
在刑事速裁程序的試點過程中,法庭庭審程序省略了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程序,只保留了公訴方簡要介紹指控罪名和量刑建議,被告人當庭發表辯護意見,以及被告人最后陳述程序。因此,法庭審理動輒持續10分鐘以內,有些案件的庭審過程甚至只有區區數分鐘。于是,一些法官、檢察官明確提出了在刑事速裁程序實行書面審理方式的建議。
很多基層法官和檢察官之所以認為法庭審理是流于形式,甚至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就在于這種庭審仍然將控辯雙方均不持異議的定罪和量刑問題作為審查的對象,而沒有確立一種新的審查對象。有鑒于此,未來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當引入一種新的審理對象,那就是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由此,未來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不僅要繼續保持開庭審理的方式,而且要將法庭審理的重心放在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問題上面。
具體而言,在被告人表達自愿認罪的意愿之后,檢察官與被告方可以就有關的量刑種類和量刑幅度進行協商和討論,在法律允許的減刑范圍內達成協議后,檢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訴。獨任法官在開庭前應當全面閱卷,審查檢察官指控的犯罪事實是否有確實、充分的證據加以支持。一旦發現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人“犯罪事實”的,法官有權立即終止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程序。在法庭審理中,法官要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進行審查。法官要詢問被告人的認罪認罰是否出于真實的意思表示,有無受到威脅、利誘、欺騙等非法行為,有無征詢過辯護律師的意見,是否了解認罪認罰的法律后果。不僅如此,法官還要詢問被告人對于指控的罪名和所提出的量刑建議有無異議,是否對選擇簡易庭審加以反悔。在對這一切確認無誤后,法官聽取被告人的最后陳述,并作出當庭宣判。
認罪認罰案件的證明標準
在刑事速裁程序的試點過程中,不少司法界人士提出了降低證明標準的建議。也有人認為盡管應繼續堅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但該證明標準的層次可根據該類案件的特點來把握。
筆者認為,對于證明標準問題,需要區分犯罪事實的證明與量刑事實的證明。無論如何,在公訴方指控的犯罪事實的證明問題上,證明標準是不能降低的,只能繼續維持在現有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排除合理懷疑這一證明程度上。道理很簡單,確立最高證明標準的3個根據并沒有因為被告人的認罪認罰而消失:無罪推定原則和實質真實原則繼續發揮作用,避免冤假錯案仍然將是一項不容回避的訴訟目標。即便法院對被告人可能判處較輕的刑罰,但是在定罪問題上是不容降低證明標準的。況且,根據筆者以前的研究和論證,無論是罪刑法定原則還是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都決定了控辯雙方不可能圍繞著指控的罪名數量和罪名本身進行協商和交易。因此,法院對被告人犯罪事實的認定,必須嚴格遵循法定的證明標準。
但在量刑事實的證明問題上,情況確實有所不同。一方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推行,使得檢察官與被告方可以就量刑幅度進行必要的協商和交易,檢察官可以降低量刑的幅度,這一幅度甚至可以達到30%左右。另一方面,在特定量刑情節的認定和解釋上,檢察官確實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權,而不必嚴格遵循法律所設定的標準。因此,為吸引更多的被告人選擇認罪認罰,同意適用簡易審判程序,檢察官對量刑事實的證明不需要達到法定的最高證明標準。即便是對那些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節,如主犯、累犯、重犯、教唆犯等,檢察官也不需要證明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這種對量刑事實證明標準的降低,既不會破壞無罪推定和實質真實原則,也不會造成冤假錯案,而只會使更多的案件得到快速審理,訴訟效率得到提高,司法資源得到合理配置。
認罪認罰案件的審級制度
據統計,在2014年至2016年的刑事速裁程序試點期間,全部速裁案件被告人的上訴率為2.01%,檢察機關抗訴率僅為0.01%。在此背景下,一些法官、檢察官提出了對刑事速裁案件實行一審終審制度的改革設想。
按照通常的觀點,在刑事訴訟中針對那些被告人自愿認罪的輕微刑事案件確立一審終審制,也可以成為一種可行的改革思路。畢竟,假如剝奪了當事人的上訴權,不允許檢察機關提起抗訴,那么,刑事案件的審判環節將得到進一步的簡化,結案周期會大大縮小,訴訟效率也會得到相應的提高。
但是,在刑事訴訟中引入一審終審制,不能僅僅關注訴訟成本的降低和訴訟效率的提高,還要考慮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根據前面的統計數字,為期兩年的改革試點結果顯示,只有2%的被告人提起上訴,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的案件更是微乎其微。這從另一角度也說明,即便在這類案件中保留兩審終審制,那些進入二審程序的案件量也是不大的,二審法院也不會增加太大的審判壓力。可以說,要指望通過推行一審終審制來降低訴訟成本、提高訴訟效率,并沒有顯著的實際意義。
另一方面,假如在未來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取消了兩審終審制,那將意味著一審法院的判決將成為終審判決,當事人的上訴權、檢察機關的抗訴權都將無法行使。這會帶來一系列消極的后果。首先,在大量被告人無法委托辯護律師的情況下,值班律師僅僅提供極為有限的法律幫助,無論是被告人還是值班律師,都無法閱卷,難以了解檢察機關所掌握的證據情況,不熟悉公訴方的“底牌”,這就造成一種控辯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局面。其次,在一審法院開庭審理基本上流于形式的情況下,二審法院假如不再對一審判決進行重新審查,那么,一審裁判的錯誤就難以糾正了。再次,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包含著控辯雙方就量刑問題的協商和討價還價成分,這里既可能發生控辯雙方違法達成協議的情況,也可能出現被告方屈從于公訴方的壓力、威脅、欺騙而被迫選擇某一量刑方案的情況。最后,一旦實行一審終審制,那么,被告人就連對一審判決提出異議、表達反悔之意的機會都失去了。
值班律師的辯護人化?
隨著2016年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工作的啟動,值班律師制度在那些被告人可能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案件中得到推行。根據這一制度,值班律師主要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等法律幫助。該制度大大突破了刑事訴訟法對法律援助適用范圍的限制,是我國刑事辯護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
但現行的值班律師制度還是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值班律師并不具備“辯護人”的身份和地位,而僅僅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一些有限的法律咨詢,無法全程參與刑事速裁程序的全部過程。其次,值班律師無法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幫助。在刑事速裁程序的試點中,值班律師并不享有閱卷和調查的權利,無法對檢察官所掌握的證據情況進行全面審核。
在筆者看來,建立值班律師制度,在法院和看守所設置法律援助律師值班辦公室,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這僅僅是辯護制度改革的第一步。這種改革還是遠遠不夠的。從理論上看,凡是在嫌疑人、被告人面臨法律風險的場合,辯護律師都有參與辯護的必要性。基于這一觀點,在嫌疑人、被告人明確表達認罪認罰的意愿時,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和法院都應當及時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師。該法律援助律師一經確認,即應具有辯護人的身份。作為辯護人,法律援助律師不應僅僅局限于為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而應享有會見權、閱卷權和調查權,并對檢察官指控的罪名和理由進行審核,對檢察官準備提出的量刑方案進行一定程度的協商。在法庭審理中,法律援助律師也應當出席庭審過程,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明智性進行審查,對檢察官的量刑建議發表辯護意見。而在被告人提起上訴后,二審法院也應為被告人繼續指定法律援助律師進行辯護,辯護律師應督促二審法院對被告人認罪的自愿性、明智性進行重新審查,對一審法院認定有罪的事實是否達到法定證明標準進行審查,并對一審法院是否存在違法法定訴訟程序的行為發表辯護意見。
控辯協商的法律控制
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推行的過程中,引入控辯雙方的協商機制幾乎是不可回避的一項改革配套措施。主流的意見認為,我國目前試行的這種控辯協商不同于美國法中的辯訴交易。那么,究竟如何對我國的控辯協商進行法律控制呢?
第一,辯護律師應參與控辯協商的過程。未來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應當確立檢察官與辯護律師進行控辯協商的機制,確保被告人獲得真正意義上的法律援助,而辯護律師應全程參與控辯協商過程和法庭審理過程,從實質上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辯護律師應當與檢察官進行協商,而不應與法官進行協商。應當確立一條法官審判活動的底線,那就是不得參與這種控辯協商的過程,更不得主動提出旨在吸引被告人認罪的量刑方案。檢察官與辯護律師所進行的控辯協商只能在庭前進行,所達成的量刑方案只能作為檢察官量刑建議的一部分,法官在庭審中只能對這種量刑建議進行審查,對于其中不合法、不自愿的量刑方案,法官應保留拒絕的權力。
第三,控辯協商應給予被害方一定的知情權和救濟權。法院在開庭前應將起訴書連同控辯雙方達成的量刑協議,一并送達被害方,以保證被害方享有對控辯協商的知情權。假如被害方對控辯雙方達成的量刑方案提出異議,法庭應給予被害方出席庭審的機會,使其發表本方的量刑意見。假如對法庭所作的裁判不服,被害人還應享有申請檢察機關提起抗訴的權利。
第四,二審法院對控辯雙方答辯協商的自愿性和合法性可以進行上訴審查。對于明顯違反法律程序、影響公正審判的一審審判行為,應當作出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的裁定。這是避免一審法院為追求快速結案而劍走偏鋒、剝奪被告人自由選擇權的基本制度安排,是不容削弱和廢除的。
刑事訴訟的全流程簡化思路
簡化法庭審理程序、壓縮法庭審理時間、減少法庭審判周期,已成為我國簡易程序改革的基本思路。但是,對那些較為輕微、無爭議的案件來說,法庭審判的周期已經被壓縮到了極限,持續的時間也已經沒有了進一步減少的余地。我國簡易程序的改革探索還可以有另一種思路,那就是在簡化審理程序之外,通過簡化審判前程序、壓縮辦案環節、跳躍訴訟階段等方式來實現。
第一個思路是“訴訟程序的省略和跳躍”。具體而言,對于嫌疑人、被告人自愿認罪的案件,在任何一個階段都應當貫徹程序省略和跳躍的思路,不必經歷完整的刑事訴訟程序,而直接將案件交由檢察官提起公訴,法院直接開庭審理。通過這種較為靈活的程序設置,原來存在的立案、審查批捕、偵查終結、審查起訴、開庭審判等訴訟程序,就不再具有嚴格的界限,而可以選擇省略中間程序,跳躍不必要的程序流轉過程,實現在立案后、偵查階段、審查起訴階段直接進入法庭審理程序,大大省略審判前的程序過程。
第二個思路是“公檢法三機關內部審批環節的簡化”。在公安機關內部,對于這類案件不再經過法制部門的審查和分管局長的審批,辦案警官可以直接提交檢察院起訴;在檢察院內部,負責辦理案件的檢察官可以自行作出提起公訴的決定,不必再向公訴處長、分管檢察長等主管官員請示匯報,檢察委員會也不再討論;在法院內部,獨任法官一律自行組織庭前會議,自行組織法庭審理,自行作出當庭宣判,自行簽署裁判文書,不再交由院庭長簽署裁判文書,也不再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通過這種改革,公檢法三機關逐步將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與員額制、司法責任制等改革措施加以銜接,逐步減小乃至取消公檢法三機關內部的層層審批機制,大幅度地加快各個訴訟階段的辦案流程。
審判程序簡易化的限度
為期兩年的刑事速裁程序試點經驗表明,在簡化訴訟程序環節、降低訴訟成本和提高訴訟效率的同時,還應保障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要求,避免可能出現的刑事誤判和量刑自由裁量權的濫用,保障被告人認罪認罰的自愿性和明智性。
迄今為止,我國以簡化刑事審判程序為中心的改革思路,已經被運用到了極致,已經到了對審判前程序乃至全部訴訟流程進行簡化改革的時候了。我們有必要對被告人認罪認罰的案件,采用跳躍中間訴訟程序的辦法、加快刑事訴訟的流程。同時,在任何一個訴訟階段,公檢法都應簡化內部審批和討論環節,賦予一個辦案人員獨立自主的決定權,從而流暢順利地推進刑事訴訟程序的進程。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摘自《中國法學》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