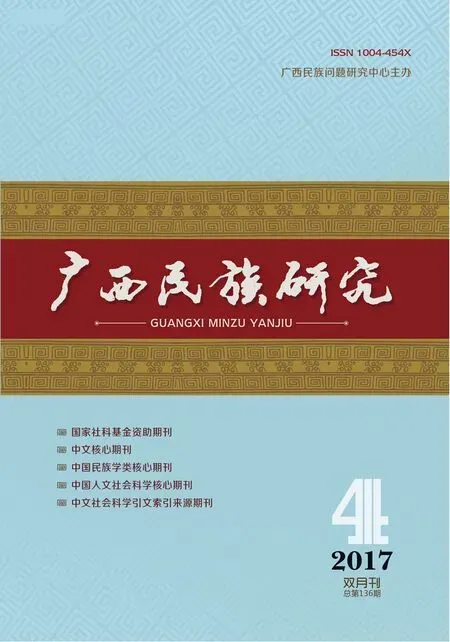民族、婚姻、伙有共耕與上帝:基督教嵌入藏區傈僳族社會之闡釋*
——以滇西北德欽縣霞若鄉為例
葉遠飄
民族、婚姻、伙有共耕與上帝:基督教嵌入藏區傈僳族社會之闡釋*
——以滇西北德欽縣霞若鄉為例
葉遠飄
基于對云南西北部一個傈僳族鄉村全體傈僳族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改信基督教的過程進行考察,指出傈僳族信仰基督教是身處碎片化、原子化社會結構中的族群面對周邊民族的歧視與物質資料和人口再生產的重重壓力下作出的無奈選擇,提出“婚姻—家庭—土地—民族”是基督教在傈僳族社會傳播的網絡,這一模式可以解釋為什么基督教在傈僳族社會傳播呈現出民族性特征,區別于基督教在漢族鄉村社會傳播呈現出的宗族性特征。
藏區;傈僳族;伙有共耕制;基督教
2016年10月,筆者趕赴云南西北部藏區進行調研。盡管去之前,筆者已經從文獻中了解到云南西北藏區是基督教在我國藏區唯一傳播成功的地區,信仰基督教的教徒大多為傈僳族,但進入到滇西北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下的霞若鄉以后,傈僳族信仰基督教的場景還是令筆者感到震撼——在該地,基督教已經被傈僳族視為本民族的民族宗教,成為區分傈僳族與其他民族的關鍵要素。期間,該地區的一位被公認為最熟悉《圣經》的女基督教徒骨干告訴筆者關于她本人皈依基督教的故事:她的母親在結婚前談過幾場戀愛都無疾而終,印象最深的是和本鄉的一個藏族小伙子愛得無法自拔,但是按照傈僳族的傳統風俗,結婚時女方需要以銀耳珊瑚及麻毯回贈男方送來的豬、牛、羊等,由于母親家里窮,拿不出財禮,被男方家嫌棄,婚姻告吹了,母親曾數次尋短見,這時早年過世的鄰居托夢勸她的母親信仰上帝,并向她保證,信了“主”以后命運就會好轉。于是,她第二天就到了維西縣的基督教堂去受洗。之后,其母親的生活果然有了起色,后來與同樣信教的本民族男子結婚,對方當時送了1000元禮金,而且不需要母親回禮,此事讓當時很多嫁女兒的家庭羨慕。在結婚當天,母親當著牧師的面立下規矩,要求日后自己的兒女們要一輩子侍奉“上帝”。
這個故事吸引筆者注意的并非其真實性如何,而是作為當地基督教的骨干在選擇性的歷史記憶中突出了民族婚姻與基督教傳播的糾結。顯然,故事敘述了一位女性從不幸到幸福的婚姻,而由不幸走向幸福的轉折點就是主人公聽了那個能夠代替上帝向主人公做出種種保證的“鄰居”的話,那么這個“鄰居”是什么來頭?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我們不能把這種記憶簡單地視為個體對信仰的一種文化創造,應將其置于鄉村的網絡社會脈絡中重新理解,進而去追求這種記憶背后隱藏的歷史。基于此,筆者持續在該地開展了為期3個月的田野調查,現以第一手資料對上述思考展開敘述。
一、傈僳族皈依基督教及相關成果的解釋
霞若鄉位于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德欽縣東南部,東與茶馬古道的中轉站——奔子欄接壤,北面穿過白茫雪山則是歷史上著名的漢藏貿易要地——升平鎮,西南面視野開闊,與維西傈僳族自治縣連成一片。該鄉平均海拔為2362.6米,年平均溫度在10.7℃,面積1359平方千米,轄霞若、石茸、奪松、月仁、施壩、各磨茸、粗卡通7個行政村,91個村民小組,214個自然村,總人口為8290人,其中傈僳族4394人,藏族3813人,分別占全鄉總人口的53%和36%。①霞若鄉2010年政府統計數據。兩個民族的分布格局比較清晰,藏族多居于平均海拔在2100米的河谷臺地,而傈僳族大多居于平均海拔2400米的高山區老林。地理的分野亦為宗教的分野——藏族信仰藏傳佛教,在海拔2400米以下的房子屋頂上到處可見用磚頭砌成的煨桑爐;傈僳族原本信仰本民族的原始宗教——尼扒,兼有一定的祖先崇拜,但是自1991年②德欽縣民族宗教事務局證實,基督教向霞若鄉傳播始于1991年。但筆者調查發現,實際時間可能要早得多,1991年是傳教士進來傳教的年份,在這之前,已經有不少人皈依基督教,在家里做禮拜。基督教由西南面的維西縣傳播進入到該鄉以后,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成為該鄉傈僳族的“民族宗教”,海拔2400米以上的地方隨處可見用木頭制成的大小十字架掛在房屋頂上。
回顧歷史,基督教在滇西北傳播顯然比向該鄉傳播的時間要早,19世紀末20世紀初,內地會(China Inland Mission,CIM) 的傅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神召會(The Assemblies of God)的馬導民(Clifford Morrison)等傳教士就將基督教傳至云南滇西北傈僳族社會,并分別于20世紀30年代與20世紀80年代兩次達到高潮,信仰的人數劇增。[1]關于傈僳族接受基督教的原因,學術界大致有三種認識:一是從文化、衛生的角度考察,認為早期傳教士采用的“贈醫施藥”[2]213-214與“文字布道”[3]227兩種手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是從政治、歷史的角度考察,將其視為傈僳族受異族與階級雙重壓迫在政治層面做出的反抗;[4]三是從經濟的角度考察,認為傈僳族皈依基督教受工具理性驅使。確切地說,基督教禁酒的教義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他們擺脫貧困的迫切心理,具有幫助他們提高生活質量的功能。[5]
上述三種觀點皆成一家之言,對于解釋具體的、歷史的傈僳族皈依基督教有較強的合理性,但是能否解釋霞若地區與藏族混居的傈僳族接受基督教則需謹慎對待。比如前兩種觀點主要是針對民國時期小聚居,而非大雜居的傈僳族社會(主要針對怒江流域傈僳族聚集區)所面臨的環境而言的,但身在藏區霞若鄉的傈僳族接受基督教卻是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時間要比其他地區的傈僳族接受基督教晚了近1個世紀,這時候的傈僳族社會內部,無論是政治、衛生、文化方面都已經與民國時期大不相同。至于第三種觀點,筆者的田野調查材料證實在一定程度上有說服力,因為對于許多已經皈依基督教的傈僳族而言,喝酒耽誤生產也是他們難以忘卻的歷史記憶之一,其實對照藏族對酒的態度也可以相互印證。目前鄉里的藏族喝酒鬧事的案例比較突出,在筆者做完田野調查離開的前一天晚上,鄉里還發生了因為喝醉酒引發的嚴重刑事案件。事實上,鄉政府大約在2010年針對藏族喝酒的情況組織過一場聲勢浩大的戒酒行動,當時請了活佛為藏民念戒酒經,勸藏民不要喝酒。據說儀式過后的兩三天,確實沒有人敢喝酒,可是時間稍微一長,藏民又忍不住喝了起來。后來民間就開始流傳,說活佛并沒有規定大家不能喝酒,而是說大家不能喝醉。傈僳族信仰基督戒酒成功與藏族信仰藏傳佛教戒酒不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酒并沒有像傈僳族那樣給藏族的生活造成嚴重影響。如果從兩個民族的生產環境去考察,當可發現藏族大多住在海拔較低的地方,占有相當大面積的肥沃水田和干田,水田盛產水稻,糧食充足,干田盛產的苞谷、青稞和大麥,都是釀酒的上好原料。反之,傈僳族山上的坡地只能種雜糧,雜糧大多只能用來煮粥,很少能釀出質量好的酒。因此,藏族總是在筆者的面前炫耀說,藏族家釀的酒喝不完,而傈僳族只能買酒喝。
權且認為“基督教的禁酒教義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傈僳族力圖擺脫貧困的心理”,但是社會是有等級的,同屬于傈僳族,內部也存在貧富差距,所以它實際上回答的是為什么那些貧困的傈僳族接受基督,而不能回答為什么全體傈僳族認可基督。換言之,它只是在部分程度上說明了“為什么”,沒有在整體層面說明“怎么樣”,為學術界沿此思路進一步考察基督教在傈僳族社會內部的傳播網絡留下了空間。
二、民族婚姻:外部基督教向傈僳族社會傳播的途徑
誠如故事揭示的那樣,該地區的基督教傳播可能與婚姻存在某種密切的關聯,有必要先考察該地區傈僳族的婚姻圈。傈僳族目前流行自由婚戀,但其通婚圈相對較小。以施壩村為例,該村有38戶家庭,計194人,平均每戶約為5人。據統計,村中約25%的人口處于前生育年齡階段(0-15歲),其中男26人,女24人,基本持平。而處于生育年齡階段(16-45歲)的人口占58%左右,女的60人,男的57人,女比男多3人。①數據來源:根據筆者的田野調查統計整理。該村的人口統計學表明,無論是在將來還是現在,該地區傈僳族男女比例是平衡的,在適婚年齡階段,不會出現單身家庭。然而,有必要指出,該自然村的38戶家庭是由虎氏、蜂氏和魚氏3個氏族裂變而成的,有些家庭還存在很近的血緣關系,這決定了適婚年齡的男女無法把配偶限制在單個自然村內,通婚圈自然要向村的上一級單位——“鄉”擴展,這勢必遇到與藏族能否結親的問題。田野中的確發現有這樣的事例,但卻往往被當地群眾視為“特殊”。盡管過去幾十年,我國已經實行了民族平等的政策,該鄉兩個民族的關系也還算融洽,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身處整個大藏區的藏族在潛意識中多少還帶有對傈僳族的歧視。在傈僳族的觀念中,藏族往往是不講道理的人,編號為6號、10號、12號的家庭在接受筆者訪問時都一致認為藏族很野蠻,他們說:“我們信基督,是不喝酒的,但藏族無論男女,經常醉酒,最好要躲著他們,女的喝醉酒以后也會打人的,公安也管不了。” 從“公安也管不了”這一句可以看出,藏族的一些所作所為在傈僳族看來很過分,但又無可奈何。難道一個傈僳族人口比藏族人口多的鄉,傈僳族還會被藏族歧視嗎?一名藏族干部卻這樣回答筆者:“你不要以為它冠上傈僳族民族鄉的稱號就說傈僳族多,那只是為了得到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要知道,‘霞若’是藏語的發音,并不是傈僳族語的發音。‘霞’在藏語是‘巖石’的意思;‘若’為‘下方’的意思。”更多的藏族相信傈僳族有“很多下藥害人的巫師”,以下是筆者的報道人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我13歲的那一年路過傈僳族人的家,在那里喝水。水是我從家里自帶的,按理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晚上回到家后我就開始發高燒、肚子痛,脹得像懷孕一樣大,請喇嘛來看都說快要死了。后來我媽媽說我是中了傈僳族下的“蠱”,她去找了傈僳族的“刀巴”幫我做法,那個“刀巴”念了很多咒語,然后往我的肚子吐口水,當時感覺肚臍很辣,還聽到劈里啪啦的聲音,像把蟲子燒死一樣,肚子就好了。②訪問時間:2016年11月3日,地點:霞若鄉奪松村,被訪問人:卓瑪,女,藏族,33歲。
許多藏族對筆者表示,可以到傈僳族的家去做客,但是最好不要吃他們家的酒飯。筆者曾經在許多藏族群眾家做客,入門以后,都能品嘗到主人端過來的酥油茶或青稞酒;筆者也曾經到過一名被藏族視為下藥害人,但現在已經信基督的傈僳族老婦女家做客,她很熱情,但自始至終沒有給筆者遞上一杯酒,這說明她的潛意識已經習慣了這種歧視。
如此一來,要保持本民族人口的繁衍,霞若鄉的傈僳族必須將通婚半徑向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毗鄰的鄉村延伸。近10年的婚姻統計數據表明,16-45歲的傈僳族適婚男女與維西縣毗鄰鄉村通婚的比例占60%。維西傈僳族自治縣是基督教在傈僳族社會傳播的大本營,早在20世紀30年代,美國傳教士莫爾斯就在維西縣成立了“滇藏基督教會”,并將此作為長期傳教的活動據點。仍然以施壩村為個案說明問題:從1991年到1999年10年間,娶進來或者入贅的婚姻共計31例,其中有18例的配偶來自維西縣,占總人數的58%,而來自維西縣的配偶幾乎都是在結婚前就已經是基督教信徒,他(她)們的另一半則在結婚前后改信基督教。可以說,維西縣的基督教向霞若傳播最先依賴的是婚戀網絡。誠然,婚戀固然只是基督教傳播的充分條件,但年輕人如果在戀愛方面受挫折以后,離信教就不遠了,這是因為基督教嚴禁婚前發生性行為,而傈僳族的傳統婚戀文化卻實行“公房制”①公房制:即在傈僳族社會,男女12歲以后被認為屬于成人,可以自由談戀愛。男方通常在自家的田地附近單獨建一個簡陋的房屋作為戀愛的場所,戀愛期間允許發生性關系。。眾所周知,在父權制社會,性的主動權掌握在男子一方,戀愛中的男性多以能和女伴發生性行為為榮,否則他會被人認為沒有本事,而女性多半是“逆來順受”的,甜蜜的背后遺留下的是懷孕、流產、分手等無奈,而這些后果大多由女性承擔,無疑增加了她們身心受傷的幾率,當戀愛過的女性在接觸基督教的男性時自然就有了對比,這就是為什么在婚戀階段,該鄉信仰基督教的青年女性比男性多的原因。當男性在婚戀方面面臨本鄉逐漸轉變為基督徒的女性與維西縣全部是基督徒的女性夾擊時,男性自然也會開始信仰基督教,以下便是一個生動的個案:
25年前,現年48歲的阿木與一幫同齡年輕人到維西縣去“釣姑娘”,期間與時年21歲的姑娘認識。但在后來的進一步交往中,早就皈依基督教的姑娘提出分手,因為她忍受不了對方身上的煙味、酒味和汗味。阿木為了挽回姑娘的心,原本信仰藏傳佛教的他還是下決心戒煙戒酒,為此他還遭遇到在一起玩的藏族朋友的嘲笑。但他堅持每次在兩人約會之前都使用香皂洗澡,使自己的身上散發出一股淡淡的香皂味。日子久了,阿木發現,戒煙、戒酒、洗澡符合現代生活的潮流,在與姑娘結婚當天同時受洗。
三、伙有共耕制:基督教在傈僳族社會內部流動的網絡
前面談的是基督教是怎么來到霞若鄉的,接下來我們分析基督教來到霞若鄉以后又是如何進一步在傈僳族社會內部流動的。在此之前,有必要認識傈僳族傳統的家庭、祖先祭祀和親屬稱謂,因為這種碎片化、原子化的社會結構將決定基督教在該地特有的傳播模式。
傈僳族社會實行一夫一妻制的父權制小家庭,這種核心家庭一般只包括父母和未婚的子女兩代。有多個兒女的,女兒長大以后要出嫁,不能繼承家里的財產(入贅婚除外)。有多個兒子的,大兒子結婚以后按人口比例獲得遠離家里的一部分土地另起房子生活。由于該鄉地廣人稀,家與家之間的距離比較遠,人員的流動性不強,導致近親弟兄分家遷到別處后就很少再聯系,兄弟之間共同的祭祀活動也不多見。但是,如果大哥結婚去世的時候弟弟還未成家的,弟弟有義務娶大哥的妻子入門。在筆者看來,這或許是在通婚圈有限的環境下通過淡化血緣觀念緩沖倫理以解決人口再生產壓力的變通。在改信基督教之前,傈僳族有祖先祭祀,傈僳語稱之為“尼詞底”,但祭祀對象通常只限于二代以內的、自己見過的祖先,屬于一種近祖崇拜,特殊情況下也包含沒有成家就去世的兄弟姐妹,這是傈僳族突出核心小家庭成員的表現。故而,盡管該鄉所有傈僳族的家庭是由十幾個氏族裂變生成的,但氏族之間沒有任何聯系。筆者在田野調查期間問及氏族概念時,許多群眾只表示:“好像聽老人說過,甲家和乙家以前都崇拜某種動物。”在現實生活與勞動生產當中,被認為曾經崇拜共同動物的各個家庭并不會因為這個原因走得更近。與這種家庭結構相對應的是傈僳族的親屬稱謂,它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在橫向上對核心家庭成員實行分類式稱謂,但對與核心家庭成員無血緣關系的外來加入者不區分。舉例如下:家庭內的子女以Ego為中心,無論男性、女性都有排行名,如用阿普、阿得、阿娜、阿妮等,但是對哥哥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統稱“瑪拉”;同理,對于姐姐的丈夫和妹妹的丈夫統稱為“咩武”。二是在縱向上對于與父母同一輩的親屬加予區分,而父母之上的親屬就不再區分。仍然以Ego為中心,父親的哥哥稱為“哦扒”,父親的弟弟稱為“阿塢”,母親的姐姐稱為“哦瑪”,母親的妹妹稱為“瑪有”,但對于父親與母親的父母一輩,即Ego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則統一稱為“阿叭”。[6]這種對核心家庭內成員實行專有稱謂,核心家庭以外的親屬實行概括性稱謂的做法無疑是傈僳族父權制核心家庭、近祖崇拜的思維反映。
傳統漢族鄉村社會的宗族觀念在這些地區并不存在,傈僳族重視核心家庭成員,但在核心家庭以外就不再依據血統的遠近整合人群,那么整個村落的人群整合方式又是如何呢?——那就是通過土地耕作方面實行的“伙有共耕制”。“伙有共耕制”是傈僳族傳統社會固有的一種勞作制度,也是傈僳族在淡化血緣觀念后,在生產力水平低下、勞動力不足的環境中采取的一種土地耕種合作制度。具體形式是兩個以上的家庭共耕一塊土地,采用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甲家出力、乙家出物的形式,也有兩家平均出錢出力的形式,但無論哪一種方式,所得糧食皆平均分配。需要指出的是,“伙有共耕制”并非僅局限于兩個家庭之間,如甲家和乙家實行“伙有共耕制”的同時,也可以根據自身的條件和精力再選擇和丙家實行“伙有共耕”,而實行“伙有共耕”的兩個家庭并非是兄弟各自組成的家庭,而是談得來、處得好的鄰居、朋友。這樣,借著“伙有共耕制”,傈僳族原子化的核心小家庭組成了一張縱橫交錯的網,而最初接受基督教信仰的人很自然就通過這張網向伙伴傳播基督教,因此這張網就是基督教在傈僳族社會內部流動的血脈。下面我們以一些個案說明:O與P是自小一起玩到大的伙伴,O娶了維西縣的姑娘,同時受洗加入基督教會,P則與本村姑娘結婚,但兩人的關系一直很好,所以婚后選擇在一起實行伙有共耕。O信仰基督教,星期天不勞動,但他提前告訴對方,對方認為這是信仰問題,要尊重,所以這不影響雙方的合作。O一直利用機會向對方傳教:“你天天勞動也不見生活就比那些不天天勞動的好,還是要做上帝的孩子,死后可以回上帝的家。”P聽后看看周圍和自己,比較以后也覺得他的話有道理,后來又在他的鼓動下陸續參加了幾次活動,信仰慢慢就發生了轉變,直到受洗。M與基督徒X實行伙有共耕,對方多次給他講加入基督教的好處,M一開始并不理會,但雙方存在勞動合作,不好撕破臉皮,就一直聽他講。后來自己的父親過世了,幫忙的人手少得可憐,但是看到對方家里無論什么事,都有許多信徒去幫忙,就感覺這個組織挺有愛心的。一次,M大病一場并得到X及其教友的幫助后果斷受洗。基督教徒D與B實行伙有共耕,D雖然星期天不從事勞作,但能提前告知對方做好安排,從不失言,而B卻經常酗酒,醉得不省人事,好幾次都耽誤了生產,自己覺得不好意思了,于是決定戒酒,跟著D出入教堂,后來受洗。A與C實行伙有共耕,后來前者信教以后多次向C傳教,但C不為所動,A就認為兩個人性格不合,向對方提出不再實行伙耕制,他希望能找信徒一起合作。由于信徒之間都很團結,A很快就找到了新的伙伴,但是C再找伙伴卻相對困難,過了一段時間,他也加入基督教。
總而言之,傈僳族固有的伙有共耕制是基督教在該地發展的顯著特點,最初皈依基督教的信徒以核心小家庭為中心,三三兩兩在自己的家里進行禮拜,然后利用“伙有共耕制”的網絡渠道向勞動伙伴的核心小家庭傳播,對方家庭接受了基督信仰以后又將基督教傳向與自家實行伙有共耕制的新的核心家庭,使該社會的勞作制度逐漸呈現出基督徒伙有共耕制,其特點是不吸煙不喝酒,安息日不勞動,星期三、星期六晚上做禮拜,不與非信徒通婚。宗教信仰已經成為社會分化的重要指標,信徒的人際關系之拓展和維持建立在宗教的基礎之上形成人際依戀,使信徒傾向于與其所處社會網絡的宗教屬性保持一致。[7]
四、結 論
中國的民間宗教在鄉村社會歷來非常發達,少數民族地區更是如此,楊慶堃曾用“分散性宗教”[8]271-272作為指稱,并認為它與基督教依賴的社會基礎有著本質的區別。近代西方社會中人與人的結合方式是“團體格局”,就像幾根稻草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扎。[9]25在這樣的社會中,它非常有必要創造出一個全能的上帝統領社會。然而,“分散性宗教”所依賴的社會基礎是由傳統的人倫道德維護的“差序格局”[9]27。由于“倫理本位”的社會能讓人在現世人倫關系當中獲得人生的意義滿足,道德代替了宗教。[10]88因此,我們在分析新時期基督教在鄉村社會傳播的時候一方面固然要注意它所運用的手段,但鄉村社會自身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狀態使其得以在內部流動不容忽視。
追根溯源,傈僳族是來自西北古羌族系沿三江并流南下與當地土著融合而形成的,公元8世紀中葉,傈僳族受唐朝、南詔和吐蕃三大勢力的統治,至元、明時期,又分別受麗江納西族木氏土司、金沙江東岸彝族奴隸主的統治。在異族的長期統治和剝削下,不堪兵丁苦役重負的傈僳族進行過多次斗爭,但皆以失敗告終,為了生存,只能不斷往深山老林遷徙。毫不夸張地說,傈僳族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就是一部受異族歧視不斷遷徙的歷史。事實上,長期的遷徙早已使傈僳族的社會結構碎片化,如其對核心家庭內成員實行專有稱謂,對核心家庭以外的親屬實行概括性稱謂正是其社會固守原子化的核心家庭為本,而其他親屬關系松弛易變的表現。但無論如何,人們在這樣的環境中面臨物質資料再生產的困境時是非常渴望集體關懷的,如此一來,才能夠解釋為什么實行一夫一妻制小家庭的傈僳族要同時保留“妻兄弟婚”——這是為了防止缺乏集體主義關照下的單親家庭陷入生活的絕境。但是,迫于物質與人口再生產的壓力需要淡化血緣,需要杜絕聯合家庭和擴大家庭的出現,需要杜絕因共同祖先祭祀而發展起來的宗族組織。在兩難的境地之中和社會自身又無法發展出共同體的情況下,伙有共耕成了他們渴望共同體唯一能夠采取的有效抵御不確定性風險的手段。毋庸置疑,在傳統社會乃至集體主義時代,伙有共耕制帶有“道德”意義上的互助。但自20世紀9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道德”意義上的義務式互助已經逐漸趨于理性——這時候的伙有共耕制不再由“倫理本位”的道德主導,而是基于核心小家庭,依照“經濟人”的原則重新組合。倫理本位的崩塌使得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分散性宗教”走向衰落,準宗教意義上的道德被沖垮了,唯有一個全能的上帝才能將這個碎片化的社會再次凝聚起來——這既是生產生活的需要,也是傈僳族重建傳統互幫互助之道德的需要。因為“西方的教堂,超越所有的村莊和所有的社會群體。在一神的支配之下,教堂的等級制度畫下來就是我們社會學所說的‘society’”。[11]
本文選擇的雖然只是一個地區的個案,但是該個案所折射出的共性拓展了我們的視野:即基督教在霞若鄉以“婚姻—家庭—土地—民族”的鏈鎖進行傳播的模式是否適用于其他地區的傈僳族社會?事實上,在這一鏈鎖中,“婚姻—家庭”只是基督教向霞若鄉傳播的外部途徑,而“土地—民族”才是基督教在霞若鄉內部社會流動的網絡。根據唯物辯證法的原理,外因只是事物發展的條件,內因才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因此,即使“婚姻—家庭”途徑或許只是特例,它不適用于解釋其他地區的傈僳族社會,但是依附于市場經濟背景下的伙有共耕制度而形成的“土地—民族”傳播網絡在整體上卻能夠有效解釋改革開放以來全體傈僳族為什么把基督教當成了本民族的宗教。
[1]黑穎,楊梨.傈僳族基督教信仰的本土化與民族身份認同[J].世界宗教文化,2016(1).
[2]楊學政.云南境內的世界三大宗教[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3]顏思久.云南宗教概況[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1.
[4]高志英.20世紀前半期中緬傈僳族的基督教發展[J].世界宗教文化,2010(6).
[5]盧成仁.體味變化與基督教傳播——怒江傈僳族的田野調查[J].二十一世紀月刊,2011(10).
[6]盧成仁,劉永青.核心家庭與人群結合——云南怒江娃底村傈僳族親屬稱謂研究[J].云南社會科學,2012(3).
[7]阮榮平,鄭鳳田,劉力.宗教信仰選擇——一個西方宗教經濟學的文獻梳理[J].社會,2013(4).
[8]楊慶堃.中國社會中的宗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費孝通.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0]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三卷[M].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
[11]王銘銘,劉鐵梁.村落研究二人談[J].民俗研究,2003(1).
ETHNIC GROUP,MARRIAGE,CO-OWNERSHIP AND CULTIVATION BY SHARERS AND THE GOD:AN INTERPRETATION TO THE EMBEDDEDMENT OF CHRISTIANITY IN THE LISU SOCIETY IN XIARUO TOWNSHIP,DEQIN COUNTY,NORTHWEST YUNNAN
Ye Yuanpiao
The LiSu people in the northwest of Yunnan province chose to believe Christianity from the 1990s,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ethnic living in the atomized and fragmented social structure,facing discrimination of the surrounding people and the multiple pressures of reproduction of population and material goods.Based on investigation to the process of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of the Lisu people in a township,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mode of“marriage–family-landminority” is the network of Christianity spreading to the Lisu society,it can be used to explain why Christianity spreads in the Lisu society with ethnic characteristic,which differs from the Christianity’s growth in the Han society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lineage.
the Lisu people;co-ownership and cultivation by sharers;Christianity
C912.4【文獻識別碼】A
1004-454X(2017)04-0066-006
﹝責任編輯:袁麗紅﹞
【作 者】葉遠飄,廣東醫科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人類學博士。廣東湛江,524003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青川藏滇結合部多元喪俗信仰的宗教人類學研究”(16BZJ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