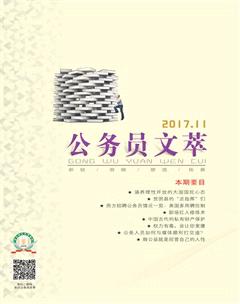貧困縣的“總指揮”們
王軍偉+++甘泉等
扶貧攻堅戰已發起最后的沖鋒,近600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是其中的主戰場。作為一線總指揮的縣委書記們,是決定這場戰役成敗的關鍵因素。
從年初起,《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深入桂豫甘黔等省區20個貧困縣,對10余位縣委書記跟蹤采訪,全天同吃同車同下鄉,記錄下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狀態;同時,記者還對東中西部50位貧困縣縣委書記進行匿名問卷調查,力圖勾勒出這一群體真實的所思所為。
“在我這一任脫貧,我很光榮”
背后是峭壁,眼前是連綿的石山,站在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七百弄鄉的一條山路上,50歲的縣委書記楊龍文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感嘆道:“對貧困如同宿命一樣的七百弄鄉瑤族群眾來說,這輪脫貧攻堅戰是改變命運千年未有之機遇。”
大化縣位于滇黔桂石漠化片區,嚴重缺水缺土的七百弄山區是“中國最貧困的角落”,被聯合國糧農組織認為是“世上除沙漠外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如今,盤山路就像毛細血管一樣正在改變當地的面貌,不少村屯通公路后,新房雨后春筍一般冒了出來,世世代代居住的茅草房、土坯房變成了瓦房、樓房。
“這個地方自古貧困,如今在黨的帶領下修路、搬遷、富民,這里的群眾將擺脫延續了世世代代貧困的命運,這是一件足以寫進縣志的大事。”楊龍文說:“在我這一任脫貧,我很光榮!”
楊龍文的“興奮”并非個例。采訪過程中記者發現,雖然脫貧攻堅是難啃的硬骨頭,但縣委書記們不僅沒有抱怨,反而豪情滿懷。“‘雄心征服千層嶺,壯志壓倒萬重山的都安精神是農業學大寨時期提出來的,幾十年過去了,都安仍有十幾萬貧困人口,一想到將在我這一任實現脫貧目標,我就心潮澎湃。”廣西河池市副市長、都安瑤族自治縣縣委書記陳繼勇躊躇滿志。
受訪縣委書記普遍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貧困縣獲得精準扶貧的投入力度、精度、效度和深度“前所未有”,這些曾經積苦積弱的貧困地區,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這既是貧困群眾改變命運的機遇,也是縣委書記們個人干事創業的重要機遇。
采訪中,《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深切地感受到,在對脫貧攻堅和縣委書記使命的認識上,這個群體有三個特點:一是責任感強,面對當前的脫貧形勢,“寧做忙官不做閑官”;二是對在自己任上擺脫貧困倍感光榮,中部一縣委書記說:“中央這么看重這支隊伍,咱就是累死也心甘”;三是以往追求GDP的政績觀悄然變化,開始真正將共產黨人的事業與自身的人生追求相統一。
“我要讓自己的斗志去感染
整個干部隊伍”
改變貧困面貌的巨大機遇和無限的使命感激發了貧困縣縣委書記干事創業的激情。對于每天的工作狀態,調查問卷顯示,26%的縣委書記選擇“平均每天工作10小時以上”,68%的縣委書記選擇“5+2,白加黑”。
這并非“虛言”。為了更真切地感受貧困縣縣委書記的工作狀態,《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先后對十余名縣委書記進行了全天跟訪,與他們同吃同車同下鄉。結果每天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滿滿當當:早晨六七點天色微曦出門,晚上披星戴月而歸,十一點之前無法休息。記者的采訪本上,也留下了一連串這樣的記錄:
——甘肅省定西市副市長、通渭縣委書記令續鵬2016年下鄉121天,走訪117個村,攢下一份厚達34頁、A4紙打印的《每月發現和解決問題情況匯總》,其中大部分內容是扶貧。
——陳繼勇平均每天開五六個會,白天下鄉調研就晚上開,會議經常開到深夜十一二點,記者兩次采訪陳繼勇,時間都約到了晚上十點之后,結果走進縣委辦公樓,許多辦公室仍然燈火通明。
——河南盧氏縣委書記王清華去年下鄉超過250天。他說:“縣里的干部隊伍任務重、壓力大,作為縣委‘一把手,我要讓自己的斗志去感染整個干部隊伍。”
500多個貧困縣是脫貧攻堅的核心戰場,作為一線總指揮的縣委書記身系戰局成敗。采訪中,有人感慨,“縣委書記相當于團長,但我還要干連長、排長的事兒;對很多事兒不放心,有時還直接做一線戰斗員。甚至需要‘唱黑臉當個激勵士氣、賞罰分明的大刀隊隊長。”
“定了就得干,出了問題我來負責”
脫貧攻堅涉及方方面面,一些政策規定難免滯后,甚至有脫離實際的情況。推進扶貧過程中面對一些棘手問題,尤其是與上級部門的規定不符時,縣委書記需要敲鐘問響、順勢權變地開展工作——風險,是檢驗干部擔當的一面鏡子。
楊龍文曾遇到這樣的情況:按照上級有關部門規定,通村屯扶貧道路坡度要低于10度,但是大化縣的許多石山區山坡陡峭,如果按照低于10度的標準修路成本要增加兩三倍。
《瞭望》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恰逢楊龍文召集相關部門開會商討此事。“按10度以下修沒有錢,按20度修,又怕驗收時不過關,今年任務很重,很多條路都等著開工,書記您要盡快拿主意。”扶貧辦主任說。
經過一番討論,楊龍文最后定調:“扶貧任務這么重,我們不能干等,讓施工隊先動起來,出什么問題我來擔著。同時盡快去上級扶貧部門面對面匯報情況,不要文件來文件去。”
采訪中,不少縣委書記表示,脫貧攻堅事關醫療、教育、民政、交通、農業、財政、金融等方方面面,一些部門的政策規定難免滯后于基層探索,面對這種情況,“一把手”的擔當精神尤為重要。
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縣委書記梁嘉庚上任之初,對自己和當地干部提出了“五不”要求:不爭論、不張揚、不浮躁、不落后、不折騰。他告訴記者:“有些事爭論來爭論去,最后往往還定不下來,我必須擔當,沒有那個時間了,定了就得干,出了問題我來負責。”
“壓力都在主席臺,責任都在前三排”
一次,《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從早上開始跟訪楊龍文,他一整天眉頭緊鎖、悶悶不樂,縣委辦主任也不解其由。晚上書記從全縣養雞業形勢分析會下來,已是夜里10點多,他卻一臉喜色拉著記者陪他去街邊吃點烤羊肉串。縣委辦主任跟記者感慨:“記者同志,書記兩年多從來沒有吃過夜宵,看來今天多虧了你,才這么高興。”endprint
記者了解后才知道,楊龍文之所以高興,不是因為自己,而是因為一個電話。原來,面對全縣貧困地區缺水少土的現狀,從2016年初開始,大化縣大力發展養雞產業,但是今年的H7N9禽流感給當地的養雞業蒙上一層陰影。一旦貧困戶養雞賠了錢,將極大打擊產業扶貧的積極性。因此,楊龍文一直在為銷售發愁,還專門去深圳跑市場。經多方聯系后,就在當天會議間隙,一家企業負責人給他打電話,答應將縣里存欄的雞統一收購、宰殺、冷凍。正是這個電話,讓楊龍文大松了一口氣。
對50名縣委書記壓力程度的問卷調查顯示,66%的人壓力較大、很大,以致“夜不能寐”“如臨深淵”。
壓力主要來自貧困的現實性和艱巨性。不少地區貧困程度深,歷史欠賬多,要找到一條穩定的脫貧之道十分不易。發展扶貧產業是貧困群眾穩定脫貧的根本之策,但貧困地區往往基礎差、底子薄,貧困群眾往往缺技術、少知識,加上市場形勢瞬息萬變,扶貧產業無異于“走蜀道”。問卷調查中80%的縣委書記認為“如期脫貧容易,穩定脫貧不易,全面小康任重道遠”。
陸川縣是廣西2016年預脫貧摘帽的9個縣區之一,經過努力,目前全縣貧困發生率由10.14%降到2.74%,初步實現脫貧摘帽。盡管如此,陸川縣委書記蒙啟鵬絲毫不感覺輕松。“去年我們有6萬多群眾脫貧,這么大的貧困人口數量,如果沒有產業作支撐,很難實現穩定脫貧。”群眾雖然經廣泛動員種植中藥材橘紅,但距離掛果需要三年時間,不能解燃眉之急。
尤其是一些貧困戶內生動力不足,更增加了脫貧的難度。廣西一縣委書記為勸一貧困戶易地搬遷,三次上山登門。事后他感慨:“縣委書記親自做工作還這么難,普通干部可想而知。真是群眾脫貧,干部脫皮。”一些縣委書記告訴記者,隨著脫貧攻堅進入“深水區”,相對物質貧困,精神貧困變得更為突出。
壓力還來自于過于頻繁的各類考核檢查。從問卷統計結果看,64%的縣委書記認為“上級檢查、匯報材料太多,占據基層干部太多精力”。
一些地方干部分析,檢查考核組過多的主要原因是扶貧資金和項目分布在眾多部門,這些部門為了資金安全或推進項目就得層層檢查。“省里檢查市里,市里又加碼,最后全部落到了縣里,檢查組來了,難免占用縣里很大精力。”采訪中,一位縣委書記向《瞭望》新聞周刊記者“訴苦”:“壓力都在主席臺,責任都在前三排。在市里開會縣委書記坐前三排,在縣里開會縣委書記坐主席臺。”
盡管壓力大、困惑也不少,但記者跟訪和問卷調查的50名縣委書記,無一例外都表示有信心按期脫貧摘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