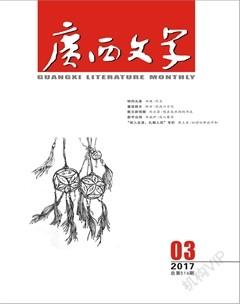趙青云隨筆四題
龐氏陷阱誰之過
猴年春節回老家過年,碰到一臉烏云的鄉下表哥。幾番詢問,得知其剛剛經歷了人生的一次滑鐵盧。表哥在縣城經營商品批發,幾年拼搏下來,積累了不少資本。去年,他與許多人一樣,也經不起誘惑,擠入了民間融資渠道,企圖借此收獲比銀行更高的借貸利息。憑著表哥良好的信譽,不少親戚朋友還都借他之力一起投資。誰知到了八月份,風云突變,那家所謂的P2P公司資金鏈斷裂,不僅無力償還利息,連本金都無法拿回。這年,表哥肯定是過不好了,一生的積累沒了,本想留給大學快畢業的兒子買房的錢沒了,還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一班親朋好友,一向忠厚寡言的表哥,也慢慢出現了一些戾氣。
我且由此聯想起2015年的一系列投資“淪陷”事件:股市暴跌、人民幣貶值,以及民間借貸網絡化后所形成的P2P龐氏騙局。有多少人從小康之家一夜間變成赤貧如洗;有多少人從稍有積蓄變得負債累累;有多少人被打趴下,趴在那里至今沒起來,或許再也起不來。據我所知,光e租寶就非法集資五百多億,涉及投資人九十多萬,還有多少線上的、線下的,大型的、中小型的,城市的、鄉鎮的,各種名義的、各種形式的非法集資平臺,還有多少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深陷其中而損失慘重。這些人,都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逐步培養起來的中產階層,而只用了一年多時間,一大批中產就這樣灰飛煙滅了,甚至連他們自己都沒有反應過來。
也許你可以說這只能怪他們自己,被利益驅使而罔顧風險。但對任何一名享受到國家改革紅利的老百姓來說,想通過各種理財手段來使自己的生活更趨小康,這無可非議,問題是有沒有給予他們一些健康的投資方式,或者說他們的有益投資有沒有得到應有的保障。
金融市場的不健全,無疑會給國民經濟帶來各種損失,其中最大的損失就是中產階層的退化與消失。一個健康穩定而不斷發展的經濟社會,其所依托的中堅力量無疑就是龐大的中產階層。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還是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都少不了一支穩定的中產隊伍在持續發揮作用。而中產一旦被擠壓,最直接的后遺癥便是降低社會經濟的抗擊打能力,使整個經濟體系變得更脆弱,而更為嚴重的是會使經濟體系變得畸形,使百姓對發展失去信心。
如何健全金融體系,培育中產階層,經濟學家們有著各種專業論斷,而從一個比較樸實的角度看,關鍵是要讓每個人都有發展的安全感,有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投資渠道和保障體制。當你身無分文時,你可以堅信通過自己的努力一定能闖出一片天地,而不是無所適從;當你腰纏萬貫時,你可以堅信只要自己奉公守法,就不用擔心一夜之間變成窮光蛋;當你投資時,你可以堅信有著堅強的制度保障,就不會有那么多的忽悠、詐騙和欺壓。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的共同努力,考量各方改革的方向,調整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以及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優化、健全、穩定各方的運作體系,讓政府給人民以信心,讓市場給人民以希望,讓社會給人民以保障,而這才是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亟須解決的問題。
改革進入深水區,就是需要考慮到各方面的改革和改革的各方面,金融不僅是金融,同時也是民生,更是政治,只有把這個深水區趟好了,“表哥”們才能安心地過個好年。
親民與作秀
如今一些官員流行“親民”。毋庸置疑,親民的實質即是為民做事,其落腳點就是社會基層。老百姓可不愛看那種舞臺表現,也不喜歡“光說不練”的天橋把式。站在傳統的角度講,中國的老百姓就喜歡實在,傾心實惠,中意樸實,推崇厚實。他們不僅要聽干部說得怎樣,更要看你做得如何。花拳繡腿不愛看,文過飾非看不慣。
“親民”意識,在中國由來已久。“四書”中之《大學》的第一段話便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楚大夫屈原做到了“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唐詩人白居易則為饑寒中掙扎的百姓而愧疚:“念彼深自愧,自問是何人!”據傳他在杭州為官時,見水患頻發,就竭盡全力搞了修堤工程。離去時百姓夾道歡送,白居易只是平和地以詩作答:“唯留一湖水,與汝渡兇年。”封建社會的這種親民之舉,你也可以說是為了穩固統治階級的政權什么的,但站在官員本身的角度講,實是一種做人的良心所致。
自然,今之親民,就是要以自己扎實的工作去察民之情、體民之苦、排民之憂、解民之難。一個好官員,一名好干部,僅僅不貪不占是不夠的,“兩袖清風”卻是“一事無成”,這樣的行為標準顯然是偏低的。真正的親民者,無疑是全身心地為民眾的幸福美滿建功立業,竭盡全力地為改革發展去逢山開路、遇河架橋。這樣的干部在個人利益上想得很少,在為人民奉獻上則付出甚多。
但現實中仍然有些官員,看似親民,實屬作秀。總是承諾不少,實效不多,即使略有實效,其出發點也僅是做給上面看的。他們的一舉一動,總是讓老百姓有一種吃了“空心湯圓”的感覺,很不爽心。這些善于作秀者,注重的只是自己的名利,考慮的只是個人的得失,盤算的是仕途的升遷,規劃的是親友的利益。他們好出風頭,愛玩花頭,喜趕浪頭,時常為了自己政績的一個雞蛋,而不惜拆毀公家一幢“樓房”。如此做秀,近乎作惡與作孽,實在令人作嘔!這樣的干部和做派與親民為民相去甚遠,因此難免會被老百姓嗤之以鼻,棄之如敝履。是把群眾路線落實到行動上面,還是停留在嘴巴上,按習近平總書記的一句話來說就是:“是不是做秀,老百姓一看就知道。”
親民,就要愛民、敬民,更要為民。要改進領導方式和領導方法,轉變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就要深入到群眾中去,汲取群眾的營養和草根的智慧,進而增朝氣、添底氣、具靈氣,徹底去掉我們身上的“官氣”,從而找出人民群眾真正的民心民意所在,使我們的工作如實地反映群眾意愿,避免工作的盲目性和片面性。聽民聲,不僅要認真了解群眾的意愿和要求,還要能夠聽得進群眾的“牢騷話”和“刺耳話”,正所謂忠言逆耳良藥苦口。察民情,就要眼睛向下,多看“群眾臉色”,仔細體察群眾的情緒。總之,一切站在人民群眾的利益上想問題,講出群眾所想的,干出群眾所盼的,糾正群眾所怨的。做到不作秀,不作弊,遠離作孽與作惡。不以“施舍者”自榜,不搞“面子工程”“政績工程”,真正履行好“公仆”的權利與義務。
前進中的中華民族杜絕平庸虛偽,需要真抓實干。要做到實實在在的親民,就是要順應民心,重視民意,將“民眾是否快樂”作為工作的標準,就要努力聽民聲、維民權、解民難。多聽民聲,便于早發現問題;多聽民聲,利于早解決矛盾。這就要求手握權力的干部,全面轉變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深入基層,深入一線,暢通便民訴求的“綠色通道”。只有滿腔熱忱地為群眾做好事、辦實事,才能真正確保社會和諧、百姓安居樂業。
痛與通
中醫有曰:痛則不通,通則不痛。倘若將此話延伸開來,我倒覺得這世上最難通的,恐怕就是政令吧。
政令不暢通,亦即上行下不效。如上有要求,下不執行;上有命令,下不服從;上有指示,下不落實。而其具體表現則是陽奉陰違與見機行事相結合,你若來真動硬,他便俯首諂媚;你若風吹楊柳,他便恣意橫行。頗有“敵進我退,敵疲我擾”的戰術。只打自己的小算盤,只算自己的小九九。正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有些個領導干部也確實聰明,不管上面出什么政策,總能找到應對的辦法。即便在全面從嚴治黨的今天,隨著監督手段的不斷加強,應對的方式也在不斷變換花樣。他們求穩,手段更高明、更隱蔽、更不易被發現;求小,即便是被發現了,也動不了筋骨,無傷大雅;求通,搞土政策,打擦邊球,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總能找出一大堆理由來遮掩、來推卸。“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執行中央精神”“結合本地特色,讓上級精神落地”“因地制宜,尊重基層創新發展”等,在這些借口下搞變通,鉆空子,塞進地方主義、本位主義的私貨,利用政策執行和政策檢查中的不完善之處,使不執行政令有了“合法性”。
造成政令不暢通,其原因無非就是利益。當地方政府利益與中央利益有沖突時,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有沖突時,有利于地區、單位的內容就落實、照辦;維護整體利益、要求做出某些犧牲的內容就擱置、舍棄,使政令變得支離破碎,甚至歪曲精神實質。于是,執行上級的政策就變成了一個虛假的形式和過程,通常是新瓶裝舊酒,管你風起云涌,我自巋然不動。
說到底,這是自由主義的一種具體表現。更有甚者,還覺得自己處處比中央聰明。在他們眼中,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法律、法規、條例和制度都是可以鎖進抽屜里的。做,或者不做,他們都有辦法做到“依法依規”。更要命的是,這些干部在不把中央和上級要求當回事的同時,卻又在自己的領域制造出特有的“政治紀律”,于是違反上級要求沒人管沒人問,違反了他們的要求就要被砸飯碗,甚至是死無葬身之地。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就揣著“這里是老子的天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這一切,無疑是政令不暢的梗阻所在。
不通之痛,如何解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肯定不行。若以西醫治之,當全面檢查身體各項指標:政策的出臺是否符合實際,有沒有成為個別部門利益的收納盒,是否便于下級或者基層的操作與落實;權力的分配、制約和監督機制是否完善,集權與分權是否有利于政策的落實;信息的傳達與共享是否到位;班子配備、干部素養,特別是一把手的政治覺悟是否達到要求,有沒有過于重能輕德,弱化了干部“三觀”這個總開關等。然后再分而治之,該手術的手術、該切除的切除、該化療的化療,力求藥到病除。
若以中醫療之,當以氣養身。下令者和執行者的目標要一致,都是為民族的發展,為人民的福祉,而不是為了實現和維護本級利益,只要保證政令本身代表了民眾利益,而執行者亦是真心用這些政策為民眾謀福利,則打通了任督二脈,其他一切問題,都一通了之。
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必答題,不是選擇題。如果各吹各的號,各唱各的調,政令不通,難達人和,損害的是中央權威、人民利益,黨和政府的形象,全面深化改革的發展大計也就變成了鏡中花、水中月了。
玩“飄”者戒
年輕人的街舞中有一種形式稱為“飄浮”,其步輕盈,飄然如行走云端,給人以空靈之感。而在時下官場,也有一種作風叫“飄浮”,玩的卻是另類的腐敗藝術,讓老百姓很是厭煩。俗話說,官員的檔案在百姓心中。老百姓最忌恨說話輕飄飄,辦事風飄飄,做了一丁點事就飄飄然的人。
史上因做事飄浮而誤大事者多矣。戰國有趙括者,不求實干,卻崇尚理論至上,只把紙上文章做得花哨,結果長平一戰,兵敗如山倒,強盛的趙國也因此踏上了下坡路,同時中華詞典上也就多了一條“紙上談兵”的成語。三國的馬謖也是以飄出名,底氣不夠信心超然,僅憑良好的自我感覺為人做事,結果要隘失守,將蜀國拖入了被動,也丟掉了自己的腦袋,同時中國的戲劇史上也多了一出百看不厭的《失街亭》的經典曲目。
回頭再看如今的官場,飄浮者仍不在少數,而且飄得更為華麗與醒目。所謂官僚主義也好,形式主義也罷,都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有的官員權力攥得很緊,責任推得很遠。他們下基層進村不入戶,隔著汽車玻璃看,等著材料送上來。還有的喜歡爭名,不愛實干,常常是當著人前拍胸脯,事后總是撣屁股。這些人總是把功勞歸于自己,將不足推給別人,談思路頭頭是道,落實工作卻是躲得遠遠,正所謂措施一條條,豪言一串串,官話一套套,到頭來全是圖門面裝裝樣子而已。所有這些“飄技”,說到底就是耍小聰明,花樣再多,卻萬變不離其宗,都是無求真務實之心,僅靠嘩眾取寵取勝。因此說他們是“飄官”,一點也不為過。
這些玩飄者似乎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怕苦怕累,心態浮躁。他們忘記了認識來自實踐的道理,以致工作作風出了偏差,在思想作風上他們又忘了群眾是老師,實踐是課堂,所以工作上就成了“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漂浮,無疑是求真務實的大敵,是奮發進取的路障。其華而不實的做法,顯然是與腳踏實地、真抓實干背道而馳。我們要戒輕飄,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弘揚求真務實的作風。不能光談不做,不能崇尚空談。對于有的人急于出名掛號,不是扎扎實實在抓落實上下功夫,搞一些形式主義的行為,我們就要有措施治之,決不能給那些整天飄飄蕩蕩、不干實事、搞“花架子”的人以任何好處。不然,一些人就自以為得計,“飄”得更高更遠。作為領導干部來說,應該視“飄浮”為恥,崇尚實干,真抓實干,這才是良好精神狀態的落腳點。如果只重“唱功”,不屑“做功”,不思作為,總愛作秀,只圖表面,不求內質,干工作搖搖擺擺,做事情飄飄蕩蕩,再好的路線方針政策也會變成一紙空文。這樣的“飄浮”者,如果委以重任,就難免會像趙括或馬謖之流,誤了我們國家的大事、要事。
作者簡介:趙青云,浙江溫州人,復旦大學哲學博士、高級工程師。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浙江省雜文學會副會長,中國作家書畫院浙江分院副院長,《半月談》專欄作家。出版雜文集《清風云語》、學術著作《卡爾·柯爾施的馬克思主義觀探要》《趙青云書法作品集》,編著《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畫冊》《走向新世紀現代企業黨組織》《溫州港發展戰略研究》《甌跡》《甌饈》等。雜文榮獲第一屆全國魯迅雜文獎金獎、浙江省第一屆魯迅雜文獎金獎、全國“克服‘四風 ”征文活動大獎賽特等獎,“云瀾灣杯”全國第四屆魯迅雜文大獎賽特等獎。
內刊選粹責任編輯 韋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