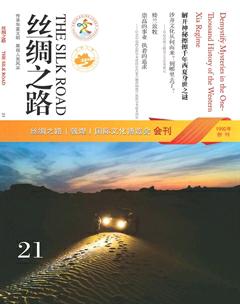海上絲綢之路的蘇祿往事
梁二平
2016年10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到訪的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進行了會談,談到中菲關系的未來發展時,習近平主席提出,要加強政治互信、開展務實合作、推動民間往來、加強地區和多邊事務合作。習主席在說到民間往來時,就提到了一個人——蘇祿王。次日發表的中菲聯合聲明中也提到,“2017年是蘇祿蘇丹訪華600周年”。那么蘇祿國在何方?蘇祿蘇丹又是何許人?這段歷史承載著中菲兩國友好交往什么樣的共同回憶呢?
鄭和下西洋與蘇祿國
燕王朱棣奪權登基后,第一個大動作就是派艦隊“下西洋”,告訴天下,大明換了新皇帝。
所謂“西洋”,元大德八年(1304)的《南海志》是迄今所知最早同時提及“東洋”“西洋”的著作。依該書所記,元代的“東洋”“西洋”應以中國雷州半島—加里曼丹島西岸—巽他海峽為分界線。其東邊的海域為“東洋”,爪哇島﹑加里曼丹島南部﹑蘇拉威西島﹑帝汶島直至馬魯古群島一帶被稱為“大東洋”,加里曼丹島北部至菲律賓群島被稱為“小東洋”;其西邊的為“西洋”,其中又以馬六甲海峽為界,其西為“大西洋”,東為“小西洋”。實際上,明代多數時候把東洋、西洋統稱為“南海”,“南洋”是明嘉靖年間才出現的說法。
鄭和下西洋身負兩個重要任務,一是出洋巡游告訴天下,大明皇帝已是永樂帝了,二是尋找逃出金陵的建文帝。公元1390年,菲律賓蘇祿群島建立了其歷史上的第一個國家——蘇祿蘇丹國。由于獨特的地理位置,蘇祿國是中國通往東洋和南洋的交通樞紐,更是中國海上貿易的重要節點。絲綢、瓷器、鐵器之類物品從中國運往蘇祿,香料、珍珠、藥材等物從蘇祿運回中國。從公元1405年開始的“鄭和下西洋”,船隊曾于1409年訪問過蘇祿國。據傳,鄭和曾與蘇祿東王會面,蘇祿東王對強大的明王朝十分傾慕。于是,有了帶領蘇祿另兩位國王一同前往中國朝貢的想法。
明永樂十五年(1417),蘇祿東國首領巴都葛叭哈剌、西國首領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國首領叭都葛巴剌卜組成的三王使團訪問明王朝,這實際上是對鄭和訪問蘇祿的回訪。使團在南海望岸而行,途經渤泥(今文萊)、滿剌加(今馬六甲)、真臘(今柬埔寨)和占城(今越南中部和南部地區),歷經三個多月航程,于七月到達泉州,稍作休整后,又一路北上,而后進入京杭大運河至北京。一路上,地方政府按朝廷指令,以國賓禮遇接待這個340余人的龐大使團。《明史》記載了蘇祿三王到北京后與明永樂帝朱棣互換國禮的場景。三王向大明皇帝“進金縷表文,獻珍珠、寶石、玳瑁諸物”,朱棣以“印誥、襲衣、冠帶及鞍馬、儀仗器物”還禮。蘇祿使團在北京逗留27天,后踏上歸途。
九月,蘇祿使團的船隊沿大運河行至山東德州安陵時,東王巴都葛叭哈剌突患急癥,不幸殞歿。
訃告到京,明成祖朱棣深為哀悼,即派禮部郎中陳世啟赴德州安德水管驛,按照伊斯蘭教的習俗,為東王舉行了隆重的葬禮,謚曰:恭定,并在德州城北十二連城九江營的西南部,為其修建了蘇祿王墓。
拜謁德州蘇祿王墓
借參加2017年中國博物館協會航海博物館專業委員會的聊城年會,我與深圳大學海洋藝術中心的張巖鑫主任從聊城驅車北上,跑了100多公里,來到德州拜謁蘇祿王墓。墓園在城郊,離運河不遠。這里曾被人們稱為蘇祿王墓、蘇祿王御園,現在是蘇祿文化博物館。園區有一條長長的神道,兩邊蒼松翠柏,郁郁蔥蔥,兩邊立著石人、石獸。神道中央有一高大的石牌坊。
在神道邊可以看到灰色磚砌的“御碑樓”,里面是永樂十六年(1418)的“御制蘇祿國東王碑”。當年,明成祖朱棣親自為蘇祿東王撰寫了碑文。現在碑文已難以辨認,文獻上記載,永樂帝贊譽蘇祿東王“聰明特達,超出等倫”。
進得儀門,是祾恩門,而后是正殿與東、西配殿。正殿正中,高懸著蘇祿東王的巨幅畫像,畫中的東王著一身龍袍。顯然,生前他是不會穿龍袍的,卻不知死后這畫像依據什么為他穿上了龍袍。后院是蘇祿王墓園,正中是一個碩大的圓頂土冢,墓前有一高大石碑,上書“蘇祿國恭定王墓”。這是后來復建的碑,原碑尚不及它一半大,且字跡也不如現在的規整大氣。與其他王陵不同的是,墓園旁還有一個建筑規整的清真寺。因東王后裔信仰伊斯蘭教,明萬歷年間(1573~1620),北營村蘇祿王的后裔和附近的穆斯林群眾共同捐資興建了一座清真寺,名為北營清真寺,并由溫、安二姓各選一人對其進行管理,負責宗教事務。明崇禎元年(1628)九月二十日,明廷頒發“札符”,任命溫守孝為清真寺的掌教。
蘇祿王墓園東南側,還有三座土冢,分別是其王妃、二子溫哈喇與三子安德魯之墓。當年,永樂帝曾勸諭東王長子都馬含與西王、峒王一起回國,同意東王妃葛木寧、次子溫哈喇、三子安德魯及侍從共10人留居中國,居喪三年。永樂二十二年(1424),明朝政府派人護送王妃葛木寧回國。由于對東王的眷戀,她于次年又返回德州城,從此再未離開,與兩位王子長期留居在了德州城,去世后也葬在這里。
明朝皇帝對守蘇祿東王墓的東王后裔非常照顧,不僅賜田免稅,且由德州官倉供給守墓的王室家人每人每月口糧一石,以及布匹、銀鈔等,還“恩賜十二連城祭田三頃三十八畝,永不起科”。清朝初期,朝廷也對蘇祿東王的后裔給予了特殊照顧。
我們走進正門,問看門的兩個中年人是不是蘇祿王后人,他們一致否認,說蘇祿王后人有兩大姓,一姓溫,一姓安。走進展廳才明白,這兩個姓氏分別取自二子溫哈喇與三子安德魯的首字,漢化為姓。蘇祿王后人的名字也很有漢語的味道,如展廳中就有蘇祿王第十六世孫溫守齡與菲律賓駐華大使在東王墓前的合影,其名“守齡”顯然取的是“守陵”之諧音。
清代,根據留居德州城的東王第八代孫溫崇凱、安汝奇提出的“本國遠隔重洋”,要求加入中國籍的請求,清朝廷禮部同意東王的后裔以溫、安二姓入籍德州,同時規定:“溫、安二姓各立奉祀生一名,照山東省先圣先賢子孫之例……嫡裔承襲。”并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發給永久性執照。清乾隆年間,蘇祿東王的后裔們也和其他同袍一樣,參加了朝廷的科考,通過科考涌現了不少棟梁之才。endprint
在展廳中可以看到蘇祿王后人中的杰出人物事跡介紹。溫姓之后人,有的當過知縣、知府,甚至成為朝廷的正四品大員。安姓之后人,在民國時期,其第十五代孫安樹德參加了馮玉祥的部隊,后來成為將級軍官。
“要想富,須往貓里務”
考察之前,我特意觀看了1986年中菲兩國合拍的大型歷史傳奇故事片《蘇祿國王與中國皇帝》。電影開頭是一位中國張姓造船工匠幫蘇祿人造遠洋大船,這故事可能是編劇蘇叔陽想出來的,但中國造船技術引領東洋、西洋或南洋航海和貿易是不爭的歷史事實。
明朝時,在中國東南沿海就流行著這樣一句話:“要想富,須往貓里務。”貓里務位于今菲律賓群島南部某島,至于具體是指哪個島,各種說法不一。但可以確定的是,當時那里貿易發達,商機很多。同時也說明,當時的中菲民間貿易往來已經發展到相對細化和系統的階段。
《閩書》記載,番薯傳入中國的時間在明萬歷年間(1573~1620),最早是由旅居呂宋的福建華人引入福建,后廣泛種植于中國南方各地。番薯耐寒、耐澇、耐堿,在中國并沒有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史書記載,明朝時番薯種植的畝產量遠高于水稻,對增加人口、應付天災等發揮了重要作用。除紅薯以外,拉丁美洲的一些經濟作物也經由菲律賓傳入中國,如煙草、菠蘿、西葫蘆等。
明朝后,不少福建籍商人留居菲律賓,史料留下的記載頗多。有史料寫道,呂宋國(今菲律賓島馬尼拉一帶)“去漳為近,故賈舶多往”。《明史》記載:“閩人以其地近,且饒富商,販者至數萬人,往往久居不返,至長子孫。”
中國人定居菲律賓,開展跨洋貿易,極大程度地帶動了當地的商業,并且與當地人相處融洽,所以也吸引了這里的蘇祿政權對中華文明的向往。蘇祿三王來訪大明之后,到了清代,蘇祿仍與中國保持往來。清雍正四年(1726),蘇祿蘇丹派使者來到中國向清廷“朝貢”,重建了與中國的“藩屬”關系;雍正九年(1731),蘇祿蘇丹親自“來朝”,并拜謁了蘇祿東王墓;乾隆十八年(1753),蘇祿蘇丹國弱不敵強,被西班牙百般欺凌,希望依托中國,尋求庇護,曾向清廷上呈《請奉納版圖表文》。
考察時,蘇祿東王墓正在進行修繕,眾所周知,2016年10月21日發表的中菲聯合聲明稱:“雙方重視兩國人員往來,注意到2017年是蘇祿蘇丹訪華600周年,愿舉辦雙邊紀念活動。”相信中菲兩國將以此為契機,續寫新的海上絲綢之路故事。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