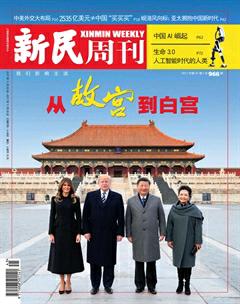稻谷守夜人
別墅區的南邊是一條尚未打通的路,叫蔡家浜東路,原先冷寂得很,但最近忽然熱鬧了起來,一個早晨醒來,發現它已經渾身金光閃閃——無數金黃的稻谷把它的右側鋪成了一條長達兩公里的“黃金大道”。
秋收了。新收的稻谷必須曬場。因為是“斷頭路”,出于對農民利益的“一過性照顧”,交警對“黃金大道”眼開眼閉。
那晚8點以后我們外出散步,已經立冬,松江泗涇的秋野蒹葭蒼蒼,白露茫茫,初冬的田野已肅殺,不遠處的人行道上赫然可見一頂北風中掙扎的帳篷。
不,只是大幅的塑料布用繩索牽成一個窩棚,南粵人叫“寮”,上海人叫做“披”而已,一個老者裹著被子,蜷縮在那里,頭旁是一堆泡沫碗具,盒飯的痕跡宛然,腳跟是一瓶喝剩的“五糧醇”,殘肴狼藉,地鋪前是一雙泥痕斑斑的鞋,一雙布絲模糊的襪子趿拉在鞋幫上,路燈照著他疲憊不堪的臉而鼾聲如雷。我們輕輕咳嗽了一下,他就驚醒了,迅速抬起頭來:什么人?!
我們只是吃驚,怎么現在還有如此落魄的流浪露宿者?他看出了我們的疑惑,說,我是看守稻谷的。“必須通宵守在這里嗎?”我們問。畢竟已立冬,呼嘯的北風把塑料窩棚吹得咔咔震響,毫無保暖的可能,蜷縮在內,等于露天。
被我們吵醒了,他干脆和我們聊天,自謂姓楊,今年六十歲了,松江區泗涇鎮人,包租了26畝地,辛苦了一年,稻谷收上來了,得趕緊曬干,否則一受潮,霉啦!
但是,為什么要冒著寒冷守夜呢?難道還有人會偷盜?老楊見問直搖頭,嘆口氣說,你們城里人很多事不知道。第一,最怕下雨,一下雨,哪怕是半夜或凌晨,我必須緊急“攏稻”,把它們堆成一堆,蓋上防雨油布。第二,稻谷曬在這里,最怕車碾,我們只曬了半邊路,不少轎車根本不管我們死活,明明有路,還是往稻谷上壓過去,一些人甚至故意的,壓的時候,伸出頭來哈哈大笑。夜深的時候,我們主要防止重型車輛的碾壓,整夜間我的耳朵都豎著……說到這里他竟然眼睛紅了:我知道違反交通法,公路不能曬糧食。但是交規的執行也允許一定的“人情味”吧,類似的“斷頭路”,只要不影響行車,是否可以大家照顧一下,一年365天,就這么兩三天。
“第三,守夜的確防盜”,老楊說,你別奇怪,稻谷都有人偷——雞鴨鵝,一吃稻谷就長膘,產蛋量也增加,所以他們偷起來,都是機動車,鏟了就跑。
“為什么不去打谷場曬稻谷呢?”我們問。“現在哪里還有什么打谷場呢?”老楊苦著臉,可以去烘干稻谷,但是第一,烘干的糧食就不香了,而且殼皮繃緊,再加工耗損很大;第二,烘1斤,就得付1角2分,我這里兩萬多斤,就得交付兩千多元,烘不起啊!
自古都有“谷賤傷農”的說法,由此我們轉入了種稻的利潤探討。
他的稻種叫“南粳46號”,種子費每斤1.6元;包租費,每畝500元;肥料,每畝200元;請人機耕,每畝105元;農藥,每畝115元;電灌費,每畝50元;收割費,每畝100元。為確保口感香軟,還得每畝加施雞糞一類的有機肥,還有脫粒費、碾米費……這樣,每斤大米的成本就在3元以上,我的商品價是4元1斤,那么我每斤其實1元都賺不到,26畝包租田,一年下來也就賺個一兩萬元,成本這么高,所以我必須守夜,輸不起啊!
對自己的新大米,老楊相當自信,吃口既軟又香,“不造假、不摻陳米、不摻劣米,做成的飯冷了,還是柔軟的,你米缸里放上十個月,口感不會壞”!
夜已很深。老楊的聲音越來越啞。他將在此苦熬四天。
但愿明天是個大晴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