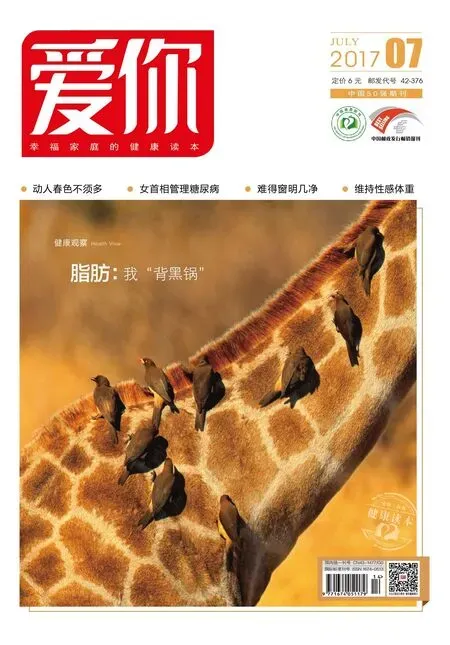續
2017-11-24 16:26:38曉蔣
愛你 2017年20期
關鍵詞:美麗
曉 蔣
續
曉 蔣
直到我做了母親,才發現自己居然和媽媽一模一樣:留意的是兒子的性情與思想,至于他能認多少字,加減法能算到幾位數,真的不怎么關心。
很快,我就因此挨了一記悶棍。從兒子上一年級開始,我就不斷接到老師的電話。兒子的關注點總和別的孩子不同,還經常冒出與語文老師不一致的想法。考卷里要求把詞語連成句子,他不能理解為什么只有“我送給媽媽一張美麗的卡片”是對的,“我送給美麗的媽媽一張卡片”就錯了。題目問喜不喜歡梅蘭芳,他偏偏回答“不喜歡”。我企圖開導他,只要是正面人物,一般都應該回答“喜歡”,但兒子固執地說,明明問的是“喜不喜歡”,意思是可以喜歡,也可以不喜歡。
我終于找到了癥結:我從小告訴他事物有多面性,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但在一座三線小城的普通小學里,大多數老師都認為權威是必須維護的,家長也只能合謀。我告訴兒子:“你有想法可以回家跟媽媽說,不要在學校里說。老師很辛苦,你想證明自己,只能提高分數……”我不停地妥協,不想看到他成為另類。
我決定陪孩子寫作業。可別扭地過了兩年,我心力交瘁。
二年級暑假時,我沒有把兒子關起來做卷子,一家人開車去郊區游玩。三年級暑假時,我們又去看青海湖。
教育還得教學生怎么生活。代際傳承延續了家族的思維方式以及前人古拙的價值取向。有些東西會流失在時間的河流里,有些東西則會一路蜿蜒至海洋。
(摘自《37°女人》2017年第4期 圖/筱竹)
猜你喜歡
歌海(2021年6期)2021-02-01 11:27:18
中國化妝品(2020年9期)2020-10-09 08:58:18
中學生百科·大語文(2020年2期)2020-01-13 05:01:19
作文評點報·低幼版(2019年45期)2019-12-30 09:39:32
學苑創造·A版(2017年6期)2017-06-23 10:10:38
幼兒教育·父母孩子版(2017年4期)2017-06-13 05:41:24
學苑創造·A版(2017年3期)2017-04-27 22:30:42
小溪流(畫刊)(2016年11期)2017-01-05 12:30:06
娃娃樂園·3-7歲綜合智能(2016年4期)2016-10-24 09:35:39
Coco薇(2015年12期)2015-12-10 02:3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