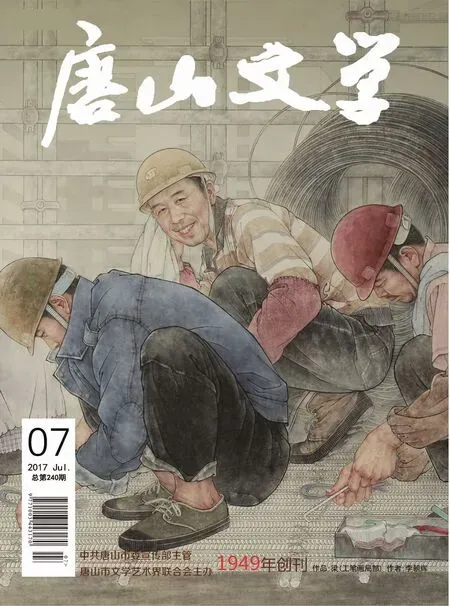淺論地域文化對劉震云鄉土小說創作的影響
◎原 雨
淺論地域文化對劉震云鄉土小說創作的影響
◎原 雨
地域文化對作家的創作個性有著重要的影響。河南作家劉震云的鄉土小說中帶著鮮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多方面、多層次地體現了河南鄉村世界的人情世故以及廣闊土地下巨大的歷史滄桑。
《管子·水地》篇中認為一方水土會產生一方人的氣質、精神。因此在研究一個作家的文學創作時,一定要關注他成長的自然地域環境,還要關注該地域的文化風俗、社會歷史等方面。劉震云是土生土長的河南人。他的作品如《瓜地一夜》《栽花的小樓》《故鄉天下黃花》《故鄉面和花朵》一系列反映故鄉河南人民生活圖景的小說自然包含著博大精深又獨具特色的河南地域文化色彩。本文從物質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三方面闡述其鄉土小說所蘊含的地域文化,進一步了解河南的地域文化對劉震云鄉土小說的影響。
一、地域物質文化與原鄉意識
河南地處中原,地勢平坦、土壤肥沃,物產豐饒,農業是其物質文化的基礎,農業文化是其地域文化的基本基調。從中原的歷史發展過程來看,黃土地與人民百姓緊密相連,孕育了這一空間上獨特的土地文化。也使得農村生活的留戀和追懷成為文學的重要主題。但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大潮的推行,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化,人們在逃離物質貧困、精神匱乏的地域故鄉之后,人們試圖在精神返鄉中找尋靈魂的安身立命之處。劉震云的鄉土小說中,正蘊含著這兩種矛盾的心理。他的作品,正是通過關注農民命運,尤其是在經濟大潮中小人物的生活來體現矛盾所在。比如《塔鋪》中就寫了兩代農民的現實境遇。父親在得知“我”要參加高考時,并未全力支持,但是一本來之不易的世界地理書寄托了父親的期望;“我”不甘農民出身,不甘家庭貧困,渴望通過知識改變命運。劉震云的視點集中在這些人物上,著力描寫農民的心靈創傷及對土地的愛戀,他一次次加倍放大顯示故鄉中苦難的內容,深刻表現對故土的愛戀,同時,又夾雜著對故鄉的不滿。
二、地域精神文化與苦難書寫
河南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其精神文化包含著很多內涵。首先,表現在注重傳統的倫理道德和文化教養。它所倡導的是爭做具有良好道德良知和高尚道德實踐的君子,同時也要求君子包含對苦難的包容,對艱辛的隱忍。其次,在歷史上,作為王朝建國建都的中心,嚴苛的管理和忍讓大度精神加深了百姓的臣服心理,體現出更多的是對苦難的不反抗。劉震云對于這些刻骨銘心的生活苦難,頗為關注。他的新歷史主義小說《一九四二》中,展現抗日戰爭中,一方面面臨著自然災害的傷害,百姓掙扎在死亡的生死線上,過著饑餓煎熬的生活;一方面蔣介石作為當時的領導人,無視普通老百姓的生命,急于國家大事,讓百姓交軍馬繳納飼料。雙重的夾擊使苦難成為時代的特征。劉震云自稱:“這些慌亂下賤的災民的后裔”認為自己有責任有義務去回顧那一段獨具苦難的歷史。除此之外還有對于戰爭,對于大遷徙,對于文革,這些被苦難無情摧毀的生命,被苦難重壓下的底層人物都成了他寫作的素材,成為他同情的對象。他的鄉土小說既寫出了歷史苦難,又寫出了大多數人所忽略的社會現實苦難。
三、地域制度文化與權力崇拜
河南古代是軍事要塞,現代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擁有權力對于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是生活的最大優勢。因此權力的爭奪在這塊土地上歷代更迭,循環上演,也形成強烈的“官本位”意識。劉震云在長期的制度文化中成長起來,更能體會到飽受社會苦難,處在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對于權力的既敬畏又熱衷的心態。其實,不光光是權力,權力所帶來的金錢和裙帶關系,是他們認為的人生路上的絕對通行證。這也造成了有人為了獲取權力,不顧禮義廉恥,不顧仁義道德,成為金錢權力的奴隸。劉震云曾說:“我的故鄉是很看不起我的,故鄉的人們以為我出門在外這么多年,原本應該混了個青年作家。在我們國度里,你是否混得好,要看你的地位,地位就是一切身份。而做沒做官,做多大官,是和地位有密切聯系的。大家全都怕官,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怕。”這段話深刻闡述了中原民眾對于權力的熱烈追求。劉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蓮》塑造了一段因權力干預而長達二十年訴訟的案件,主人公李金蓮的青春和人生也因此被消磨殆盡。還有小說《故鄉天下黃花》中塑造了由爭奪權力而引發矛盾的孫老元、李老喜兩大家族,還有許布袋、李老喜等人對于權力熱烈的追求,他們在利欲熏心的權力腐蝕下也都失去了人性底線。劉震云通過文字淋漓盡致地表現鄉村民間的生命狀態,深刻表現對權力和生命喪生的失望。
河南作家劉震云,作為中原文化的吸收者和展示者,他的鄉土小說是對中原地域文化呈現、反思、審美的標本。他將故鄉的生存圖景展現在文字筆端,立足于民間,著眼于百姓,記錄著中原鄉村大地上民間的悲喜劇。作家將地域文化和文學作品相互融合,體現著作者的人文關懷和文化價值,展現豐富的多彩的河南社會生活圖景。
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文學院 73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