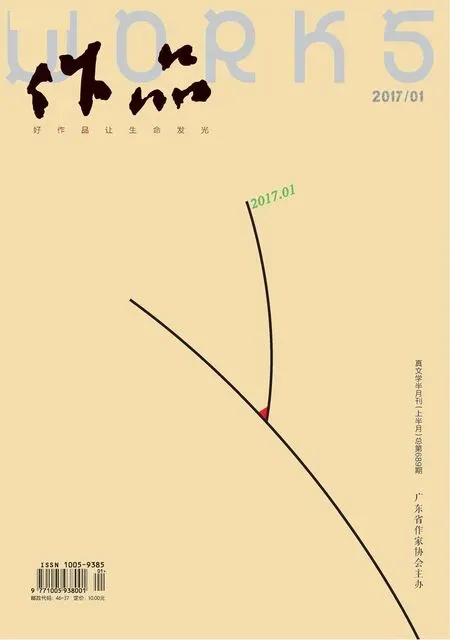靈感
文/殘 雪
靈感
文/殘 雪
殘 雪原名鄧小華,原籍湖南耒陽,1953年生于長沙,當過赤腳醫生,工人,開過裁縫店。1985年開始發表作品,至今已有六百多萬字,她的實驗小說和文學評論在國內外均有較大影響。小說代表作有短篇《山上的小屋》,中篇《黃泥街》《蒼老的浮云》 《痕》 《民工團》,長篇《五香街》 《最后的情人》 《新世紀愛情故事》等。這些小說都被翻譯成多種外文出版了。
征在青年時代沒有干過什么像樣的工作。他一般都是打零工,不論什么工作都做不長。這是因為他除了愛寫詩,做其它的工作都不專心。即使是寫詩,他也不屬于一鼓作氣、努力追求的那種類型,而是有點猶疑,有點缺乏自信,對自己又比較苛求的那一類。所以他的作品的產量極低,也不可能以寫作謀生。可悲的是,他一旦從事別的工作,寫作起來就更為困難了,他的注意力很難集中。于是征為了寫作,便盡量地不去做別的工作,并且減少消費,成日里躲在家中或坐在圖書館里冥思苦想,并且拼命閱讀。雖然寫得少,征的詩歌在同行的小圈子里還是有相當高的評價。有時候,他一年才寫一首小詩。他認為自己還沒有成熟。近年來,征不再寫詩,改為寫短篇小說,他覺得寫小說更順手,所以他的寫作態度正在逐漸變得積極。征的轉變有一些決定性的外力在起作用,除了好友晚儀對他一貫的鼓勵和影響之外,文學女王戴姨在提升他的品位方面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戴姨看出征的潛力之后,便鼓勵他去找一份體力勞動的工作。于是征成了碼頭的裝卸工。這個工作很繁重,而征在這之前是個懶懶散散的人,一開始他很吃不消。但他終于咬牙挺了過來。不過征只在碼頭干半天,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是他的創作時間。這樣堅持了五個月之后,征竟發現自己的寫作有了進展。他比過去更能集中注意力了,某些瓶頸也自然而然地被他突破了。于是征在創作上打開了局面,同時又解決了生活費用的問題,可謂一舉兩得。
“戴姨真神奇,她一看就知道我該如何努力。現在我明白了,懶惰是我這一生最大的敵人。 我必須鍛煉我的筋骨,做一個強壯的人。”他對晚儀說。
現在征很少做那些冥思苦想的無用功了。不論是閱讀還是寫作,只要他坐下來,總有一定的效果。他的自信心正在漸漸地建立起來。
從前寫詩的時候,征的閱讀范圍比較狹窄,一般只限于文藝和歷史類的書籍,而且他的閱讀不夠細致,時常不耐煩,所以收獲也就不大。自從在朋友那里偶然結識了戴姨之后,征的眼界一下子就打開了。現在他不光讀文藝和歷史,還讀哲學和自然科學書(他本來就喜歡動物學)。不知從哪一天起他開始感到,不論讀哪一類的書,全都同他所從事的文學寫作有關,并且他只能以文學的眼光來看待各種各樣的知識。這個發現給了他巨大的閱讀的動力,從此他就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夠用了,以前的那種種空虛無聊也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哲學和動物學使他的好奇心大漲,他開始改換文風,嘗試短篇小說的寫作。這一次,幾乎是一試就成功了。
“不少東西在里面看不清,但又不是完全盲目的,差不多是有條不紊地出來。”
當他這樣告訴戴姨時,戴姨就說他“上路了”。
“我開始成熟了,我是作家了。”征對自己說。
他仍然愿意下苦力,出大汗。他嘗到了甜頭。
不過像他這種性情的人,搞創作并不會一帆風順。在某些低潮的日子里,閱讀也常常走神。每當他想松懈下來,便記起了戴姨的叮囑。她說,像他這種氣質的人,如果熱愛寫作,就得訓練自己過一種近似兵營的生活。只有這樣才會有一定的產量。戴姨是板著臉說這些的,當時她那冷酷的目光掃視著他,就好像他是一只產蛋的母雞一樣。于是他明白了,他不能退,一退便全盤崩潰。于是,他幾乎天天去碼頭,沒有缺過工,與此同時,他也每天閱讀與寫作。哪怕只讀一頁書,哪怕只寫兩三個句子,他也在堅持。他想,這是他的命運,他喜歡這個命運,他不愿意做另外的選擇。尤其不愿休假,因為在這個關鍵時刻休假會奪去他的精神享受。
在晚儀的眼里,征是一位晚熟的作者。她相信他的不一般的才華,在他頹唐的日子里時常暗暗為他著急。后階段他的爆發又令她無比欣慰。她想,多少年都過去了,她和征都有點盲目,只有戴姨知道要怎樣塑造個性,難道不是她將征塑造成了奇跡嗎?當然,也是征自己將自己塑造成了奇跡,戴姨的工作就是調動征身上的活力,使其盡力發揮。晚儀認為征的命運的轉折是由于戴姨。女王是世界上的一個神奇的存在。
多年的實踐早就使征體會到了,文學可不是好玩的,你必須用性命去拼,任何取巧和松懈都會導致一敗涂地,唯一的方法就是迎難而上。對于他征來說,當好一名碼頭裝卸工是他有可能從事文學的保障。所以有時即使情緒陰郁,他也咬緊牙關去碼頭。往往是當他出了一身臭汗之后,抑郁的癥狀就會減輕,垂死的創作欲望也會漸漸抬頭。勞動不光是鍛煉了征的體力,同時也使得他與周圍的工人們建立起了實質性的關系。在去碼頭工作之前,征的性格有點像“獨狼”。在文學圈和社會上,他除了晚儀和另一位詩人,再沒有其他的朋友或相熟的同事,他不愿和人來往。然而進入碼頭工人的群體之后,一切都由不得他了。他的工作有合作的性質,不管他愿不愿意也得同這些粗獷的人打交道。他們有的簡單質樸,有的靈活狡詐,有的病態陰沉……漸漸地,征成了他們中的一員。于是征發現,他的文學素質在他與人打交道時給了他很大的幫助。由于他善于揣摩別人的心思,并且見多識廣,他在人們當中越來越受歡迎了。現在去碼頭對于他來說成了一樁身心放松的事,他甚至在工人們當中發展了兩位讀者。常常在入睡前,他會在腦海中重演白天里同工人們打交道的場景,這些場景一般來說都會令他滿意。即使有些小小的不痛快,在日后的深交之中也會轉化為彼此相安的關系。他進而感到,他對日常生活的投入如今也在促進著他的創作上的突破——自信心一提升,創造就更有把握了。
晚儀對征說:“你現在渾身洋溢著碼頭工人的粗獷氣息,我覺得你成了干大事的人了。”
“這話說得好,”征高興地說,“你們都在鼓勵我。雖然我并沒有干出什么大事,可我心里很踏實。現在我對短篇情有獨鐘,我的野心是將生活中的美的圖形一個一個地畫出來。”
“你已經成功了,還會繼續不斷地成功。一流的作家總是這樣的,連連爆發,出人意料。”晚儀真誠地看著他說道。
晚儀還告訴他,他介紹來的那兩位讀者,很快就融入了他們的讀書會,受到大家的歡迎。因為他們對文學的看法很獨特,引起了不少人的興趣。
啊,那些碼頭工人,他現在已經離不開他們了。他倒不是要以他們為小說的素材,他的小說不屬于那種以生活表面事物為素材的小說。他之所以同工人們打成一片,是因為這是他近年的生活模式,一種以寫作為中心的、理想化的生活模式。他必須同人打交道,而周圍人的喜怒哀樂,正在間接地刺激著他的創作欲望。他找不出明顯的證據,但他本能地感到事情就是這樣的。他不再萎靡了,經過多年的浮沉之后,他看見了那條路,而這一切,皆因文學女王的指點。他多么幸運!他記起自己在三十五歲時曾經想過學習做一名圖書管理員,他還買了一些專業的書籍打算進行這方面的鉆研。但兩個月之后他就將這個計劃拋之腦后了。當晚儀向他詢問這事時,他想了想說:“到底意難平啊。”晚儀聽了便不住地點頭。他不適合做圖書管理員,卻適合做碼頭工人,這就是戴姨那天才的大腦為他做出的設計。他雖對自己是否能長期創作下去沒有把握,但他現在的確是幾乎每天都在創作。他覺得自己應珍惜這一段黃金時期,畢竟自己已經擁有了,即使明天就迎來創作的危機也沒有關系,到那時再去做圖書管理員或讀者也來得及。晚儀特別欣賞他的這種態度。
有同行對征說,他的小說中的人物都很穩重,很結實,思想有定準,這是不是裝卸工作給他帶來的啟示?征當時沒有回答他的同行。他在黑夜里仔細搜尋著他的記憶,某個模模糊糊的形象便在腦海中像半成品一樣時隱時現。嗨,這位同行真神奇,他看到了他征的內面形象。從那天起征便開始觀察自己周圍的工作伙伴,對這些司空見慣的面孔一天比一天感到驚奇起來。后來他便確定了,這些人都是他小說中的人物,每一個人都是。不光碼頭工人,還有他的同行,還有那些讀者,或不從事文學的人,他們全都具有深奧的、看不清的本性,他們生活在這大地之上,人人都深諳一種隱秘的技能。而他征,作為一位作家,是發現這一點的人。否則的話,他又怎么能在故事中再現這種秘密呢?征想到這里,便從床上爬起來。坐到書桌旁開始寫。他是如此的興奮,整整寫了一個半小時還停不下來。后來,他聽到環衛工人已在他窗下清掃街道了,他這才滿意地放下筆,進入吸引著他的夢鄉。
征的理想中的愛人是晚儀。自從青年時代加入寫作行列,遇見這位同行之后,征從未改變過對她的愛。熟人們都覺得征的這種單戀有點不可理解,有點柏拉圖似的愛的意味。征對周圍人的看法不加理會,他心里認為,要是他不愛晚儀了,這倒是一件怪事了。晚儀對于他來說就是文學、愛人和美。對于征,即使是戀愛,也得將文學擺在首位,文學是他的終身的情人(至少他目前這樣認為)。而晚儀,正好與文學合一了。他也知道晚儀沒有愛上他,他將原因歸于自己個性方面的缺陷,他希望通過從事寫作來改造自己的個性。然而在以往的那十幾年里頭,他取得的成效甚少,直到戴姨出現……并非他現在在改變個性方面取得了進展,晚儀就有可能愛上他了,他知道這種可能性很小。但他不能不愛晚儀:她是他的理想,對他來說她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女人。只要他還在追求文學,晚儀在他心中的形象就總是那么生動、活躍。晚儀從來不勸征成家,她深知他的難處,知道他要將有限的精力投入文學,無法同時維持一個家庭。這位純粹的文學工作者深得她的喜愛,在十幾年的友誼中,她從未在他面前有過輕浮的舉動。
“實際上,我把我們之間的友誼看得與愛情同樣重要。”晚儀說。
征則在心里說:“我從來都是把自己看作你的第二個愛人。”大概因為沉浸在文學氛圍中的緣故,征并不為晚儀不愛自己而感到痛苦,雖然有些失望。晚儀是他的創作的重要的靈感之源,他每寫出一篇成功的作品,都要設想一通晚儀的看法,為之興奮,為之鼓舞。他認為要是換了另一位女士,他就不可能再得到這種幸福了。他想,他同晚儀之間的這種融洽契合在人當中只有幾千萬分之一的幾率,現在落到了他的頭上,是上天對他的垂青。是因為晚儀的出現,他才真正意識到了自己在文學上的才能,過上了他愿意過的這種生活。在晚儀和戴姨的幫助之下,他始終走在正道上。這兩位女性遠遠超越了歌德《浮士德》一書中的永恒女性,因為現在是新時代了。
在上一次的文學聚會上,征經歷了觸及靈魂的震動。從聚會回來之后,他和晚儀兩人就像競賽似地投入了狂熱的寫作。有時在半夜,他會突然接到晚儀的電話。
“到處都敞開了,什么都可以寫了。”晚儀說,“征,我猜想你也到了那個地方,對嗎?真沒想到我倆會這么走運。”
“我正在想關于永恒女性的事。我當然到了那里,因為晚儀總在我身邊嘛。”
“你的話讓我放心。我們同樂吧。晚安。”
征想,剛才寫作的時候,他也有這種感覺。句子從黑暗里沖出來,順利得讓他想不到。所有的柵欄全都被沖開了……
有時他也會在半夜打電話給晚儀。
“晚儀,你幫我判斷一下看,我會不會像夜游神一樣四處溜達,隨便在紙上寫些句子?這種東西能不能算文學?”
“老朋友,祝賀你升級了!你這是非常高的境界了,我應該稱這種境界為自由。天哪,我現在都追不上你了,你跑得沒影了……征!征?!”
“我在聽呢,晚儀。我想起了從前那倒霉的一年,我要是那個時候放棄了的話,如今該有多么慘。好了,我再說就要被沖昏頭腦了。”
他感到無比幸福。被自己心儀的女人欣賞,還能有比這更高的滿足嗎?這樣的小日子多么美,但愿能持續下去。即使晚儀沒有愛上他也不要緊,這種境界一點都不亞于愛情。她是一位知己者,杰出的女作家,她對他的創作有極高的評價。征激動得在房里走來走去,平靜不下來。就在黎明時分,他看見了自己的手。那也許不是他的手,只不過有點像他的手罷了。它握著什么東西,握著什么呢?他終于看見自己的手了,而在這之前,他從未看見過自己的身體。這是寫作給他帶來的穿透性視力。他,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突然看見了自己的手,他走火入魔了。
他沒有上床睡覺,洗了個冷水澡,給自己做了早餐吃了,就去碼頭上了。他看見自己正在投入火熱的生活,渾身有使不完的勁。
“征啊征,你今天工作起來像老虎一樣!”他的同事評論說。
“可能我本來有點像老虎,以前自己完全不知道。”他笑起來。
“現在完全知道了嗎?祝賀你啊。”
這些工人總是這么風趣。多么奇怪,好多年之后,他才發現自己周圍的人深奧又風趣。這都是創作所導致的,不創作,他就看不見人們的本質。比如這位老傅,他走路時一只胳膊老是彎曲著,這是因為他家中的負擔很重。征以前也認識老傅,可他從來沒有關注過他的家庭負擔,他認為老傅自私自利,不懷好意,這種人活在地球上對誰都沒有好處。征對自己眼光的變化暗暗感到欣喜。現在,看見自己的手成為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了。并且在清晨,當太陽還沒升起來的時候,他還聽到過兒童朗誦童謠。“我的圈子在漸漸地擴大,雖然前方是一片渾沌。”他聽見自己在說,“什么是短篇小說?短篇小說就是另類的詩散文啊。你在寫作時并不那么盲目,你差不多可說是胸有成竹了,因為你的思維的深處有原型。一個就是另一個,另一個從前一個生出……堅持一下,讓句子持續地流出來。”
勞動給他帶來的是神清氣爽。他自然而然地想要坐下來讀書寫字了,他一點都不曾強迫自己。今天天氣不是很好嗎?這是最適合創作的日子啊。一想到過后那種收獲的快樂,情緒就高昂起來。
“征,出來散散心吧,我們都想為你慶賀一番呢。”新近交的朋友說。
“我正在筆耕,我不能離開,不然會后悔的。”
他歉疚地掛上了電話。有什么好慶賀的?他浪費了那么多的時間,現在必須盡全力彌補。他可不想再返回過去的頹唐生活。那種比死還難受的陰暗生活,他已經受夠了。他現在的生命是虎口余生,得拼搏。
他拿起筆,便有某種誘惑性的詞句在向他招手。于是他放下了懸著的一顆心——寫下第一句,便會有第二句追隨而來。晚儀,晚儀,你瞧現在的征變得多么有能耐,多么幽默了!
他寫得不算多,但也夠多了,因為每天都在寫啊。為保持形象氛圍的鮮明,他每天的寫作都適可而止。寫作生活是任務,一項最最愉快,最最自由的任務,他每天最樂于去完成的特殊任務。窗子外頭,城市的燈火在顫抖,那是從心臟里涌出的愛的暖流所致。
靈感真是一種奇怪的東西啊。從前,他老是有枯竭的感覺,不知道要如何突破,創新非常艱難。自從文學女王啟發他,使他形成一種新的生活模式之后,靈感便源源不斷地到來了。這種情形確實像晚儀所說的“到處都敞開了,什么都可以寫了”。征讓自己的思緒沉淀下來之后,努力地回憶種種細節,得出了一個結論:寫作同肢體的訓練直接有關。如果人想得到一種旺盛的、源源不斷的創造力,他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勞其筋骨——或參加勞動,或進行體育鍛煉。一個懶人,即使天賦中有創造力,也會隨著時間不斷萎縮。他自己的例子就說明了這個規律。那么靈感,就應該既是心的渴望,也是肉體的渴望。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藝術家應該是最健康的人。他們的健康體現在能夠從事一種高強度的靈肉合一的運動。在這種新生活中,征解放了自己,而且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健。他的近期目標是讓寫作帶來金錢,然后脫離碼頭上的工作,代之以更為隨心所欲的體育鍛煉。為了明白這個道理,他繞了一個多么大的圈子!幸運沒有同他擦肩而過,他的覺悟還算及時。關鍵就在于戰勝動物性的惰性,像一個“人”那樣生活,這該是多么淺顯的道理!在四十四歲這一年,征才在戴姨的啟發下明白了靈肉之間的關系,這件事令他刻骨銘心。現在他不但自己要身體力行地實踐這條規律,還要將自己的經驗告訴同行和讀者,還要寫一本書去宣講!那些在昏暗中掙扎的人將因此受益。這段時間,他同晚儀討論得最多的就是他的這個心得體會。他感到他從前就像一個孤兒,現在他才通過他的文學與整個世界發生了互動。
征的文學上的聲譽在漸漸上升,弦也繃得越來越緊了。現在他成了一臺好用的機器,產量不斷增加。盡管如此,他還是不敢有一點點懈怠。他已經辭去了碼頭上的工作,租了一套大一些的公寓。現在他除了圖書館,幾乎什么地方都不去了。因為無論去什么地方都覺得難以忍受。他的位置在圖書館和家里,還有鍛煉場所。他希望自己過一種刻板的生活,每天讀、寫、鍛煉,讀寫、鍛煉……日復一日地循環,直到八十歲以后。“這才是真正的享受啊!”他告訴晚儀說。他從晚儀那里獲得了熱情的回應。不過他的節奏有時也會被打亂,碼頭工人中的讀者和他后來交的一些書友會來拜訪他,他們一般先打電話,得到允諾后便來到他家中。這種交流雖不多(人們擔心會干擾他的寫作),但同樣給征帶來了樂趣。他的作品本來就是為這些書友們寫的,現在書友們對作品做出了反應,同作品、也同他這個人產生了互動,從而使作品存活,并得到延伸,還有什么比這更美好的事呢?他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個嗎?
“親愛的征老師,我讀您的作品時有這樣的感覺,好像正是我想寫的那種——我激動得不時站起來。您覺得像我這樣的——我是電子產品售貨員,文化不高,可我酷愛文學,您覺得我也可以嘗試寫作嗎?”書友之一說道。
“為什么不可以?太應該了!如果您有沖動,不妨馬上去試。我從前也是這樣試出來的。我的文化也不高。能不能搞文學,要試一試才知道。”
“征,我目睹了你在從事重體力勞動的同時搞創作,這給了我極大的鼓舞!我家境不好,還得做好幾年裝卸工,可是我還年輕,我打算今后也要從事文學。我現在就每天晚上閱讀和做筆記,我要向你學。”裝卸工說。
“你用不著向我學,你做得比我好。你會找到時間來做你喜歡的工作的。我已經隱隱約約地看到了你的前景。”征說。
“我太激動了,今天就像,就像,不,我找不出合適的形容詞!”
裝卸工漲紅了臉。他想了想又說:
“在你的小說中,總有一個中心旋渦,從那里頭出來的張力分成好幾股力,每一股力的形式都不同,但讀者感到這些全是同一種類型的力……好長時間了,我一直在思考這種問題。”
“你說得太準確了!兄弟,我覺得你已經做好了創作的準備,你可以在休息日開始嘗試。你的水準非常高。”征也很激動。
“我還有一個看法就是,最好的文學不寫已經有的事物,只寫你最想要的。將你最想要的寫出來,就成功了。因為你真正最想要的,別人也想要,你就會獲得讀者。我說得有道理嗎?”售貨員說道。
“豈止有道理,”征愉快地看著他,“您是一位真正的前沿文學的研究者,您的潛力非同一般。”
這一類的交流意外地成了征的創作的動力。他覺得自己沒有理由休息,哪怕就為這些親愛的書友,他也得多寫,再多寫!為了多寫就得多讀。他認為書籍全是相連著的,他總在這些山巒的內部穿行,為的是弄清書籍的結構。年輕時他憑表面的記憶讀書,現在完全不同了。他早就停止了大腦的記憶功能,現在他的工作是探測和實驗。他喜歡去觸動那些障礙物,看看它們會有些什么樣的表現,也看看自己的思維把握它們的能耐。對于現在的征來說,讀書就是建立屬于他自己的歷史。從前他不知道歷史是什么樣的,哪怕書讀得再多,關于這方面也沒有多少感受。自從他在創作方面上路之后,歷史感就逐漸地建立起來了。歷史在書籍中,也在日常生活里。他發覺自己獲得了一種眼光,他愿將這種眼光稱之為歷史的眼光。在書籍中,在生活中,他都用這種眼光為自己開路。
“我想預測一下這個東西會不會跳起來,我用我的意念拍打它,我聽到它里面發出悶悶的響聲——它不是實心的。那是歷史的回聲。難道你不覺得所有的書籍都得這樣來閱讀嗎?”他對晚儀說。
“有道理。歷史應該從內部去接近。凡是做表層記錄的人必定失敗。征,我覺得你越來越高明了。”晚儀回答。
“你比我覺悟得早多了。即使我現在有了什么進步,那也是戴姨對我的幫助啊。你忘記這一點了。”
“戴姨是明燈,征也很了不起啊!”
“讓我們相互吹捧吧。”
那一次兩人談得高興起來,就由征請客去四川餐館吃麻辣燙。
“二位好久沒來了,真想念你們啊!”老板齊師傅說。
“征現在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了。他今天是來齊師傅這里尋找歷史感的,齊師傅你給他一點啟示吧。”晚儀說。
“征,你可找對了地方!我這里到處都是歷史!看看這桌面上的木紋就知道了。幾天前,有一個人朝這木紋吹氣來著。”
“你說的是礦工嗎?”征問道。
“是啊,就是礦工。他吹氣時這些木紋就變了色。”
“我明白了。”
齊師傅去后廚炒菜去了。征和晚儀相互打量,兩人都驚異于對方的變化之大。他倆各自私下里嘀咕:“這還是原先那個人嗎?前不久看見的容貌已變成了歷史。”他們這樣想,倒不是因為對方變老了,他們還算不上老,而是因為一種沒有把握的感覺在內心升起來了。此時雙方都有點尷尬,不知道要如何樣向對方敞開心靈,恢復從前那種關系。
征看著晚儀頭頂的空間,分明感到自己一副蠢像。幸虧這時老板娘來上菜了。她擺上了幾個冷盤。
“二位想想你們從前辯論的情景吧。”老板娘似笑非笑地說。
征的表情立刻變得活躍了。
“文學之愛發展到了新階段,這是個猜謎的階段。我說得對嗎,晚儀?你有什么看法?”征說道。
“我同你不可能生分。今后,十次猜謎總有九次猜中吧。我們在將文學的規律付諸實踐。”晚儀興奮地說。
“這些木紋會為我們證明。”征也興奮了,“從前有一次,我倆坐在這里,外面發生了地震。那時我就有種預感,雖然那時我很幼稚。”
麻辣豆腐端上來了。兩杯酒喝完,兩人都伏在桌上睡著了。
齊老板說:“這就是歷史啊,他們進去了。”
老板娘說:“多么過癮的歷程啊。”
虎紋貓急切地叫著,在兩人的褲腿上擦來擦去。兩個人都在睡夢里聽到了它的叫聲。這只老貓是齊老板的計時器,它總是敏捷地朝著需要計時的地方鉆,從來不會出差錯。
當天空出現紅色的晚霞時,兩人一道醒了過來。他們手挽著手走到街上,站在人行道邊看那落日的余暉。
“貓咪怕我們錯過了這人間的美景,當時我也急著要醒來。”
征說這句話的時候一臉的滿足。
“你瞧,這就證明了!”晚儀回應道,“我同你不可能生分。”
夜晚的陰影鉆進那些角落時,征和晚儀沉入了城市的歷史,他們兩人都隱藏起來了。
征信步走到河邊的餛飩攤子那里坐了下來。
“一九八三年時,你的事業出現過轉機。你還記得那時城市是什么表情嗎?”
老婦人一邊下餛飩一邊垂著眼皮問征。
“那時到處是急切的表情,媽媽。我永生忘不了。現在已經緩過來了,但仍有一雙詢問的眼睛。有一天半夜,就在這里,您的美味小吃給了我無限的慰藉。您基本上沒說話,但您說出的只言片語在后來漫長的日子里不時在我的記憶深處響起。媽媽,您如何評價我這樣的神游者?”
“你啊,小伙子,你已經知道我的看法了。凡是來吃餛飩的都是心如明鏡的人。今夜的河水不再是一九八三年的節奏了。這是很好的。”
“真好吃啊。此刻我有了新的記憶。真正的新!”
后來征在河邊看見了人群,人群正在騷亂,不久就潰散了,只有兩個人留在堤邊。他們是一男一女。女人居然同征打招呼了,是晚儀。
“晚儀,這位貴姓?”征問道。
“我想找我的男友老黃,結果找到的是礦工老賀!這種陰錯陽差令我愉快。歷史就是這樣的,對嗎?”晚儀俏皮地說。
他們三人站在那里聽河水。后來老賀忽然跳起來就跑,說地下坑道里發生了變故,他得趕去救援。
“晚儀,你真是來找老黃的嗎?”征問。
“當然不是。老黃是我的歷史,我不可能去找他,只能等他在某一天重演。當然我也不是消極地等,我花樣百出。”
“我祝你好運。地下坑道的事故你聽得到嗎?”
“聽得到。隱隱約約地,那里同這里是相通的。一九八三年時——”
“啊,為什么你們都說一九八三年?”
“那是希望之年嘛。”
“說下去啊。”
“我忘了后面的句子了。我總是這樣。”
天黑時征回到家里。在臺燈柔和的光線里,他又進入了那個地方,那是一幢只有一層的、屋頂很高的瓦屋,門口有兩棵國槐,樹葉的長勢蓬蓬勃勃。屋里是兩間房,里面一間,外面一間。里面那間有書桌和木椅,他坐在那里寫。現在他已經比較熟悉這個地方了。屋后有些吵吵鬧鬧的聲音,不過比較模糊,并不影響他的冥思,倒像是在促使他的語言傾巢而出。
他在他稱之為“槐樹屋”的房子里呆了兩個小時,感覺自己不能再這樣寫下去了,就停下來,走出屋子,回到自己家中。“哈,我今天太棒了!”他說。
他坐在黑暗中同戴姨進行想象中的對話。
他:感覺不到寫作的意義,這是否走在正路上?
戴姨:那意義在行動中。如果順手又流暢,便不會偏離目標。
他:我好像越來越熟練了。
戴姨:恭喜你啊。
他:可我總有恐慌感。
戴姨:恐慌吧,恐慌吧。看那金燦燦的麥浪。
他走到窗前,城市涌進來,嗡嗡地應和著他。如此安靜、富足的生活使他陶醉了。經過多年的掙扎,他征終于完全上路了。即使到了今天,當他回想從前那一輪又一輪的沉淪時,仍然感到后怕。生活中的轉折是隱藏著的,表面的不幸下面有巨大的幸運。他和晚儀都已經得到了幸福。
他挺過來了。他的素質并不好,所以才有那些挫折。是他對于文學的無窮無盡的、純真的愛支撐了他,而晚儀和戴姨這兩位非凡的女性也是他的支柱。這大地有溫暖,所以才會生出這類杰出的女性。她們就是文學,他愛她們,永遠愛。如果遠離了她們,他簡直不知道自己是否還實存。人類的整體感就是通過她們傳送到他體內來的。
(責編:鄭小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