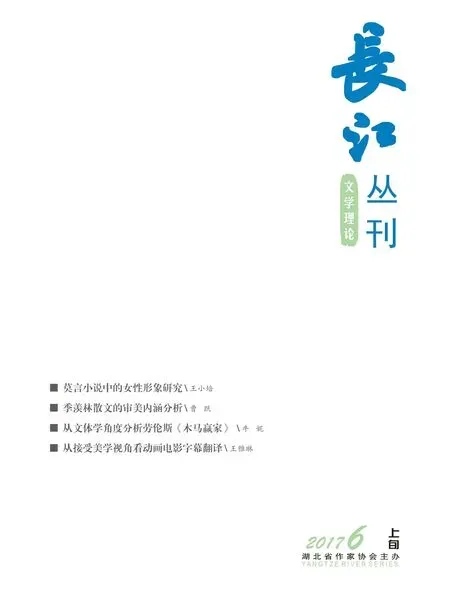從文化翻譯觀視角看《黃帝內經…素問》文化負載詞的英譯
晏 麗
語言研究
從文化翻譯觀視角看《黃帝內經…素問》文化負載詞的英譯
晏 麗
《黃帝內經…素問》(簡稱《內經…素問》)中存在的大量文化負載詞反映了中醫特定的文化信息,是《內經…素問》翻譯的重點和難點。本文以蘇珊…巴斯納特的文化翻譯觀為指導,通過例證分析李照國《內經…素問》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探討文化翻譯觀對《內經…素問》翻譯的解釋力,以期對中醫典籍乃至整個中醫翻譯有所啟示。
文化翻譯 《內經…素問》 文化負載詞
一、引言
《黃帝內經》(簡稱《內經》),即《素問》與《靈樞》之合稱,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醫學典籍。據現有史料,《素問》成書于周秦之間或戰國至兩漢時期,而《靈樞》的成書年代尚不確定。由于成書年代久遠,且受古代哲學思想和古代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的影響,《內經》形成了獨特的中醫文化,書中可以找到大量反映中醫特色的文化負載詞,而正是這些文化負載詞給《內經》的理解和翻譯帶來了很大困擾和挑戰。本文選取《內經…素問》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負載詞,通過例證分析李照國教授文化負載詞的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以蘇珊.巴斯納特的文化翻譯觀為指導,探討文化翻譯觀對《內經…素問》翻譯的解釋力,以期對中醫典籍乃至整個中醫翻譯有所啟示。
二、蘇珊.巴斯納特的文化翻譯觀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翻譯的重心從語言文字方面轉向基于語言轉換的跨文化交流。1990年,作為當代西方文化翻譯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國蘇珊.巴斯納特(Bassnett,Susan)在她的《翻譯,歷史與文化》(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翻譯觀。指出,翻譯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過程,而不單單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解碼和編碼。翻譯是為了沖破語言之間的障礙,從而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轉移和結合。翻譯是為了滿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體的需要。(Bassnett, Susan,1990)。蘇珊.巴斯納特提出,翻譯的過程中應盡量保留源語文化的差異性,讀者應該主動去了解異國文化,從而適應文化差異。文化翻譯觀強調,真正實現文化交流的手段是采用“異化為主,歸化為輔”的翻譯策略。
三、文化負載詞
目前,國內外學術界對文化負載詞的定義各有不同。如彭智蓉將文化負載詞定義為“標志某種文化中特有事物的詞、詞組和習語。這些詞匯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長歷史進程中積累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的生活方式。”也有很多學者采用包惠南和包昂先生在《中國文化與漢英翻譯》中提出的“詞匯空缺”的定義,即“源語詞匯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在譯語中沒有對應語”。Mona Baker將文化負載詞定義為源語在目標語中完全沒有對應的詞匯。由此可見,文化負載詞標志著特有的民族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
由于《內經…素問》成書時間早,且受古代哲學思想和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的影響,形成了獨特的中醫文化,書中存在大量反映中醫特色的文化負載詞,是翻譯的重點和難點。《內經…素問》文化負載詞的分類大致有三種:一是根據詞性分類,如張璇和施蘊中按詞性分為名詞類文化負載詞、動賓類文化負載詞和形容詞類文化負載詞。二是根據性質分類,可以分為人名類文化負載詞、中醫名詞術語類文化負載詞、中醫相關哲學概念類文化負載詞和其他描述類文化負載詞。三是根據與目標語文化內涵的對應情況分類,可以分為不完全對應文化負載詞和完全不對應文化負載詞。
四、文化翻譯視角下《內經…素問》文化負載詞英譯分析
目前,《內經…素問》的英譯版本有十幾種,本文選取李照國教授《內經…素問》英譯本主要出自以下幾方面原因:李照國母語為漢語,曾獲英語語言文學學士學位和中醫博士學位,其《內經…素問》全譯本入選《大中華文庫》。作為漢語背景譯者英譯《內經…素問》的杰出代表,李教授在國內具有較高的影響力。
本文按照性質分類,將《內經…素問》中的文化負載詞分為人名類文化負載詞、中醫名詞術語類文化負載詞、中醫相關哲學概念類文化負載詞和其他文化負載詞。其中,人名類文化負載詞的出現頻率很高,而每一個人物背后又有一定的歷史背景和典故,所以人名類文化負載詞的翻譯也不容小覷。如開篇《上古天真論篇》中“黃帝”一詞的翻譯歷來就爭論不休,李照國譯為“Huangdi, or Yellow Emperor”,采用音譯加直譯的翻譯方法,并且在文后加尾注給讀者提供關于“黃帝”的背景信息,有效地還原了源語文化信息。再如“天師”一詞,原句話中“天師”即指“岐伯”,李本將其譯為“Master Qibo”,可見,李本采用直譯法,并補充了人物的背景知識。
中醫名詞術語是反映中醫文化特色的詞匯,是《內經…素問》文化負載詞的重要組成部分。此類文化負載詞在英語中完全沒有對應,因此翻譯難度大。如《上古天真論篇》中的“虛邪賊風”是具有中醫特色的名詞術語,泛指四時不正之氣,李本將其譯為Xuxie(Def i ciency-Evil) and Zeifeng(Thief-Wind),并在尾注中指出Xuxie and Zeifeng refer to all abnormal climatic changes and exogenous pathogenic factors.李本采用的是音譯加直譯的翻譯方法,并用尾注把中醫文化補充進來。再如,《生氣通天論篇》中的病名“薄厥”一詞,指的是大怒導致氣血上沖,臟腑經絡之氣受阻而引發的昏厥證。李本將其音譯為“Bojue”,并在尾注指出:“Bojue means syncope caused by disorder of Qi and blood due to rage”.李本使用音譯加尾注的方法保留了源語文化內涵,方便外國讀者了解這一中醫術語的特點。
受傳統哲學的影響,《內經…素問》中存在許多哲學概念類的文化負載詞,如陰陽、五行等。這類文化負載詞在英語中也屬于“詞匯空缺”,無法找到對應語。如《上古天真論篇》中的例句“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陰陽,和于術數,”指的是上古時的人,懂得養生之道,他們遵循陰陽變化的規律,掌握養生的辦法。其中,“道”是指懂得養生的道理,李本譯為“the Dao(the tenets for cultivating health)”, 采用的是音譯加夾注給予語義補充;“陰陽”音譯為“Yin and Yang”;“術數”是指養生的辦法,譯為Shushu(the ways to cultivate health),采用音意結合的翻譯方法,有效地保留了源語文化的內涵,便于外國讀者理解。
《內經…素問》中存在很多古漢語特有詞匯,如古今字,通假字等,本文把這類詞歸為其他文化負載詞。這類文化負載詞給《內經…素問》的理解和翻譯也帶來了不小困難。如《陰陽應象大論篇》中的例句“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其中“四支”中的“支”與“肢”字,“六府”中的“府”與“腑”字分別為古今字,該句話的意思是清陽之氣充實于四肢,濁陰之氣內走于六腑。李本分別譯為“four limbs”和“Six Fu-Organs,”采用了直譯法再現源語文化內涵,方便外國讀者了解古漢語特有詞匯。再如《四氣調神大論篇》中的例句“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該句話的意思是對于養生法則,圣人切實地奉行著,愚人卻違背了它。其中,“佩”與“背”是通假字,李本將該句譯為“The Dao(law of nature) is followed by the sages, but violated by the foolish,”準確地將通假字“佩”的含義表達出來,便于外國讀者理解。
五、結語
綜上可見,李本在翻譯《內經…素問》中的文化負載詞時大量使用了音譯的翻譯方法,并結合直譯和加注法,主張異化的翻譯策略,旨在最大限度地保留源語文化內涵,讓外國讀者更準確地了解中醫和中醫文化。正如文化翻譯觀所強調,在翻譯的過程中應盡量保留源語文化的差異性,要求讀者主動去適應文化差異,了解異國文化。“異化為主,歸化為輔”的翻譯策略是真正實現文化交流的手段。從文化翻譯觀視角下解讀《內經…素問》譯本可以看出,不同的翻譯觀和文化認同對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的選擇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1]Bassnett Susan,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M].上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0:8~11.
[2]彭智蓉.試論文化負載詞匯的翻譯[J].瘋狂英語教師版,2006(6):43~46.
[3]包惠南,包昂.中國文化與漢英翻譯[M].北京:外文出版社,2004.
(作者單位:江西中醫藥大學)
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規劃項目“文化翻譯視角下中醫文化翻譯策略研究——以《黃帝內經》英譯本為例”(課題編號:14YY14)研究成果。
晏麗(1983-),女,江西中醫藥大學人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中醫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