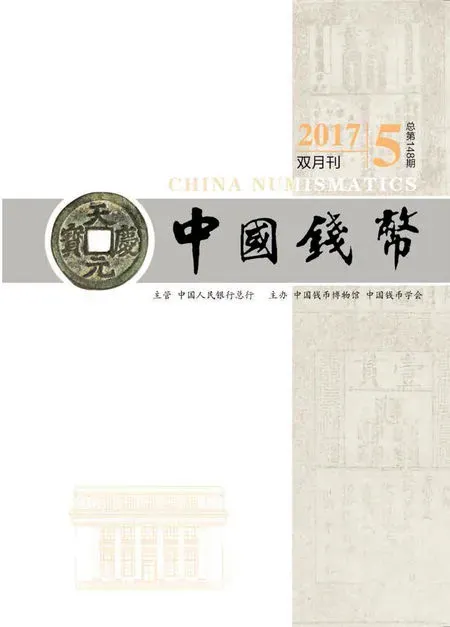翁樹培《古泉匯考》初探
關(guān)漢亨 (香港)
清代著名泉學(xué)家翁樹培(1764-1809)字宜泉、順天大興人,著有《古泉匯考》八卷。該書是清代錢幣學(xué)重要著作,為古今學(xué)者所推崇。因書稿未及刊刻故流傳絕少,民國前翻閱過翁書者屈指可數(shù)。后來翁譜輯入《古錢大辭典》時(shí)已化整為零,分別融入于各泉之下,如今已難一窺全豹。鮑康曾說:翁書八巨帙,厚幾盈尺,蔚成大觀,可見其篇幅甚具規(guī)模。翁譜究竟考訂了多少種古錢?全書有多少文字?劉喜海對(duì)翁書稿本校訂整理做了哪些工作?本文嘗試對(duì)翁書作一次剖析和探索,一方面有助揭開上述謎團(tuán),同時(shí)進(jìn)一步探討翁氏考訂歷代古錢的途徑和方法。此外,翁書稿本輾轉(zhuǎn)流傳多年,有不少鮮為人知的經(jīng)歷,也可在此一記。
一 記翁氏遺稿輾轉(zhuǎn)流傳經(jīng)過
《古泉匯考》是翁樹培嘔心瀝血之作,就在他去世那一年(嘉慶十四年),仍在努力考訂古錢入編,其中有一按語,記述當(dāng)年泉友何緩齋購得靖國元寶折二錢,“字帶隸體,元左挑,與靖康錢制作文字吻合”。同年冬樹培因患重病離世,遺下稿本二份,一是定稿本,另一份是草稿本,并留下翁藏古泉墨拓本至少十二冊(cè)。金石古泉名家葉志詵(1779-1863)字東卿,湖北漢陽人,官至兵部郎中,收藏金石書畫古泉甚富。翁書定稿本及泉拓十冊(cè)先由葉氏所得,藏于平安館。葉氏于同治二年卒后,其所藏仍保存完好。同治十三年(1874)平安館遭火劫,葉氏遺藏盡毀。翁氏遺稿幸好早前已轉(zhuǎn)歸楊幼云(1820-1901)收藏。光緒廿七年楊氏去世后,翁譜不知再落入誰家。1937年秋,翁書稿本八卷及古泉拓本十冊(cè)在北平琉璃廠文奎堂內(nèi)被發(fā)現(xiàn),由著名金文專家燕京大學(xué)教授容庚(1894-1983)經(jīng)手購得,歸燕京大學(xué)收藏。容庚曾說:翁書“雖有刪改,實(shí)為定本”。1952年大學(xué)院校調(diào)整,燕大一分為六,翁氏遺稿不知分到何處,數(shù)十年來杳無音訊,如今未知尚在人間否。
另有一份草本,據(jù)說“翁歿后,匯考為傭人竊出,售于劉(喜海)氏”。經(jīng)查核,翁氏卒年劉喜海十六歲,集泉?jiǎng)倲?shù)載,對(duì)這本增刪涂改幾不可讀的書稿未必有興趣。故“售于劉氏”之說不確,當(dāng)年接藏者另有其人。道光元年(1821)喜海時(shí)年廿八,是年其師金蒨谷見他案頭上置有翁氏書稿。道光十三年(1833),喜海出守福建臨汀時(shí)已開始校訂翁稿。道光十八年他曾說:“北平翁學(xué)士覃溪先生子宜泉比部著古泉匯考,其家止存稿本,涂乙?guī)撞豢勺x,余為費(fèi)三年功,抄錄正本藏之”。
根據(jù)資料顯示,喜海校訂翁稿時(shí)做了兩項(xiàng)工作,一是校正全書稿文字及理順文句,再抄錄成正本;二是參與考釋各類古錢,在“樹培按語”之后,分別寫下211條“喜海按語”。劉氏按語短則僅四字,長(zhǎng)則近四百字,一般二三十字不等。例如見四字按語:“鐵當(dāng)三錢”;五字按“此錢疑偽作”;六字按“此錢今世未見”;七字按“此說甚確宜從之”;八字按“喜海所藏此錢篆書”;九字按“喜海曾于都門見此品”;十字按“此泉應(yīng)列于不知年代品”。其論斷精確而顯出自信。道光十八年(1838)他初步完成校訂工作,此后十四年間,劉氏仍繼續(xù)考證補(bǔ)充多條按語。道光廿六年(1846)在西川任按察使時(shí),仍見他在書稿上添加按語;道光廿八年出任浙江布政使,在兩浙藩署蓬巒軒內(nèi),又寫下多條按語,直至去世前一年(咸豐二年)在京師寓所內(nèi),他先后寫下考訂順天元寶及熙寧重寶錢兩條按語,可見喜海為翁書稿用力之勤,令人敬佩。
翁樹培生前泉家能閱覽其書稿者,已知有兩人,一是泉學(xué)家倪模(1750-1825),嘉慶元年(1796)他在京師曾借錄匯考中有關(guān)歷代錢譜資料,其后載入《古今錢略》卷廿八內(nèi),二是藏泉家金錫鬯(蒨谷),金氏曾說:宜泉“所著古泉匯考一書,終日隨身,聞其夜臥亦置之枕畔,簽改粘綴,不遺余力。予于壬戌(1802)晤于京,后數(shù)年留京,時(shí)至旅館,常見其書,欲留一宿而不能”(《晴韻館古泉述記》)。
劉喜海在世時(shí),曾向他借閱翁書稿者亦有兩人,一是鮑康(子年)于道光廿年(1840)在秦中借閱此書;二是李佐賢(竹朋)于道光廿六年(1846)出守福建汀州知府之前借閱此書,鮑、李二氏均在其著作中評(píng)述過翁書稿本。
咸豐三年(1853)劉喜海在京師去世后,遺稿《古泉苑》歸陳介祺(字壽卿)收藏,而翁譜最初未知落入誰家。金石古泉名家王懿榮(1845-1900)字廉生,山東福山人。光緒元年(1875)他曾購得翁氏泉拓二冊(cè),并請(qǐng)鮑康題跋。大約在光緒中后期,懿榮才獲得翁書稿本。他在閱覽翁譜時(shí),于四種古錢下分別寫了“懿榮按語”。古泉名家胡義贊(1831-1902)字石查,河南光山人,胡氏與懿榮同為京官,為古泉至交。光緒廿四年(1898)胡氏曾借閱翁書稿本,并在書稿內(nèi)又分別寫下三則記事。至此,翁書在劉喜海加按之后,又增加“懿榮按語”四條,“石查記事”三則,從而將翁譜所記述泉家收藏事的年份,再延續(xù)至光緒廿四年,其考訂內(nèi)容及集泉資料比原稿更為豐富。
光緒廿六年(1900)庚子之變,八國聯(lián)軍侵占北京,王懿榮殉難。王氏卒后其天壤閣藏書便散出,翁書稿本由山東著名藏家趙孝陸(1875-1939)所得,趙氏山東安丘人,光緒三十年(1904)進(jìn)士。他十分珍惜這本流傳絕少的翁氏錢譜,嚴(yán)加保護(hù),不輕示人。民國廿三年(1934)著名學(xué)者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zhǎng)王獻(xiàn)唐(1896-1960),欲向趙氏借抄翁譜,再三請(qǐng)求下得趙氏允許,并由山東日照馬官縉(仲紳)負(fù)責(zé)繕寫,抄錄半載始告完成,馬氏抄本已入藏山東省圖書館。王獻(xiàn)唐曾說:“日后如有機(jī)緣,當(dāng)為印行”,然而世事多變,翁譜至此仍未能付刻傳之。
民國廿七年(1938)丁福保(1874-1952)主編《古錢大辭典》,曾向王獻(xiàn)唐借得翁譜馬氏抄本,并抄錄了一份,其后將全書稿輯入“大辭典”內(nèi)。至此,翁書稿本幾經(jīng)波折,輾轉(zhuǎn)流傳一百二十余載,終于有個(gè)好歸宿。從以上記事可知,翁氏遺稿未被湮沒得以保存,劉喜海、王懿榮、趙孝陸、王獻(xiàn)唐都是功巨,而翁譜得以傳后世,丁福保先生更是功不可沒,為世人稱道。
二 匯考八卷及前一卷考釋
倪模、李佐賢及鮑康先后看過翁書稿本,并寫下記事或評(píng)說。
倪模在《古今錢略》卷廿八中記述:古泉匯考(未定寫本)翁樹培撰,“此書匯考古泉源流沿革,以及歷代著述,收藏諸家,凡見于載籍者,一篇一句,罔不詳究異同,誠足為考古泉之總匯”。“以上歷代各家著錄(五十三種),皆翁宜泉古泉匯考中所錄者,余嘉慶丙辰(1796)都中曾借錄一通,間加按語,今全載于本卷”。
李佐賢在《古泉匯》首集卷三寫道:“古泉匯考計(jì)八卷,大興翁樹培宜泉著。卷一屬刀布、卷二至卷七自周秦以迄明季,并外國、無考者俱載,卷八則厭勝之類。視諸家錢譜搜羅宏富,可稱大觀”,“八卷俱有注而無圖,閱者不能一目了然”,“此則系未成之書,未及刊刻而宜泉謝世”。
鮑康在《觀古閣叢稿》記述:“道光庚子(1840)夏六月,(燕庭)觀察亦以奉諱流滯長(zhǎng)安,相見即索是書,觀察舉以相授八巨帙,厚幾盈尺,且謂余曰,此本出抄胥之手,未及校讐,子為我讀而正之”,“是編博引旁征,幾于無書不采”,“后二卷外國暨厭勝吉語諸品,不及詳其制,僅志其目而已……并為勘正數(shù)百字而歸之”。
從以上三泉家的記述可知,劉喜海所得古泉匯考草本共八卷,有注而無圖,卷一刀布,卷二至卷六自周秦兩漢下至元明兩朝,卷七外國錢及無考品,卷八厭勝吉語錢等。倪模所借抄者,內(nèi)容包括古今收藏名氏及歷代各家著錄五十三種,是翁樹培撰寫于乾隆五十八年,這部分內(nèi)容暫稱它為前一卷,它是翁書稿本重要組成部分,劉喜海所得之草稿本可能亦有收載。今見“大辭典”上冊(cè)總論中已載入倪模《古今錢略》卷廿八歷代譜錄五十九種,即已包括翁書的前一卷內(nèi)容。
丁福保曾說:翁書“惟卷一古刀布及卷八之厭勝品疵類太多,稍從刪節(jié)”。今見“大辭典”下編補(bǔ)遺僅收載翁書卷一古布幣十二品,包括安陽、宅陽、晉陽、魯陽、高都、平洲、鄩氏、襄垣及連布(四布當(dāng)千),還有空首布三品。另收載明刀(莒刀)及六品各式齊刀。其余七卷內(nèi)容已全部融入于“大辭典”各泉之下,現(xiàn)今已難一窺全豹。經(jīng)過我們分類統(tǒng)計(jì),匯考劉氏校正本共考訂歷代古錢573種(注:各朝通寶錢、年號(hào)錢,例如會(huì)昌開元、嘉定元寶、洪武通寶等版式繁多,但均作一種古錢統(tǒng)計(jì),如此類推)。經(jīng)過統(tǒng)計(jì),書稿八卷共撰寫字?jǐn)?shù)為二十四萬二千五百余字,另倪模抄錄前一卷計(jì)有13400字,李佐賢抄錄卷一古布資料計(jì)1500字(大辭典未見收錄)。因丁福保只摘錄卷一及卷八部分內(nèi)容,故可知全書稿總字?jǐn)?shù)應(yīng)不少于二十五萬七千字。(注:如要查找翁書稿撰寫準(zhǔn)確字?jǐn)?shù),可參閱:中國公共圖書館古籍文獻(xiàn)珍本匯刊之一:[清]翁樹培《古泉匯考》,中國國家圖書館文獻(xiàn)縮微復(fù)制中心。1994年)
三 翁氏博采群書匯考古泉
樹培自九歲起集錢,漸嗜泉成癖,經(jīng)長(zhǎng)年累月摩挲品賞,練就出色鑒泉本領(lǐng)。如鮑康所言:“凡泉之重輕薄厚,輪廓大小,一點(diǎn)一畫,罔不析及毫厘,既辨其形兼辨其聲,特辨其質(zhì)兼辨其色,折衷詳審,為近代譜家第一”。翁氏鑒泉一絲不茍,觀察入微,同時(shí)他十分重視從宏觀方面入手,認(rèn)真考證古錢之鑄地及國屬,并斷其時(shí)代。他嘗把考訂之古錢置于同一時(shí)期錢幣加以考察,比較兩者異同,并注重引證前人的論說,使其考據(jù)更具說服力。
1.以諸史貨志為本,旁及百家雜記
樹培十分重視集錄前人對(duì)各種古錢考訂之文字資料,內(nèi)容包括諸史貨志、史家著述、歷代錢譜及百家雜記等,幾乎無書不采。鮑康曾記述一個(gè)故事:“聞?dòng)性R(shí)(翁)先生者,偶直武英殿,見一人整冠坐廊下,據(jù)矮幾振筆疾書,視所抄則西清古監(jiān)也。當(dāng)日文淵閣武英殿圖書,悉許詣殿閣請(qǐng)觀,知必為先生,詢之確乃訂交去”。此例可見翁氏博采群書用力之勤。樹培嘗慨舊譜之簡(jiǎn)略失據(jù),曾說:竊謂(錢)譜,當(dāng)以諸史貨志為本,考其原委得失,旁及百家雜記,或有事近鄙陋而可資談助者,亦載之“(錄自《古今錢略》卷廿八)。簡(jiǎn)言之,“以諸史貨志為本,旁及百家雜記“是翁樹培撰編錢譜的指導(dǎo)思想。只要有助于古錢之考訂,任何史料皆可收集而載用之。例如名醫(yī)李時(shí)珍《本草綱目》中記載:“古稱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yàn)橐汇彛彏橐环郑姆譃橐粌桑鶅蔀橐唤铩薄_@段資料,翁氏考訂五銖錢時(shí)已被采用。
樹培考訂古錢時(shí),引用各種古籍均有先后次序,可用二十八字概括之:“諸史貨志記在前,培案在后抒己見,九位名家書八本,百家雜記助考研”。在引用諸史貨志之后,翁氏最多選錄八本錢譜包括有:梁·顧烜《錢譜》、宋·李孝美《錢譜》、南宋·洪遵《泉志》、明·董遹《錢譜》、清·《欽定西清古監(jiān)錢錄》、清·張端木《錢錄》、清·陳萊孝《歷代鐘官圖經(jīng)》、清·無名氏《錢幣考》等,(近今有學(xué)者考證無名氏即無錫人華玉淳(1703-1758)、字師道,號(hào)南林。詳見《中國錢幣》2000年第三期)。此外,翁譜最多引用諸家論泉者包括有:潘有為(字卓臣,號(hào)毅堂)、江德量(字秋史)著《江氏錢譜廿四卷》、倪模(字迂存)著《古今錢略》、瞿中溶(字萇生,號(hào)木夫)著《錢志補(bǔ)政》、張燕昌(號(hào)芑堂)著《金石契》、劉師陸(字子敬,號(hào)青園)著《虞夏贖金釋文》、何夢(mèng)華(元錫)、姜怡亭、嚴(yán)鐵橋(可鈞)等。
2.翁氏考訂各朝錢幣所引用的書籍
①考訂秦漢半兩五銖錢所引用書籍有:司馬遷《史記·平準(zhǔn)書》、《史記·貨殖列傳》、《前漢書·食貨志》、《后漢書·食貨志》、《前漢書·公孫述傳》、《晉書·食貨志》、袁宏《后漢紀(jì)》、鄭康成《周禮注》、賈公彥《周禮疏》、孔穎達(dá)《禮記疏》、司馬貞《史記索隱》、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黃鎮(zhèn)成《尚書通考》、王應(yīng)麟《漢制考》、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鄭樵《通志》、王應(yīng)麟《玉海》、竇啟瑛《四川通志》、高承《事物紀(jì)原》、朱彝尊《曝書亭集》、錢玷《古器款識(shí)考》、王昶《金石萃編》、丁傳《多野齋印說》、劉歆《西京雜記》、陳廷敬《午亭文編》、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曹昭《格古要論》、施青臣《繼古叢編》、陳恂《余庵雜錄》等。
②考訂魏晉南北朝錢幣所引用書籍有:《魏書·食貨志》、《晉書·食貨志》、《晉書·張軌傳》、《三國志·魏書》、《三國志·吳書》、《三國志·文帝紀(jì)及明帝紀(jì)》、《北齊書·文宣帝紀(jì)》、《周書·武帝紀(jì)》、《隋書·食貨志》、丘悅《三國典略》、杜佑《通典》、《唐六典》、《永樂大典》、《魏書·西戎傳》、《北史·西域傳》、《十六國春秋·后趙錄》、《河南府志》、《江南通志》、白潢《西江志》、顧炎武《日知錄》、葉大慶《考古質(zhì)疑》、周大樞《存吾春軒集》、倪濤《六藝之一錄》等。
③考訂隋唐五代十國錢幣所引用書籍有:《隋史·食貨志》、《隋史·高祖紀(jì)》、《舊唐書》、《新唐書·食貨志》、《新唐書·地理志》、《新唐書·西域傳》。《唐六典》、王溥《唐會(huì)要》、《五代史·南唐世家》、《五代會(huì)要》、陸游《南唐書》、薛居正《舊五代史》、鄭向《五代開皇紀(jì)》、《梁書·武帝紀(jì)》、《陳書·世祖紀(jì)》、《十國春秋》、《十國紀(jì)年》、《續(xù)通典》、鐘淵映《歷代建元考》、王圻《稗史類編》、龐元英《文昌雜錄》、張爾歧《蒿庵閑話》、沈括《夢(mèng)溪筆談》、孫承澤《春明夢(mèng)余錄》、王觀國《學(xué)林新編》、王楙《野客叢談》、姜紹書《韻石齋筆談》、周必大《二老堂雜志》、李時(shí)珍《本草綱目》等。
④考訂兩宋西夏及遼金朝錢幣所引書籍有:《宋史·本紀(jì)》、《宋史·食貨志》、《宋史·律歷志及職官志》、《永樂大典》、《遼史·食貨志》、《遼史拾遺》、《金史·食貨志》、《金史·廢帝紀(jì)》、方拱乾《寧古塔志》、馬端臨《文獻(xiàn)通考》、王圻《續(xù)文獻(xiàn)通考》、郎瑛《七修續(xù)稿》、胡承謀《湖州府志》、顏希深《泰安府志》、吳自牧《夢(mèng)梁錄》、屈大均《廣東新語》、屠叔方《建文朝野匯編》、曾敏行《獨(dú)醒雜志》、張禮《游城南記》、章如愚《群書考索》等。
⑤考訂元明兩朝錢幣所引用書籍有:《元史·食貨志》、《元朝典故編年考》、孔齊《至正直記》、《明史·食貨志》、《明史·流賊傳》、王鴻緒《明史稿》、《明史集腋》。谷應(yīng)泰《明紀(jì)事本末》、鄒漪《明季遺聞》、《清史·食貨志》、楊陸榮《三藩紀(jì)事本末》、張嗣衍《廣州府志》、張居正《太岳集》、顧炎武《亭林文集》、顧起元《客座贅語》、江師韓《韓門輟學(xué)》、陸琛《豫章漫鈔》、厲鶚《樊榭山房集》、沈國元《兩朝從信錄》、錢大昕《養(yǎng)新錄》、黃宗羲《行朝錄》、沈荀蔚《蜀難敘略》、侯恂《鼓鑄事宜》、王逋《蚓庵瑣語》、《經(jīng)濟(jì)類編》、《淵鑒類函》等。
⑥考訂外國錢所引書籍有:《史記·大宛傳》、《前漢書·西域傳》、《魏書·西域傳》、《隋書·西域傳》、《舊唐書·西戎傳》、《新唐書·西域傳及南蠻傳》、《宋史·外國傳》、《元史·外夷傳》、《明史·外國傳》、《明史·安南傳》、周煌《琉球國志略》、顧炎武《京東考古錄》、徐葆光《中山傳信錄》、朱景英《海東札記》、圖理琛《異域錄》、錢辛楣《養(yǎng)新余錄》、《神宗國史》、《西洋朝貢典錄》、《瀛涯勝覽》等。
丁福保曾說:“知古泉之蘊(yùn)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xué)所能盡也”。翁樹培精于兩宋錢之考訂,惟先秦古布考證尚欠精確,疵類頗多。例如將各種大小布幣列為上古及夏商布;翁氏仍依舊說,釋“賹化”為“寶貨”,并附于周景王錢之下;對(duì)先秦古幣的認(rèn)識(shí)多依從潘毅堂、江秋史之說。誠然我們不宜以現(xiàn)今學(xué)者之水準(zhǔn)來苛求古人,兩百年前翁氏能撰編這本佳作已是十分可貴。毋庸置疑《古泉匯考》也是一座古泉資料庫,它有待我們?nèi)グl(fā)掘,整理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