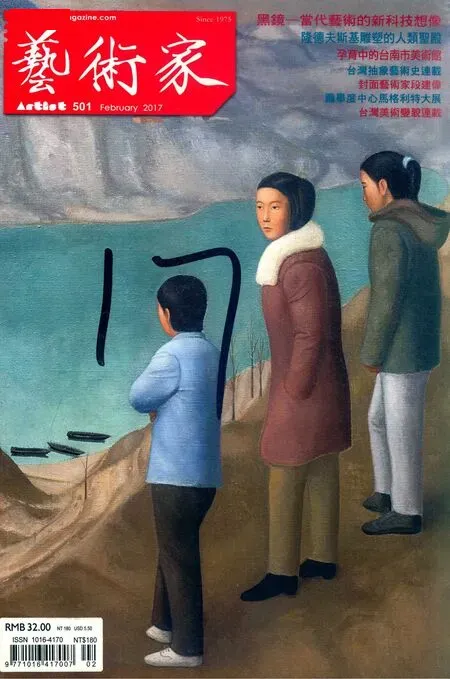隔離與人文關懷
——論張煬油畫風景創作
□亓文平
隔離與人文關懷
——論張煬油畫風景創作
□亓文平
盡管油畫風景畫只是張煬繪畫創作中的小部分,但是一如他的人物畫創作,作品完整、深刻而成系列。品讀其畫,我們很容易被其獨特的語言形式所吸引,司空見慣的景物背后往往流露出某種隔離和情懷,這種獨特的氣質總能把觀者帶到哲學思辨的境地。但是如此厚重的歷史沉思卻被畫家以一種嬉戲、輕松的畫面表現出來,這足以彰顯出張煬繪畫中的智性。
張煬自我繪畫語言的形成以及對社會、歷史的思索于北京的生活學習期間就初露端倪。20世紀90年代初,張煬在中央美院研修班學習,他和張洹、王世華、馬六明等畫家組建北京東村藝術區,如同蒙馬特的“洗衣船”,這里逐漸成為藝術家的圣地,那時張煬就認識到自由、獨立對藝術家的重要性,即使今天張煬在上海組建工作室,當初的藝術理想依然清晰可見。從某種程度上說,他用一種批判的眼光看待整個社會和自然,這種認識折射到他的風景畫作品,便成為一種學術品質,即如陳寅恪所說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他的作品顯得深刻而厚重。早期的油畫風景《大陵系列》《觸動西部系列》便具有這樣的特質。

張煬 《龍山景象》 100x80厘米

張煬 《觸動西部》 120×80厘米

張煬 《觸動西部》 100×62厘米

張煬 《觸動西部》 120×80厘米
這兩個系列不是對景寫生,而是帶有很強的觀念創作意味。畫家借助中國皇帝陵墓和西部風光這些母題,繼而融入一些超現實的元素,使我們熟悉的景物產生一種別樣的感受。細讀《觸動西部系列》,盡管大多數給人的是一種驚鴻一瞥的視覺呈現,但是畫面混沌有力的律動感足以給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畫家通過利用從現實場景中歸納的一些直線、圓形、三角形來構成畫面,繼而利用奔放而厚重的筆觸以及交織的顏色豐富畫面,因此情感傳達顯得更為干脆、直接。那些殘缺的山體、穿山而過的高架橋以及群山環抱中的攔河大壩似乎在提醒觀者,這就是人類的命運進程,換句話說,現代文明的發展既是對人類社會的推進,也帶來了巨大的精神危機,由此我們也會驚嘆于畫家眼睛的深邃,僅此一瞥,卻窺探到了人類命運最薄弱的環節。
對于人類自身命運和歷史的反思,我們可以追溯到張煬更早的《大陵》系列。在這一系列創作中,畫家用一種獨特的語言構建起特定的歷史空間,陵墓兩旁的柏樹如同落滿了火山噴發后的灰霾,冰冷而沉寂,陵前的雕塑安靜又似乎在訴說,強烈的透視給人一種空曠而又隔離的感覺。畫家通過荒蕪的田地一直把觀者的視線引向遠處的群山,觀者的思緒隨著視線的轉移縹緲于天地間,直到一道莫名光束打破這荒蕪和靜寂——這或許是畫家最獨特的語言象征,它似乎穿越了時空,顯得那么突然、銳利、震撼,這使得整體肅穆、沉寂的畫面一下騷動起來,使觀者情不自禁地聯想到歷史的滄桑變化。畫家利用幾種顏色分割畫面,前景的高級銀灰和遠景的濃烈彩色對比產生了一種獨特的意境。這種意境使我想到李白的詩句“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此時,個人的憂愁完全被拋開了,或者說融入了歷史的憂愁之中,畫家通過對歷史遺跡的重構,進入了歷史的反思。古道悠悠,音塵杳然,繁華、奢侈、縱欲,一切都被埋葬了,只剩下陵墓相伴如血的殘陽,百年、千年地存在下去。作者不是在憑吊秦皇漢武,他是在反思歷史和現實。這里交雜著盛與衰、古與今、悲與歡的反思。
這種對歷史的情懷也影響了張煬的寫生作品。從某種程度上說,張煬的風景寫生既不是地貌的自然展現,也非忽視客觀的主觀想象,更多是他個人心性的流露,是通過客體對于現實的哲思,因此,他的寫生作品給人大氣而質樸、厚重而現代的格局。近期嶗山風景寫生系列便是其中的代表。這一系列作品畫面突出了構成關系,畫家把嶗山石抽離成各種幾何形的造型語言,畫面仍然采用他擅長的框架式的結構,利用點線面來構成美的因素。我想他的這些思考一定和胡塞爾的觀點不盡相同,后者認為持“自然主義”思想觀點的人將我們認識的對象和認識的可能性都視為現成給予的和不成問題的。所以,這樣的認識和思考從一開始就已經處在某種前提規定的框架中,而缺少一種體驗的和反思的徹底性。因此,現象學把問題的本質引向心理現象,他們認為的聽和看不是物理現象,而是一種意向性活動,是對內在對象的指向和提現。張煬所看到的和聽到的嶗山,一定是經過他心理感應進而理性歸納的嶗山,而絕非現實意義上的客觀展現。

張煬 《大陵》 330×215厘米

張煬 《嶗山紀行》系列 70×70厘米

張煬 《嶗山紀行》系列 70×70厘米

張煬 《嶗山紀行》系列 70×70厘米

張煬 《嶗山紀行》系列 70×70厘米
正是這種思考,張煬的繪畫在當下更具有自我的標識性,張煬說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越來越喜歡樸拙有力、簡潔而富有內涵的作品。換句話說,張煬越來越關注的是現象背后所帶給人的心靈體驗,也就是現象學所說的“到事情本身中去”,這或許更加接近事物的真實和本質。他通過對現實景物的隔離最終喚起人們對于自然的人文關懷,我覺得這是張煬油畫風景的價值所在。
張煬的風景畫一如其為人,灑脫自由而不乏一種嚴肅感,一旦接觸,初似平淡,但往往回想起來所蘊含的豐富便一點點流露出來,從而讓人印象深刻。其實對其人其畫概括最好的莫過于著名批評家崔大中所說:“張煬并不是一個激進的自由斗士,他靜觀著蕓蕓眾生的焦慮、困惑和恐懼,審視著自己內心的焦灼不安。他從自己的感受出發,選擇描述知識分子的現代困境,描述社會的急速發展變化給國民帶來的沖擊和不適。關注自己的心靈世界,關注傳統與現代,關注自然與宇宙的奧秘,關注生與死、愛與恨、未來與夢想。因為這些,是人類世界永恒的主題。”

張煬 《南國》 80×65厘米

張 煬
曲阜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山東美協油畫藝委會副主任。山東油畫學會藝委會委員、常務理事。現居上海從事藝術創作。2000年在曲阜師范大學美術館舉辦“都市人格”主題個展,2011年在北京上上美術館舉辦個展,2016年在上海阿虛博物館舉辦個展,2017年在北京今日美術館參加“融——當代油畫語言研究展”。作品多次參加國內外當代藝術群展,并被美術館、藝術機構及個人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