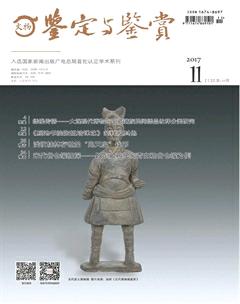元代黑陶俑鑒賞
趙昕



【摘 要】蒙元時期是中國空前的大一統時期,陪葬陶俑獨具藝術特點。本文通過對黑龍江省博物館收藏的四尊元代陶俑的鑒賞,了解元代陶俑的藝術造型特點和元代民間服飾流行特征。
【關鍵詞】元代陶俑 服飾 藝術
“俑”是古人用來陪葬的偶像,代替活人、活畜殉葬,質地以陶質居多。陶俑的制作從新石器時代就開始萌芽,一直延續到明清時期。但是隨著扎紙隨葬品的興起,用陶俑陪葬的習俗從宋元時期逐漸開始沒落。蒙元時期應該算是陶俑藝術的最后一個絢爛高峰。
蒙元時期,統治者是來自北方草原的蒙古族。蒙古先民喪葬習俗是薄葬不立墓冢,因此陪葬品很少。由成吉思汗統一各部并建立了蒙古汗國到忽必烈建立元朝,結束了宋遼金時期的分裂,中國又一次出現大一統局面。隨著民族融合,喪葬習俗逐漸漢化,但是隨葬品依然不十分豐厚。蒙元時期陶俑出土的也不多,所以顯得十分珍貴。西安是一座千年古城,歷經十三朝的古都,埋藏在它周圍的陶俑,無論是數量,還是題材,或是類型,對其他地域來說都無出其右。黑龍江省博物館有幸收藏了四尊來自西安的元代人物造型黑陶俑,讓我們穿越歷史,領略元代陶俑的藝術魅力。
一、元代仕女黑陶俑
1964年出土于西安南郊,高22厘米,色黑質堅,表面雖然無彩繪,但是散發著元代黑陶獨有的光澤。女俑微微頷首,成操手站立姿態。頭頂束盤花發髻,面部圓潤,五官清秀,耳大有輪,神態祥和。身著襦裙,上衣交領左衽,窄袖。下裙曳地,系有飄帶,未見足部外露,服飾紋路刻畫精細(圖1)。
元代社會等級森嚴,服飾區別有嚴格的法律規定,蒙古族的發型服飾與其他民族有很大不同。當時蒙古貴族婦女流行一種叫“罟罟冠”的帽冠,其底部為圓筒形,頂端呈正方形,從底部到頂端不斷加粗。冠筒用樺木、樹皮、竹子等材料制作內胎,外飾奪目的珠玉,是蒙古族婦女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不允許其他民族婦女使用的。
而元代漢人和南人成年婦女的發式沿襲遼宋時期的發式,流行堆髻,頭發中分編成發辮,盤于頭頂,有的還在發髻外罩上包巾。未婚少女一般是耳后梳雙丫髻。
蒙元時期蒙古族婦女同蒙古族男子一樣穿長袍,歐洲教士加賓尼13世紀40年代出使蒙古,對蒙古婦女的著裝這樣描述:“已經結婚的婦女穿一種非常寬松的長袍,在前面開口至底部……要把沒有結過婚的婦女和年輕姑娘同男人區別開來是困難的,因為在每一方面,她們穿的衣服都是同男人一樣的。”[1]長袍的系結方式規定并不十分嚴格,一般交領右衽,也有左衽。
而漢人和南人婦女的裝束基本沿襲唐宋風俗,上著襦衫,下系長裙,外罩半臂。上衣交領左衽。半袖在唐初已經開始流行,這種裝束除了保暖,也能遮蓋臃腫的體態,為年輕女子所喜愛。
所以,從發型服飾來看,這尊仕女俑可能刻畫的是一位漢人或南人婦女,身份應該是墓主人的侍女。
二、元代武士黑陶俑
1957年西安南郊出土,通高33厘米,顏色灰黑,質地堅實,表面無彩繪,呈站立姿態。頭戴叉形平巾幘,眉目刻畫清晰,五官清秀,耳部大且輪廓明顯。身著圓領、窄袖齊膝辮線短袍,腹部系有腰帶,衣袍前襟撩起挽于腰后。左臂曲肘,呈持握狀,左手似握有兵器狀;右臂向后擺動,手被袍袖遮擋,袍袖似被風吹動,十分靈動。雙腿岔開,褲下穿綁腿靴,站立在底座上。整個俑的姿態昂首挺胸,有威懾力(圖2)。
古代男子成人行冠禮,冠類型多種多樣。這尊陶俑所戴類似冠帽的頭巾名為平巾幘,是一種頂平且于腦后呈冠耳狀的包頭巾。這種裝束通常襯于武士冠之下,從魏晉時期已經開始流行,又稱“平上幘”“平巾”“平幘”。關中地區的考古出土的陶俑中發現有叉形與豎角形兩種平巾幘。這尊陶俑佩戴的是叉形平巾幘,頂部呈圓形,兩耳于腦后高高豎起,向兩旁傾斜,幘的兩耳略顯平緩呈“叉形”。蔡邕《獨斷》中提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點明了著平巾幘之人的身份和地位。
這尊陶俑戴這種平巾幘,身穿圓領的齊膝辮線袍,腰束帶,腳蹬靴,從其裝束來看,應為蒙元時期的侍衛武士形象。
三、元代男仆黑陶俑
1964年出土于西安南郊,通高26厘米,色黑質堅,頭帶裹巾,面部刻畫尤為精細。丹鳳眼,眼部內凹,耳大有輪,鼻梁較短,山根較低,準頭扁平,顴骨略高,下頜圓潤且短。陶俑從頸部斷裂后經修復,微頷首,低眉順目,身著辮線袍,腰系大帶,于身后打結。右手握拳,左手袍袖飄逸地向身后飄擺。下身著袴,腳穿圓頭云鞋。從種種面部特征來看,這尊陶俑應是一位蒙古族少年,身份應為墓主的高等級仆從(圖3)。
蒙古族男子的袍服種類分為質孫服、辮線襖、比肩等。質孫服本為軍服,到了元代將質孫服定為內廷大宴的禮服,為蒙族貴族男子的著裝。而辮線袍則是蒙元時期民間最為流行的袍服,或稱辮線袍,也叫腰線襖子。這種袍服最早出現于遼金時期,廣泛穿著于元代。最初為身份卑微的侍從和衛士的裝束。這種袍服上緊下松,窄袖束腰,上衣下裳,腰部作辮線細褶,使下擺寬度增大,呈裙狀,便于騎射,利于保暖。腰線的做法是把本身的面料加以打褶而成,也有用絲綢等其他材料做線后再綴于衣服上等方式。袍前后腰線的系結方式也有很多種,系扣是辮線最多見的系結方式,也有系帶式和扣帶混合式。
元朝的創立者為蒙古游牧民族,辮線袍服上身緊窄,使人們在騎馬射箭時上身活動靈活自如,下身寬松則易于上馬下馬,腰部辮線有力地支撐腰部背部,使穿著者騎馬射箭時更為舒適。這種袍服的產生和流行與游牧民族的生活習慣達到了高度的統一,不得不佩服古代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
四、元代牽馬男仆黑陶俑
1961年出土于西安北郊,陶俑通高28厘米,表面無彩繪,色灰黑,質地致密。陶俑頭戴寬沿鈸形笠帽,帽可與陶俑頭部分離。男俑發型為典型的元代“婆焦”“不狼兒”發式,單辮挽髻,發髻部分脫落。面部五官刻畫精細,眼部有“蒙古褶”,鼻梁短而塌,唇部較厚,下頜圓潤,神態生動。身著一色長袍,右衽,連衣褶都刻畫的十分精細。右手向右前方伸出,似要去抓住韁繩,左臂屈于胸前,左手隱于袍袖中,有腰帶束腰。長袍長及小腿下部,兩腿叉開,腳上似乎穿著尖頭靴。整個陶俑昂首直立,塑于一方形底座上(圖4)。endprint
蒙古族傳統的冠服為“冬帽夏笠”。蒙元時期,蒙古族男子經常佩戴一種用竹篾、藤條等編成的涼帽,帽外罩絹紗,因其形似鐃鈸,故稱之為鈸笠。這尊牽馬陶俑所戴的鈸笠帽,其帽檐伸出且傾斜向下,帽有頂,帽頂有短穗,戴這種笠帽的陶俑在關中地區元代墓葬中比較常見。鈸笠在元代帝王畫像中出鏡率也非常高,在汪世顯墓等元代家族墓中更有鈸笠的實物出土,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男子都著此帽,可見這種鈸笠帽在元代非常流行。貴族笠帽頂上多裝飾珠玉寶石。《元史·輿服志》中記載的“七寶重頂冠”,就是元朝皇帝佩戴的鈸笠。而平民所帶的鈸笠帽就簡樸的多,基本沒有什么裝飾物,僅內輔以織物,增加笠帽的舒適感。鈸笠帽的樣式也很多,有寬沿的,如上述這尊黑龍江省博物館收藏的元代牽馬男仆黑陶俑所戴的款式,遮陽效果較好,也許就是現代遮陽帽的前身。也有帽檐較短,雖不及寬沿笠帽的遮陽效果好,但是不遮擋視線,造型輕便,更加便于騎射。有的帽后帶有帔巾,還有的頂部帶纓。原來生活在蒙元時期的人們也都在追求新潮。
蒙元時期,蒙古族男子的發型特點是髡發和辮發。髡發,即剃發。蒙元統治者雖然曾下令讓其他民族也實行髡發,但卻沒像清朝統治者推行髡發制度那樣血腥的鎮壓。古代北方少數民族均有髡發的習俗,他們都是以游牧為主的民族,只是髡發的部位略有不同。這不僅是民族之間審美的差異,更是在戰斗中區別敵我的重要標志。而元代的漢族男子還是保留著蓄發的習慣,所以從發型上就能區別出一個人的民族。這尊陶俑所戴的笠帽能與頭部分離,能看到男俑的發式,其額前留有一撮“桃子狀”散發,為典型的“婆焦”發式,所以這尊陶俑表現的是蒙古族男子形象。
蒙元時期,男子袍服以右衽為主,窄袖便于騎射,下擺寬大便于腿部活動,長度從過膝到及腳踝部的款式都有。長袍開口在前方,右側有扣。在穿著袍服時,服外腰部系腰帶,稱之為“腰線”或“系腰”。腰帶用紅或紫帛捻成,色彩鮮艷,比較美觀,同時束住寬大的袍身,利于上身保暖和方便下身騎馬。這種袍服一直沿用至今,如今蒙古族牧民還在穿著這種長袍。
蒙古元朝是中國少有的空前的大一統時期,各民族乃至世界文化都在那個時期相互間不斷的影響與交融。這四尊元代黑陶俑穿越歷史來到我們面前,展示了那個繁華時代人們日常的服飾潮流以及對美的追求,也讓我們感受到了一個帝國的對其他民族和文化乃至世界的包容和影響。對于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繁榮和共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意大利)加賓尼.蒙古史[M]//道森.出使蒙古記.呂浦譯,周良宵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