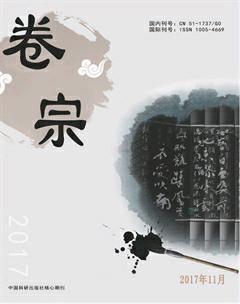道具在芭蕾舞劇中的功能
摘 要:在芭蕾舞劇中,道具雖然是演員身外的次要元素,但因其自身獨特的功能,卻能協助演員,吸引觀眾,為舞劇増光添彩。概括而言,道具對于芭蕾舞劇能夠起到類似文學寫作手法的"借物抒情、以物象征、承上啟下、渲染氣氛"等作用。
關鍵詞:道具;芭蕾舞劇;功能
1 道具概述
(一)道具含義與分來
“道具”源于佛教用語,指修行者使用的衣物、器具。唐代嚴維的《送桃巖成上人歸本寺》詩;“道具門人捧,齋糧谷鳥銜。”宋代惠洪的《冷齋夜話-石崖僧》:“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為誰?”在中國傳統戲曲中道具被稱為“徹末”,其實“徹末”是包含桌、椅、帷幕、布城、山片等在內的廣泛概念。后來,“道具”一詞被普遍應用于各種表演藝術之中,與表演密不可分,不大容易劃定其精確的范圍。多年來,約定俗成、大家認同的道具一般是指表演情境中設置的,幫助演員完成表演的各種器物,統稱為道具,諸如舞臺上除布景、服裝、燈光裝置之外的家具、臺燈、花瓶、煙灰缸等等。
不同表演形式中,道具各有特性,對道具的稱呼也不盡相同,但是各個表演行當和觀眾都認同以下幾點:第一,道具是表演情境中的器物,絕不是舞臺上的多余物件,而是協助完成表演必須的器物;第二,道具可以是實物,但更多的是舞美人員設計制作的仿制器物,有實物的形象,滿足表演的需要;第三,抽象化離形表意器物也是道具,比如戲劇中用馬鞭代替馬,畫兩個輪子的兩面小旗就是車。
總之,用于舞臺表演的器物,就叫道具。這是對道具的最基本、最重要、最本質的認識。從使用功能上劃分,道具一般可分為個人道具、象征道具、實用道具等幾類。從材質特性上劃分,道具一般可分為真實道具、模仿道具。真實器物被用于表演,就成了道具,離開了舞臺,它們仍然是普通器物,如生活中的壇子、罐子、雨傘,在舞臺上耍起來,都成了道具。但更多的道具是根據場景、情節、人物的需要而制作的,所以,它們多是模仿實物、便于表演的器物。
(二)道具和芭蕾舞
從芭蕾發展史來看,道具的確很早就與其結下了不解之緣。早在十五世紀,意大利和法國宮廷宴席中舉行的“席間芭蕾”,就曾把精美的刀叉等餐具裝在天鵝絨的袋子里,用作舞蹈的道具。而在被譽為“第一部完整的芭蕾舞劇”的《皇后喜劇芭蕾》中,宏大的布景、華麗的彩車,以及許多奢華的器具,都成了這部紙醉金迷芭蕾舞劇中不可缺少的大小道具。其后,各個階段的芭蕾舞劇也都離不開道具的陪伴;僅從舞劇的名稱,我們就可見一斑。其中以道具命名的就有歐洲古典芭蕾舞劇的代表作《胡桃夾子》,現代芭蕾舞劇的代表作《三角帽》、《寶石花》,中國當代芭蕾舞劇的代表作《大紅燈籠高高掛》等。這些夾子、帽子、寶物、燈籠無不將場景、情節、演員、動作結合為一個整體,并帶給觀眾別具一格的感受。在中國現代芭蕾舞劇的代表作中,《紅色娘子軍》的道具設計和使用更是堪稱一絕。如在《萬泉河水》這個舞段中,編導加用了海南島人民日常生活的斗笠作為道具,讓女子們一對一對地從舞臺中央升起,恰如其分地表現了解放了的海南島人民對于紅軍發自內心的愛戴之情。眾多應用道具的芭蕾舞劇不一而足。
2 道具在芭蕾舞劇中的功能
(一)借物抒情
借物抒情是通過描寫客觀事物,直接抒發人的思想感情的寫作方法。唐朝杜甫《春望》詩中“感時花滿淚,恨別鳥驚心”,就是借物抒情的典型。作者以春天原本美好的花鳥,反襯出國家遭遇“安史之亂”,民不聊生,個人也是命運多舛的悲痛之情。同樣,道具也有相似功能。舞蹈是“長于抒情”的形體藝術,舞蹈道具亦可以用來表達舞者的內心情感。喜怒哀樂是人最常見的情緒,通過道具能將它們表現得淋漓盡致。快樂時,源于日常生活的道具無不攜帶著愉悅,仿佛舞蹈者歡聲笑語的洋溢:如舞蹈伴隨著花朵(《海盜》、《睡美人》、《胡桃夾子》);少女拿著斗笠起舞(《紅色娘子軍》);喜兒舞動著窗花和紅頭繩(《白毛女》)。痛苦時,特定情景下的道具無不訴說著悲憤,好像主人公備受煎熬的內心:如瘋狂作舞、足以致人于死命的佩劍(《吉賽爾》);變幻莫測、扭曲拉動的手帕(《奧賽羅》、《大紅巧籠高高掛》)等等。還有芭蕾舞劇《關不住的女兒》中的《鍛帶雙人舞》,《艾斯米拉達》中的《手鼓雙人舞》,《舞姬》中的《紗巾雙人舞》等,都是男女同時拿著道具手舞足蹈,表現出雙方的友好信任或感情的交流。在改編自塞萬提斯同名小說的俄羅斯古典芭蕾舞劇《堂吉巧德》中,男女演員分別使用手鼓與紅綢這兩種道具跳舞,動靜之間的反差將二人的喜悅心境和深情厚誼表現得清晰易懂,并讓演員與觀眾都能沉浸其中,享受青春的美好與愛情的甘甜。
(二)以物象征
以物象征是文藝創作的一種表現手法,指通過某一特定的具體形象來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種較為普遍的意義,利用象征物與被象征的內容在特定經驗條件下的類似和聯系,使后者得到強烈的表現。唐代黃巢《不第后賦菊》詩:“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以秋菊象征了農民起義軍,以菊花的繁盛,代表了未來農民軍的聲勢浩大,以菊花的金黃,比擬了義軍身披錯甲、熠熠生輝的威武形象。芭蕾舞劇也是文藝的一種,象征手法自然應用于道具。芭蕾是用整個身體去傳情達意的動作藝術,屬于“非文字語言”藝術的范疇。比起戲劇、小說這些文字藝術,想要使觀舞者順利地理解舞劇傳遞的意圖,就需要借助有形的道具象征某些無形的精神和事物,而物象征則成為道具的重要功能。
在許多西方芭蕾舞劇中,玫瑰花都象征著愛情,如古典芭蕾舞劇《堂吉巧德》、現代芭蕾舞劇《玫瑰花魂》、《羅密歐與朱麗葉》等;而佩劍則是權力的象征,如在浪漫芭蕾舞劇《吉賽爾》、《艾斯米拉達》中等。在芭蕾舞劇《卡門》中,椅子就是典型的象征物。舞蹈演員通過扶椅背伸腿,正步吸起小腿同時抒身踏步,后坐在椅子上,腳尖踏在椅子上等動作,與椅子形成了對話,表現出卡門的人物性格及其內心世界。扶著椅子好像是對它的依賴,坐在椅上是對它的占有,踏在椅子上是對它的征服,椅子起到了象征人的作用。又如,在我國的芭蕾舞劇《八女投江》中,將白楊樹作為東北艱苦環境和戰士們頑強精神的象征,不禁讓我們想起了《白楊禮贊》一文的寓意。該劇把東北常見的不懼嚴寒、傲然挺立的白楊樹當作舞具,讓戰±們手持白楊樹枝,支撐著身體,配合著動作,走步、蓋腿、片腿、下蹲,生動地體現出他們不畏艱險、勇往直前的堅強意志。endprint
(三)承上啟下
承上啟下是語文課本中最常講的寫作方法,指的是“接續上面的,并引起下面的過渡句或過渡段”。宋代張炎說;“思量頭如何起,尾如何結,方始選韻,而后述曲,最是過片不要斷了曲意,須要承上啟下。”道具可在芭蕾舞劇中引起情節的前后轉折,或“常常能看到一件道具貫穿舞蹈作品始終”,其功能都是“承上啟下”。這樣才能使被場幕分割的舞劇劇情不會支離破碎,形成一個連貫的敘事整體,給觀眾留下完整的故事印象。在《關不住的女兒》中,麥秸捆的到來表明了該劇“由悲轉喜”,將要發生“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局面。而在《吉賽爾》中,佩劍的出現則是“由喜轉悲”的開始,預示了女主人公的悲劇命運。麥秸捆和佩劍雖然扮演了不同的“轉折角色”,但都起到了承上啟下的功用。在根據莎士比亞名作改編的芭蕾舞劇《奧賽羅》中,從奧賽羅與苔絲德蒙娜之間的相識、相戀到前者聽信讒言,由愛生恨,直至將后者勒死,這一系列復雜的感情經歷,均是用手絹這個道具與舞蹈動作的恰當配合來貫穿和完成的。
在講述民間音樂家阿炳故事的芭蕾舞劇《二泉映月》中,作為標志性道具的二胡也貫穿了四幕的始終,其音樂形成的背景,二胡的形態與音色,均對故事的發生、舞蹈的發展、感情的傳遞、人物的塑造,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渲染氣氛
渣染氣氛是在文學敘事過程中,作者通過刻畫事件發生的環境、當時的場面、整體的氛圍,凸顯作者本人、或文中人物獨特的情緒、心理、感受、情感,給讀者以身臨其境的感覺,誘發讀者的情感共鳴,増強文章感染力的一種技法。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便突出了對色彩、時空的渲染,傳達了作者愉快、豁達的內心境界。而氣氛也是芭蕾舞劇在敘事時必不可少的外部環境,為了展現故事情節、烘托演員主體,必須營造特定的環境,道具就在其中派上了用場,起到“渲染氣氛”的功能,中外芭蕾舞劇中皆有例證。比如,我國的芭蕾舞劇《大紅燈籠高高掛》中,運用了燈籠、手絹、折扇、屏風等中國特色的道具,凸顯了傳統民族文化環境,尤其是那高懸密布的盞盞紅燈籠,不僅在色彩上展現了當時的年代特征,更有腐朽沒落、禁錮人性的象征意義,是以暖色調反襯悲劇的典型。在《堂吉河德》中,理發師巴塞爾手持酒杯與舞蹈動作完美配合,便展現出演員與角色的雙重忘我狀態、精湛的技巧和幽默的性格。他雙手持酒杯表演的芭蕾舞步,如追步跳、空轉、小舞姿轉,直到最后把酒杯倒過來,拿在七位手的位置上一松手,讓酒杯掉在地上才結束。舞蹈中,演員雖然沒喝酒,卻讓觀眾感到他真的喝了,而且喝后的狀態比沒喝之前更加興奮,由此將酒館這一幕的氣氛推向了高潮。在古典芭蕾舞劇《舞姬》中,印度社會常見的花籃、羽毛、紗巾、水罐和演員優美的蛇舞相互配合,營造出印度神廟祭祀的神秘氛圍,令人產生身臨其境的異域感,其道具的功能達到了新的境界。
參考文獻
[1]王娜.陳翹舞蹈作品中道具的運用[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4-3.
[2]楊楠.試論戲劇表演對芭蕾舞表演人才培養的重要性[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5-6
[3]李曉梅.淺析芭蕾舞《榮莉花》在表現形式上的創新[J].陜西教育(高教版):2015-8
作者簡介
劉峰(1985-),男,漢族,陜西西安人,重慶人文科技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芭蕾基訓,民族民間舞。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