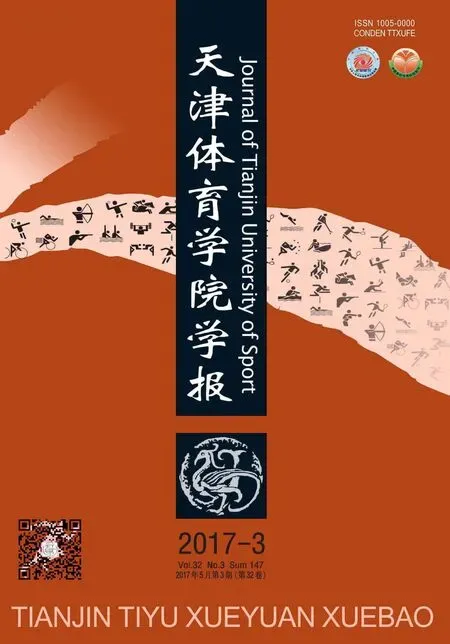我國俱樂部與職業運動員法律關系的困境與出路
——以從屬性理論為視角
李志鍇
我國俱樂部與職業運動員法律關系的困境與出路
——以從屬性理論為視角
李志鍇
長期以來對職業運動員勞動者身份的爭議,實際是俱樂部留人體制與我國《勞動法》存在沖突,并缺乏相應的利益補償機制所致。在“資強勞弱”的思維模式下,我國判斷勞動關系采用的從屬性理論僅包含“是否”一重,只存在不保護和全保護2種選擇,并不考慮勞資雙方實際力量的對比。然而,從屬性并不是僵化的判斷標準,而是一直在隨著社會變化而發展。既要實現擴大勞動保護范圍又要避免不公平,就必須對勞資雙方實際力量的變化給予回應,德國法上“類雇員”只享受有限勞動法保護等制度安排正是基于勞資利益均衡的考慮。優秀職業運動員的不可替代性降低了其人格依附的必要性,可能出現只存在經濟從屬性而無人格從屬性等情況。當一個俱樂部想從其他俱樂部獲得優秀職業運動員時,實際就是想獲得這種不可替代性,并占有其他俱樂部的前期投入。我國勞動法對職業競技體育中勞資雙方的力量變化和訴求缺乏回應,導致利益安排失衡,勞資談判體系的孱弱、資本的介入和強勢的行政機構則進一步加劇了沖突。應當將《勞動法》與《體育法》相結合,構建包含“是否”和“強弱”相結合的從屬性理論雙重判定模式,以保證體育市場的公正性,實現人才的有序流動和勞資共贏。
職業運動員;俱樂部;從屬性;權利平衡
2015年,張梓健等足球職業運動員要求與沈陽東進足球俱樂部解除合同,勞動仲裁委認為不屬于勞動仲裁受案范圍,一審法院認為雙方已約定了仲裁條款不屬于法院管轄,2016年二審法院則以該案屬于勞動糾紛案件將案件發回重審[1]。該案一波三折,歷經近2年的時間又重新回到起點,案件的核心問題是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間的法律關系,這與2014年引發廣泛爭議的籃球職業運動員吳冠希與奧神職業籃球俱樂部糾紛相似。在討論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法律關系的同時,應當反思目前俱樂部留人機制與我國勞動法法律體系間是否存在沖突。因此,本文試圖以《勞動法》與《體育法》相結合的視角,通過對從屬性理論的進一步解釋探討問題的解決之道。
1 理論分歧
1.1 對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關系的認識分歧
原勞動部于1992年頒布的《關于界定文藝工作者、運動員、藝徒概念的通知》規定,“運動員,系指專門從事某項體育運動訓練和參加比賽的人員”。我國運動員包括職業運動員、業余運動員和事業編制中的專業運動員。在建國后相當長時間的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只有編制內的運動員和業余運動員,職業運動員是我國體育市場化、職業化和產業化后產生的概念。我國法律并未對職業運動員進行明確的定義,職業運動員主要是指從事現代職業運動比賽,并以其為主要職業的運動員,具備經過體育行政管理部門批準注冊、與俱樂部建立合同關系和以體育運動為主要謀生手段等3個基本特點[2]。
理論界對職業運動員身份一直存在爭議,相應的糾紛層出不窮,如吳冠希事件、張琦事件、馬健事件等。當前主要有兩派理論:一派認為,職業運動員屬于勞動者,雙方為勞動關系;另一派認為,職業運動存在特殊性,職業運動員的從屬性較低,雙方應為《合同法》規定的雇傭關系。目前,主張雇傭關系的學者視角集中在足球、籃球特定領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分類大典(2015版)》第2-11-01-03條規定,運動員系“從事球類、田徑、體操、游泳、棋牌類等運動項目訓練和比賽的專業人員”。職業運動員的范圍顯然不限于足球、籃球,若按照雇傭關系理論,則所有的職業運動員都不受《勞動法》保護,這顯然損害了廣大職業運動員的利益,也與常識不符。因此,主張勞動關系的逐漸成為通說[3]。
1.2 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關系認識分歧的實質
不容忽視的是,雇傭關系派反對勞動關系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客觀存在的,既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有可能使轉會制度、FIFA的管理體制形同虛設,俱樂部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護[4]。雇傭關系派列舉的觀點包括:《勞動法》第3條規定,“勞動者有選擇職業的權利”,俱樂部可以派遣職業運動員去其他單位工作,但是無權要求職業運動員與其他俱樂部簽訂合同;《勞動合同法》第37條規定,勞動者提前30日通知用人單位便可單方解除勞動合同,轉會費存在的客觀基礎便會喪失;《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第16條將損失限制在有限的直接損失內等。筆者認為,雇傭關系派的論據恰恰體現了其主要的顧慮,換而言之,雇傭關系派提出的實際問題是:“在現行勞動法框架下,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間是否存在利益安排失衡”。
2 從屬性理論視野下的職業運動員身份判定
2.1 從屬性理論的歷史與現狀
以德國為代表的國家采用從屬性理論,將勞動者定義為“不獨立的、由他人決定而給付勞動的人是勞動者”[5],勞動者在人身、財產上與雇主之間存在從屬性的關系是判斷勞動關系的基本依據。英美法采用的是依附性理論,該理論認為,勞動關系當中除了契約關系、財產關系外,還附著人身關系,這是基于勞動力和勞動者的身體不可分割決定的,這構成了勞動者依附理論的基礎。依附性理論本質上與從屬性理論內在契合。通說認為,“從屬性”是判斷勞動者的基礎,并采取人格從屬性與經濟從屬性相結合的標準[6]。人格從屬性是判斷的核心標準,指勞動者對雇主存在依附關系,受雇主支配與管理。經濟從屬性是指,勞動者按照雇主命令提供勞動后可以獲得報酬,并為其主要收入來源。
事實上,從屬性理論一直在隨著社會發展而變化。以德國法為例,20世紀初,德國帝國勞動法院曾經認為勞動關系的核心應當是經濟從屬性,但是后來人們便認識到經濟從屬性既不是勞動關系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7]。隨后,以人格從屬性為核心的勞動關系判斷標準在德國得到確立并沿用至今。但是,單以人格從屬性為核心的勞動關系判斷方式也存在問題。因為一方面不同勞動關系中人格從屬性強弱有別,更存在只有經濟從屬性而無人格從屬性的“類雇員”;另一方面,互聯網的發展打破了傳統勞動關系的時間和空間,對傳統勞動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死守傳統的判斷方式顯然不合時宜,德國應對之法包括以下3個方面。首先,根據部分勞動者從屬性減弱的事實,排除其特定的權利,如德國企業組織法和勞動時間條例不適用于高級職員,德國解雇保護法不適用于企業負責人、經理等有人事雇傭權和人事解雇權的人[8]。其次,采取解除管制的途徑,減低勞動保護法的水準,提高勞資自治水平,促使勞動契約制度彈性符合現實的多樣性[9]。最后,靈活運用從屬性理論,既擴大勞動保護范圍又避免不公平,如認定只有經濟從屬性的“類雇員”不是勞動者,但是可以享受一定的勞動法保護[5]。從屬性理論發展的原因是,現代勞動方式從傳統的工廠式勞動方式向多樣化勞動方式轉變,更重要的是,應當對勞資之間實力對比的現實情況予以回應,判斷從屬性不但需要判斷“是否”,還應當考察其“強弱”。
2.2 我國從屬性理論的運用與“資強勞弱”的思維定式
我國勞動法并未對勞動者進行定義,而是采用列舉式的方式確定勞動者概念的外延。根據2005年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頒布的《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第1條規定,只要勞資雙方具備相應的主體資格,“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并且勞動者的勞動構成用人單位業務的一部分,便可視為勞動關系成立。服從規章制度、從事用人單位安排和勞動構成用人單位業務一部分都屬于人格從屬性,以“用人”為核心的人格從屬性是我國勞動關系判斷的基礎。此外,我國不存在“類雇員”的概念,經濟從屬性在我國并不是一個獨立的判斷標準。我國對從屬性的認識有濃重的傳統工廠式特征,在傳統工廠時代,勞動者完全融入組織并受雇主控制,勞動者體現極強的人格從屬性。“用人單位”一詞,便隱含著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管理著勞動者生老病死的歷史印象。
在如此強的人格從屬性下,勞動者幾乎沒有議價的能力,必須傾向勞動者并嚴格約束雇主。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國《勞動合同法》一方面在立法安排上偏向勞動者,對勞動者大力實施保護,給予勞動者寬松的單方解除勞動合同的權利;另一方面,嚴格地限制了用人單位的權利,對違約金、用人單位解除勞動合同的條件等進行了嚴厲的限制。當然,我國《勞動合同法》如此向勞動者傾斜亦有特定歷史背景。改革開放之初,我國勞動保護薄弱,勞動力供給充足而資本缺乏,因此資本獲得了充分的議價權,形成了“資強勞弱”的格局并深入人心。2007年,有媒體報道山西部分磚廠對農民工實施非法拘禁,非法收買和使用童工、智障人員,強迫他們從事長時間、無報酬勞動,此事經互聯網發酵成為轟動全國的山西“黑磚窯事件”。當時《勞動合同法草案》仍然在膠著中,各方對服務期、就業限制等無法達成妥協,山西“黑磚窯事件”的殘酷對社會和全國人大產生了極大的刺激,使得原本在僵持中的《勞動合同法》在當年便以全票通過[10]。“黑磚窯”事件在促成《勞動合同法》通過的同時,也大大膨脹了“勞善資惡”的思維定式[11]。在傳統的工廠大生產中,工人被化為生產線上的零件,對勞動者實施傾斜性保護是正當的,但是就此認為所有的勞動關系都是如此顯然有失公允。
2.3 “資強勞弱”思維定式下我國職業運動員勞動者身份的認定
依據《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職業運動員只要加入俱樂部,服從俱樂部的規章制度和管理安排,其參加比賽構成俱樂部經營活動的一部分并從俱樂部獲得報酬,便符合人格從屬性的判定標準,可以認定勞動關系。此外,2016年7月,人社部等聯合下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職業俱樂部勞動保障管理的意見》明確指出:“俱樂部應與球員等勞動者依法簽訂勞動合同”,肯定了俱樂部與球員間的勞動關系。在我國現行的聯賽體制下,判定職業運動員的勞動者身份并不困難。然而,“現代立法其實質是一個利益識別、利益選擇、利益整合及利益表達的交涉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立法者旨在追求實現利益平衡”[12]。和諧的勞資關系有賴于勞資雙方的利益平衡,在解決了我國職業運動員的勞動者身份判定后,需要進一步思考“資強勞弱”的慣性思維是否與我國當前的職業體育發展相適應,俱樂部與職業運動員的利益是否平衡。
雖然,我國勞動法采用從屬性理論,但是“資強勞弱”的思維慣性下并不關注勞資雙方實力的平衡。“勞動合同立法時,立法部門面臨的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命題,可以簡單地以‘強資本、弱勞動’來闡述一切問題。《勞動合同法》對用人單位的解雇權做出了極其嚴厲的規定,而對勞動者的辭職權做出了異常寬松的制度安排,企業幾乎沒有留人的手段。”[13]俱樂部給予職業運動員地位和自主權,部分職業運動員在俱樂部內有較大的權力和重大的影響,《勞動法》對類似從屬性的變化并未予以認定。此外,優秀職業運動員的發掘、培養和鍛煉需要時間、金錢的投入,還要面對淘汰的風險,技戰術體系和團隊搭建培養也需要很大的投入。在信息為王,關注度和瀏覽量便是財富的時代,俱樂部會將財富集中到王牌選手身上以爭取產生光環效應。上述大量的前期投入產生了資本沉淀,《勞動合同法》對俱樂部可追討的直接損失進行了嚴格的限制,俱樂部對此難免會心存恐懼。
3 對我國職業運動員從屬性及相關問題的思考
3.1 職業運動員的不可替代性與從屬性
競技體育有其自身的特點,第1名和第2名的待遇往往天壤之別,甚至存在“贏者通吃”的情況。相較于普通職業運動員,明星職業運動員給俱樂部帶來了關注度、贊助等外部效益可以達幾何倍數。競技體育比賽的特點決定了可以上場的人員的名額是限定的,有天賦、有能力的職業運動員畢竟是有限的,屬于稀缺的優質資源。相關案例多集中在籃球、足球領域,只是因為這些領域市場化程度高、資本密集,其他運動領域爭議見報較少是因為其職業化水平低。優秀運動員的稀缺性在體制內也是一樣的,歷次全運會背后各省激勵的金牌斗爭和對優秀運動員的爭奪正是因為優秀運動員的稀缺性。因為歷史和體制的原因,并不能簡單地將大量編制內運動員的身份關系全部視為勞動關系,但是這并不影響優秀運動員的難以替代性。在我國目前的職業體育環境下,保護職業運動員的勞動者權益是正當的,但是是否保護與保護的程度及其法益相稱性并非同一法律問題。
“資強勞弱”背后的供給原理是資本較少而勞動力眾多,勞動者在選擇工作時可替代的選項較少,而資本可以選擇的勞動者較多,這便形成了資本的強勢。可替代性是構成人格從屬性的重要基礎,如果勞動者是可以被輕易替代,那么勞動者為了生存就不得不依賴于雇主,形成強烈的人格從屬性,并任由雇主壓低勞動條件。但是,如果勞動者是不可替代的,那么勞資雙方的“強弱”對比便會轉化,勞動者的人格從屬性會降低,勞資雙方更有可能形成彼此依賴的關系。勞動者對雇主的依附性越強,勞動法保護的力度就應當越大。相對的,勞動者對雇主的依附性越弱,勞動法保護的必要性便會越弱。越是在開放的職業運動領域,優秀運動員的不可替代性的價值就越明顯,正是因為這種不可替代性使得各俱樂部愿意出天價與運動員簽訂合同,同樣也是因為這種不可替代性使得俱樂部懼怕優秀運動員的流失。職業運動員的人格從屬性與其不可替代性有關,優秀職業運動員的不可替代性減低了其人格依附的必要性,在適當的市場環境下可能只存在經濟從屬性,而無人格從屬性。當一個俱樂部想從其他俱樂部獲得優秀職業運動員時,實際就是想獲得這種不可替代性。不同俱樂部之間存在爭奪優秀職業運動員的“資資矛盾”,當一個俱樂部想獲得其他俱樂部辛苦培養的職業運動員時,正常的方法是與原用人俱樂部談判并支付相應的對價補償。但是,當職業運動員有單方解除合同的權利時,想挖人的俱樂部便不需要再與原用人俱樂部談判,而只需要將職業運動員推向前臺,將俱樂部間挖人的“資資矛盾”轉化為名義上維護職業運動員勞動自由權利的“勞資矛盾”,便可獲得法律和輿論的支持,最終合法占有原用人俱樂部的前期投入。受制于聯賽體制和同行制約,我國未出現大規模職業運動員解除合同的跳槽現象,但是這種默契缺乏勞動法的支持,并容易形成權力壟斷。如2014年吳冠希與奧神俱樂部糾紛案,雖然吳冠希依據勞動法解除了勞動合同關系,但是中國藍協稱吳冠希注冊手續不全,使吳冠希喪失了參加2014—2015年聯賽的機會。客觀地說,這樣的結果對任何人都沒有益處,既損害了籃協、職業運動員團隊和俱樂部之間的相互信任,又降低了外界對整個籃球行業的評價。
3.2 勞動者合同解除權與俱樂部人才培養回報權的均衡性
我國《勞動法》中,勞動者的原型與傳統的工廠工人相接近,在傳統的工廠勞動中,用人單位可以對勞動者進行流水線式的培訓,時間和投入有限,相應成本可以很快被消化。因此,我國《勞動法》對違約金等進行嚴格限制,避免用人單位借此要挾勞動者并獲取不正當的利益。但是,優秀職業運動員需要挑選、培養和逐步成長的過程,這個過程當中需要俱樂部不斷地投入。優秀運動員具有天賦高、培養時間長、投資風險成本大、投資風險高等特點,這造就了運動員職業勞動技能的稀缺性[14-16]。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的關系不同于傳統的工廠式勞作,其關系更傾向于合作共贏,職業運動員的經濟從屬性較之人格從屬性更明顯。職業運動員合同解除權與俱樂部人才培養回報權并不矛盾,職業運動員有權依法解除勞動合同,但是其同樣應當遵守契約、職業道德和行業規范。勞動合同本質上是契約,美國職業籃球比賽的球員要在沒有合約或合約已滿后才能找新球隊,相應約束以狹義保護的視角而言是限制了球員合同解除權,但是其維護了賽事的良性發展,符合全體球員的整體和長遠利益。不考慮職業運動員從屬性的“強弱”和勞資利益平衡的“一刀切”式的保護行為是過度保護行為,并不符合全體職業運動員的利益。應當跳出狹義保護的視角,以職業體育整體性和職業運動員的流動性認識職業運動員利益,實現勞資權利均衡。
在職業體育領域,任意解除權在損害俱樂部利益的同時,變相損害了職業運動員的利益。我國《勞動法》在給予勞動者寬松的合同解除權的同時,嚴格限制用人單位的合同解除權,會對競技體育行業發展產生如下反向效果。俱樂部越難解除與職業運動員的關系,俱樂部就越愿意雇傭成熟、優秀的職業運動員,越不愿意承擔合同解除不能的風險來培養新人,新人就越難成長。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聘請外援的成效顯然快過新人培養,然而外援的強大僅是一個俱樂部的強大,并非競技體育行業的強大,沒有人才梯隊的建設就不會有行業長遠的發展。資本本無善惡,逐利為其天性。越是熱門的體育賽事其資本運作越發達,資本驅動對職業運動員流動產生重要影響。2016年,中國各足球俱樂部紛紛一擲千金,國內本土球員轉會費出現從未有過的天價,暴增到8 000萬人民幣[17],球員轉會費的一路水漲船高的主要原因是恒大、淘寶等資本加入足球市場。
3.3 職業體育集體談判的必要性及其缺失
以從屬性的角度,集體談判能夠聚集勞動者的力量,通過團結的方式將原來個人對企業的“資強勞弱”變為團體對企業的“勞資平等”,降低了勞動者的依附性,使其能夠真正表達自己的意思。考慮到不同行業存在巨大差異和當事人復雜的利益需求,世界各國都提倡通過集體談判確定勞動基準與合同條款,《世界勞工組織公約》和我國《勞動合同法》都有明確規定。政府俘虜理論指出,政府對經濟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形成政府自身利益,并容易被相應利益集團俘虜,因此讓勞資雙方自行決定既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則,又有利于避免“政府失靈”。
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之間處于微妙的利益格局當中。一方面,基于人性的特點,各主體都盡量爭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沖突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職業運動員和俱樂部處于同一個競技體育行業之中,在與同行、其他競技體育行業爭奪市場資源時雙方利益又是共同的,過多的沖突、丑聞將造成不良的社會觀感,損害行業利益。集體合同的有效簽訂有賴于成熟的工會與雇主協會,這些集體組織既具備相應的威信,能夠代表其團體利益,也有成熟的談判技巧和決斷能力。遺憾的是,我國至今尚未建立專門的職業運動員工會,缺乏罷工權的法律依據,工會行政化問題明顯難以獨立承擔勞資博弈的重擔。俱樂部首先要面對的談判對象并非勞工組織,或者說,勞工組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成為其主要問題。職業體育集體談判體系的孱弱迫使政府介入,而政府的不當介入又抑制勞資談判,進而陷入只能不斷加強行政管制的漩渦。
3.4 體育行政權的介入及其替代性
因為信息不對稱、壟斷等因素,體育市場可能存在“市場失靈”,妨礙俱樂部與職業運動員正常行使權利,因此需要政府進行適當的干預和調控。在舉國體制時代,我國體育行業的管理主要靠行政管制完成,以行政管制為主導的統合式政府管理模式沿用至今,形成了對行政權的路徑依賴。過于依賴行政權是我國長期以來的治理模式問題,為此《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現代社會治理就是政府、市場和社會各司其職,彼此合作[18]。體育行政部門的行政權的行使應當以體育行業的健康發展為目的,合法、合理和有度地行使權力,以政府服務市場而非以政府代替市場。
但是,目前我國的體育社團既要接受各級體育行政主管部門的“業務指導和管理”,又要接受民政登記部門的監管,形成了民政部門與體育主管部門結合雙重管理體制,行政權力交叉且深入體育行業。雖然,我國目前已經開始將行政管理部門與行業協會脫鉤,但是相應改革仍然在推行當中,如2015年,國家體育總局才開始與足協脫鉤,實際工作至2017年初才完成。我國體育行政管理部門仍然集指導、管理、處罰與制定相應規范的權力于一體,俱樂部可以切身感受到權力的威懾,俱樂部為了自身利益盡可能地去“俘虜”行政管理部門。部分體育行政管理部門仍然持有“管理既權力”的思維定式,缺乏服務型政府的思想,權力與金錢相會容易產生既得利益集團。既得利益集團通過行業管理規范、指導意見、資格審查等方式建造一套規制體系,職業運動員如果不服從管理便有可能喪失繼續從業的機會,這種威脅常常是無形的。
4 對策與建議
4.1 職業運動員從屬性理論的雙重判定模式
勞動法以勞動關系為其法律調整對象,具有糾正形式平等而實質不平等的勞動關系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從屬性理論的目的在于識別真正需要勞動法保護的勞動者,實現法律糾正不公,實現平等的法律價值。職業運動員的稀缺性、權利均衡性等因素都在影響職業運動員對俱樂部的依附程度。傾斜式保護是建立在“資強勞弱”的大命題之下的,但是如果實踐中不考慮實際情況,就失去了勞動法“雪中送炭”的目的,而變成了“錦上添花”。當前,我國以人格從屬性判斷職業運動員勞動者身份,卻不進一步通過其從屬性的實際強弱平衡俱樂部與職業運動員的權利義務,沒有考慮職業運動員稀缺性等重要影響因素,忽視了俱樂部正當的利益訴求。
職業運動員可以得到的保護應當是依據其從屬狀態決定的,不同的職業運動員的不可替代性是不一樣的,從屬性理論在“是否”的第一重判定外,還存在“強弱”的第二重判定。在職業體育領域,職業運動員的從屬性強弱應當結合稀缺性、淘汰風險等綜合判斷。首先,借助職業運動員不可替代性標準可以考察職業運動員人格從屬性的“強弱”。人格從屬性必須根據不同的職業、不同的經濟結構等進行總體評價,并沒有一個決定性的標準,德國聯邦勞動法院不得不針對不同的職業歸納一些認定勞動關系的規律[19]。優秀職業運動員往往是難以替代的,不可替代性直接影響其依附的程度,可以成為判斷職業運動員從屬性的基礎標準。其次,對職業運動員保護的“強弱”應與其從屬性“強弱”一致,確保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權利均衡。優秀職業運動員不可替代性強,其從屬性就弱,其權利便應當受到適當限制。職業體育淘汰率很高,到達金字塔頂的只能是少數,多數普通職業運動員不可替代性弱,其從屬性依然很強,但是要求俱樂部承擔全部成本和風險并不合理,應當通過俱樂部、社會保障和保險等其他經濟替代性措施相結合的方式承擔。最后,網絡時代的到來必將影響職業體育行業,用工形式會更加靈活化,應當允許只有經濟從屬性的職業運動員享受一定的勞動保護。黨的“十三五”規劃建議亦提出,“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應當鼓勵職業體育行業探索和嘗試更多新的用工方式,這也有利于聯通體制內和體制外的運動體系。
4.2 《體育法》與《勞動法》相結合
從屬性理論的雙重判定理解應當結合《體育法》和《勞動法》,既符合我國現行的法律體系,又能適應競技體育聯賽的特征。《體育法》第33條規定體育競賽的運動員應當遵守體育道德。體育道德作為一種職業道德,是運動員參與體育活動應當遵守的行為規范和職業操守,體現體育從業人員的共同意志。體育道德要求運動員誠實信用、努力拼搏和恪盡職守。雖然《體育法》沒有直接對職業運動員進行規定,但是基于《體育法》發展體育事業的立法目的和體育職業道德要求的正當性,應當對運動員進行廣義解釋,將職業運動員包含在內。《勞動法》第3規定:“勞動者應當完成勞動任務……遵守勞動紀律和職業道德。”足球、籃球等競技體育比賽多采取聯賽制,在聯賽當中重要職業運動員若行使合同解除權無疑是俱樂部最擔心的。因此,處于重要職務、參與俱樂部重要事項決策的職業運動員其不可替代性大大增加,其從屬性大大減弱,如果不對其權利予以合理限制無疑存在道德風險,應當限制其在賽季內解除勞動合同的權力。這樣規定的目的也是為了鼓勵俱樂部推行民主管理,讓職業運動員參與民主管理,形成同舟共濟的局面。
此外,工會等組織團體可以增強全體職業運動員的不可替代性和斗爭性,有利于實現俱樂部與職業運動員權利均衡,符合《體育法》和《勞動法》追求的和諧社會關系的目標。集體談判的成熟度影響著職業運動員對雇主的依賴性,也影響著法律干預程度。集體談判不成熟,勞動者就容易被孤立,其對雇主的依賴性會加大;集體談判成熟,勞動者就可以團結起來與雇主博弈,法律干預的必要性就會降低。集體談判的作用是明顯的,2011年美國職業籃球聯賽球員工會發起罷賽,整個聯賽停擺149天,最后勞資雙方還是通過集體談判確定了高于之前標準的最終勞資協議。同時,集體談判也有利于我國進行體育行政管理模式改革。依據我國治理現代化的要求,體育行政部門應當改變過去高度管制的行政模式,打破過于依賴行政管制的治理模式。行業自治和集體談判符合多元治理的要求,可以避免體育行政部門退出后形成的權力真空,能夠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
4.3 提升行業協會的作用
勞資關系的協調與處理需要一個第三方予以協助,體育行業協會應承擔這一重要任務。我國《體育法》第31條規定:“全國單項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第36條規定:“國家鼓勵、支持體育社會團體按照其章程、組織和開展體育活動”。在行業協會去行政化的背景下,公權力不再是行業協會權威的淵源,行業協會的權威應當建立在公正、民主的行業體制之上。在良好的行業協會體系下,可以通過三方協議的方式解決轉會費等問題,如可以將轉會理解為三方協議,轉會費是對職業運動員原所在俱樂部直接損失和自愿解除勞動關系的補償,新東家支付轉會費以換取老東家解除勞動合同。為保證原勞動關系解除后轉會費支付的風險,全國性體育行業協會制定相應的行業管理章程,對三方履行合同義務進行約束,保障三方行為符合體育道德和誠實信用原則的要求,維持合理人員流動和競爭環境。
體育行業協會的去行政化工作應當同時開展,避免少部分既得利益集團壟斷權力損害整個行業的利益。發揮行業協會應有的作用,樹立行業協會的威信。2014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加快推進體育行業協會與行政機關脫鉤,將適合體育社會組織提供的公共服務和解決的事項,交由體育社會組織承擔”。在減少審批、簡政放權的行政改革背景下,應當進一步推進行業協會的改革,提升行業協會的獨立性。人民服從道德與法律獲得認同和快樂,而非挫敗感時,才會形成正面的情緒體驗,良好的社會習慣才能養成。“隨著道德化‘反思’的蔓延,全社會中彌漫起一股暴戾之氣。它不是引導公眾正確地認識和思考中國社會正面臨的制度改革和創新任務,反而人為地勾勒群體對立,誘發敵意攻訐,激社會矛盾。”[20]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的利益具備一致性,其矛盾并非是不可調和的,雙方的良性競爭會迫使雙方提高水平,有意樹立敵對的影像是泛道德化的行為。面對這樣的暴戾之氣,行業協會有義務協調雙方關系,樹立體育行業的良好形象。
[1]華商晨報.沈陽東進俱樂部遭起訴球員要求解除勞動合同[EB/OL].http://news.yunnan.cn/html/2016-03/18/content_4236758.htm.
[2]婁春風.論職業運動員的勞動者地位:以轉會權為中心[J].西安體育學報,2010(4):413.
[3]楊天紅.論職業運動員與俱樂部間法律關系的定位:與朱文英教授商榷[J].中國體育科技,2015(3):139.
[4]朱文英.職業足球運動員轉會的法律適用[J].體育科學,2014(1):41-47.
[5]雷蒙德·瓦爾特曼.德國勞動法[J].沈建峰,譯.北京:法律出版,2014:54-55.
[6]呂琳.論“勞動者”主體界定之標準[J].法商研究,2005(3):30.
[7]王倩,朱軍.德國聯邦勞動法院典型判例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5:13.
[8]石美遐.勞動關系國際比較[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10:157.
[9]黃越欽.勞動法新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9.
[10]張凱華.勞動合同法誕生記[J].政府法制,2008(4):26.
[11]董保華.勞動立法中道德介入的思辨[J].政治與法律,2011(7):2.
[12]張斌.論現代立法總的利益平衡機制[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版,2005(2):68.
[13]董保華.名案背后的勞動法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59.
[14]張恩利.我國運動員職業身份、職業特征及其職業發展權利研究[J].天津體育學院報,2016(1):46.
[15]許延威,馬立坤,劉波.對“運動員無形資產與運動員人力資本”概念的辨析[J].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14(5):559-562.
[16]鄭明,何志林,沈佳.我國職業足球俱樂部利益群體的特征和利益訴求[J].上海體育學院學報,2009(3):1-5.
[17]劉剛.“天價”轉會好不好[N].吉林日報,2016-3-17:16.
[18]俞可平.走向國家治理現代化:論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國家、市場與社會關系[J].當代世界,2014(10):25.
[19]黃程貫.勞動法[M].臺灣:空中大學出版社,1997:70.
[20]韓朝華.跳出“放亂收死”循環實現社會治理創新:改革30年的制度得失[J].探索與爭鳴,2008(1):19.
Legal Dilemma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Athletes and Clubs:From the View of the Depend Theory
LI Zhikai
(School of Law,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4,China)
For a long time,the dispute about the identity of professional athletes and laborers is actually resulted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club retention sys?tem and the labor law of our country,and lacking of the corresponding of interest compensation mechanism.With the thinking mode of"strong capital and weak labor",the attribute theory that China's judgment of labor relations merely contains a single judgment“whether”.Only two kinds of choices,no protec?tion and full protection exist,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omparison of actual strength of labor and management.However,the attribute is not a rigid criterion,but always develops with the change of society.To achieve both to expand the scope of labor protection and avoid unfair,it must respond to changes in both sides of actual strength of labor and management.Germany law"assembly staff"only enjoy the limited protection of the labor law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which are considered on the basis of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labor.The irreplaceable nature of excellent professional athletes reduces their need for the personality attachment,which may only exists in economic subordination while without personality subordination,etc.When a club wants to win excel?lent professional athletes from other clubs,it is actually trying to gain this kind of non-substitutability and to occupy the initial investment of other clubs.The lack of response in China's labor law of changes in labor and management power and their demands in occupational competitive sports led to the imbalance of interests arrangement and the weak negotiation system from the attribute theory of between labor.The intervene of capital and strong administrative institutions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conflict.We should combine the labor law and the sports law,build the double decision mode combineing"whether"and"weak" ,to ensure the fairness of the sports market and to achieve the orderly flow of talent and win-win between labor 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athlete;clubs;dependent;right balance
G 80-05
A
1005-0000(2017)03-233-05
2017-04-26;錄用日期:2017-04-28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項目編號:NO.106112016CDJSK08XK21)
李志鍇(1981-),男,廣西桂林人,副教授,在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憲法與行政法。
重慶大學法學院,重慶400044。
10.13297/j.cnki.issn1005-0000.2017.03.009
——評《休閑體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