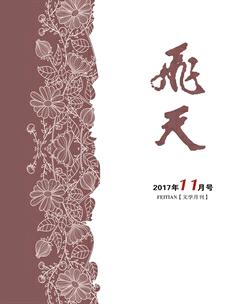活在旱地里的環縣
葛水平
我期望環縣有一場飽雨。黃土溝梁上的草都旱死了,那么好的景致,既羸弱,又矮小的草,盡管是開花結籽的季節,因為干旱,它們可能遺傳給下一代的也是羸弱。今年比往年歉收,從莊稼的長勢看,開春地里也還是有墑,看那些農作物的陣勢就知道,只是七月無雨,農作物的葉子干了,在陽光下給人揪心的疼痛。
農業,人類最初的故鄉,它和民間有著我們難以描述的親切,包括它給我們帶來的甜蜜和苦澀,希望和失望。云從頭頂走過,云里無雨,雨對環縣有多么重要!當地人告訴我,今年的農作物大部分絕收。無收成的土地,對當地老百姓是一個苦笑。
有一只燕子飛過。在北方,燕子伸展矯健的翅膀,它是要把雨的消息剪落在人間的先行者。當大片的燕子飛落時,那一定是燕子喜不自禁地逐雨而來。輕聲而鳴的燕子飛過,一切歸于遼闊的沉寂。曠野的風火燎燎熱,一粒種子回不到種子本身,發芽、開花,不等結果時就旱死了。
環縣落座在甘肅省東端,地處毛烏素沙漠邊緣的丘陵溝壑區,轄內山大溝深,山、川、塬兼有,干旱少雨,全縣耕地面積359.17萬畝,農業人口32萬,靠天吃飯,雨養農業是環縣的基本縣情。他們的縣長告訴我,環縣年降雨量只有300毫米左右,且多集中在7、8、9三個月,而年蒸發量卻高達2000毫米。這一氣候特征,注定環縣農業生產的艱難,春季干旱下不了種,越冬的莊稼也常常被旱死,每年春夏兩季,環縣四野赤地千里,群眾往往用“種了一料子、收了一抱子、打了一帽子”來形容廣種薄收的農業四季現狀。
提起吃水,環縣人給我講起了2006年夏天的事。那一年的六七月份,該有雨時,空氣干獵獵的,云輕薄得很,從環縣上空走過時沒有一絲害羞的樣子。環縣轄區:八珠、耿灣、樊家川、虎洞、毛井、合道等川塬鄉鎮的“一線四川十塬”赤日炎炎。路上的拉水車穿越,人吃水都是高價,誰舍得澆地?莊稼是徹底旱死了!對于常年干旱的環縣百姓來講,一年旱不怕,祖輩留下了經驗,家藏糧食夠幾年吃。遼闊的黃土地上人煙稀少,有的人家一口人可擁有100多畝地,一輩子種地打糧,就為了應對干旱。我不忍心想象他們的四季,春種秋收,這中間要付出多少辛苦?
拉水的路上,鳥雀攔在車前。鳥們的世界是我們不知道的世界,也是宗教不知道的世界,更是文明世界不知道的世界。它們停留在干旱的地方,它們只是要喝飽肚飛翔。拉水人取桶提水放在路當央,一群鳥飛落在水桶前,有秩序地飲水,飲飽水后鳥飛走。我不想演繹鳥對人的感恩,它們是另外一種生命,無論它們在干旱中經歷了什么,它們迷戀、癡醉和曠日廝守的地方,就是它們不想去很遠地方的理由。
那些從鄉村漂泊到城市的人們,還有多少在懷念家鄉的炊煙鄉鄰和睦勞動的笑臉?我一直在梳理自己紛亂的心緒,盡量調整自己的心情,好使自己進入到另一種狀態。年復一年和土地打交道,風吹日曬,起早搭黑,天空中哪一疙瘩云會停留,哪一疙瘩云會快活一方土地?云朵來了走了,他們坐在田間地頭,抱著腿,托著腮,從不急躁,誰有本事喊得動老天爺呢?既然喊不動,從來他們就不想留住或改變什么,人不是老天爺的睥睨者,是老天爺的盤剝者,老天給人太多,多到多少是個夠呢?沒有比農民更知道用勞動換得感恩了。我和當地的農民聊天,我說,既然常年干旱,不如離開。他們笑著搖著頭說:離開是最后的事。
我們每個人最后都會離開土地。
土地離我們饑腸轆轆的生命最近,離我們對田野的熱愛最近,只要信賴和歡喜,土地讓我們習慣,既然已經習慣,那就守著土地等著那一天的到來吧。
2006年大旱之后,由環縣縣委、縣政府統一抽調的651名黨政干部從縣城統一出發,奔赴甜水、山城、南湫等縣北13個鄉鎮,進駐134個行政村,啟動了環縣幾十年來涉及面積最廣、距離農戶最近的一項工程——縣北部人畜飲水工程。此后幾年時間內,在縣北6000平方公里范圍內,包括鄉鎮干部在內近1000多名干部蹲點督陣,三萬勞動力揮汗作業,數百名縣直鄉鎮干部住到了村子里,數千名在外打工的農民回到了村里,開始做同樣一件事情——打水窖。
水窖,夏雨到來的時候,或者秋汛開始的時候,老天閉眼給水,水漲自滿的溝壑傾瀉而來,下雨的時候,集流場里的水會自動流進窖里;雨水不足的時候,主人們會提前拉水灌進窖里。雨季會消失,水會退去,水不是這里的永久居民,它們去往很遠的地方。干旱侵入,然后,干旱用盤根錯節的方式殺死了這里的青綠。
一口口水窖,也因此成了環縣山區一個個“農家樂”。縣水利部門的同志說,人飲工程的實施,不僅可以基本解決正常年景下全縣21個鄉鎮、246個村、4.4萬戶群眾的吃水問題,也把廣大農民的一大部分精力從水里面“解放”了出來。可是,土地無法“解放”,依舊干旱。土地上栽種下的樹木在大面積死去,如果沒有風沙刮來,它們就以樹的形象站著,它們慢慢變黃,干黃,那些葉片來不及等到秋天就死在樹枝上了。在風沙刮過之后,天色會交替、草地會枯萎、人會老死泥下,干死的樹很簡單地就做了農人的柴禾,一把火點燃,就這樣,那些一代一代人的辛苦,總是叫你看不見。一棵樹的成活對環縣的土地有多么重要,浸滿著環縣種樹人的苦。
又一個春天來了,鎖住墑情,打響糧食“保衛戰”是環縣人掛在嘴上的口號,口號激發了人民的斗志,可激發不了老天的斗志。老天和隆冬一樣沒有作為,它貓在天上,它從來不知道饑渴,既沒有承諾,也沒有兌現。老天固定在一個無法走開的位置上,哀巴巴望著老天的農民,不哭,他們的眼淚是他們最后的珍藏。
過去說十年九旱,現在幾乎是十年十旱了。靠天吃飯靠不住,他們開始在地上想辦法。全膜雙壟溝播栽培技術由此進入環縣人的視野。2006年,首次引進全膜雙壟溝播栽培技術,在耿灣鄉萬家灣村試種2000畝;2007年,在耿灣鄉示范推廣全膜雙壟溝播作物1.05萬畝,經受住了70年未遇的春旱考驗,并獲得了好收成;2008年,縣上提出了以曲甜公路為主線,輻射布設方案,推廣全膜雙壟溝播種植21萬畝。其中11.02萬畝全膜雙壟溝播玉米,在生長關鍵時期連續80天無有效降雨的情況下,平均畝產達到442.6公斤,較半膜種植增產52.1%,較露地種植增產119.1%。雙壟溝播玉米因此被廣大農民稱為旱不垮的“鐵桿莊稼”。
今年年成不好,旱大了,“鐵桿莊稼”的葉子也開始泛黃。一位捂著頭巾的環縣女人挑著擔子往山上走,我問她:“七月沒有下雨嗎?”她說:“沒有。六月后半月也無雨。”我說:“沒有想過離開環縣去有水的地方居住嗎?”她說:“不想。好地方都是人家的。”
船在沒有水的對岸守著河。只有船會癡心地守著河,因為其他不是河的親人。
環縣人是環縣土地的親人。他們不想背井離鄉。干旱的土地給了他們成長,任憑風吹日曬,這是他們今生擁有的日子,他們懂得好,他們的好里有刻骨銘心的苦難歲月。
十年十旱也就到頭了,干旱的抗爭和農作物的粗糧籠罩住了環縣人的欲望,干旱的背景中襯托著黑黝黝膚色上掛著的笑容,比我們的笑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