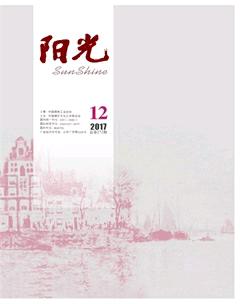《建設者之歌》始末
一九八二年,《建設者之歌》創作組
一整夜奔馳在夢中。
突然睜開眼時,發現列車正穿越一個混混沌沌的早晨,撲進一個陌生的城市,武漢。
這是一九八二年四月初的一天。
我隨著人流走出武昌車站。頭頂有太陽,卻不鮮亮,撲面而來的是一股陰冷和灰暗。想象中南方的溫暖竟成了一個騙人的故事,那渾濁的江水才是這座城市的顏色和溫度。這就是武漢?“芳草萋萋鸚鵡洲”在哪里?有著千古傳說的琴臺在哪里?黃鶴樓又在哪里?我仿佛掉進一江濁水,懵懂于寬闊的站前廣場。
路邊擺小攤賣水餃的大嬸卻有著十分的熱情,她用唱歌似的話音把我留住。
一碗水餃,像北方的餛飩,餃子很小,有味道不錯的湯。那股陰冷的氣息漸漸散去,直到這時,我好像才看到了人來車往,居然還發現了綠樹,一棵,兩棵,三棵,原來這個城市還是滿鮮活的。站起身來時,不由想起那句常說的話:境由心造……
我在離車站不遠的紫陽路上找到一個小院,門口掛著“湖北省音樂家協會”的牌子。接待我的是宋運昭先生,個子不高,瘦瘦的,說起話來一聽就是血統純正的“九頭鳥”。宋先生告訴我,他接到了我的電報,正在等我。又說,參加這個叫作“建設者之歌”創作組的共十一人,其中八人來自北京,倆人是東北的,再一個就是我了。他還說,湖北音協派他全程陪同,組內其他人都在北京集中,明天到武漢。之后,他便領我到對面的一個招待所住下。
這一年,我剛剛四十出頭。這一年,我作詞的那首歌,《年輕的朋友來相會》正唱得熱火朝天,時不時地點燃著藏在我胸腔內的激動。我很清楚,能參加這樣一次由中國音協組織的創作活動,完全是這首歌給我帶來的機會。但我又很不自信,不知在這次活動中能不能再寫出一兩首讓自己滿意的詞作,又想到這次來的人中一定有大腕級的詞曲作家,心中越發多了幾分忐忑。
第二天剛吃過早飯,宋運昭先生和湖北省音協的領導便來接我到軍區招待所,說其他人都到了。
和大家見面時,我很拘謹,在名人面前我總是自我感覺不好,這似乎是我的天性。
這個創作組的領隊是宋揚先生,中國音協創委會成員,《歌曲》雜志副主編,一個精瘦的老頭。解放前他就寫過一首很流行的歌:“小呀么小兒郎,背起那書包上學堂……”老頭子很嚴肅,操著濃重的湖北口音介紹著組內的成員。首先介紹的是作曲家唐訶先生。
唐訶,這個名字如雷貫耳,作曲家,北京軍區戰友歌舞團專業創作員。我對他的許多作品都很熟悉,《長征組歌》《老房東查鋪》《眾手澆開幸福花》等等,還有那首《在村外小河旁》,是我特別喜歡的。因為此歌的詞作者是我學寫歌詞的啟蒙老師——山西音協的周振佳先生,還因為這首歌有著濃郁的山西民歌風。唐訶先生在我心中絕對是頭頂有光環的名人,當他在我面前微微欠起身的時候,我看到的是一張極為和藹的面孔,國字臉,皮膚白潤,透出一種身份和修養。他穿一身軍裝,腳上卻是一雙干凈得一塵不染的黑布鞋。這讓他的軍人身份中突顯出一種文人的氣質。在這幾秒鐘中,我下意識地想把他的形象和他寫的那些歌連接在一起,卻發現無論如何也無法對接。那些好聽的歌,是怎樣從他的心中流淌出來的呢?
張士燮,外表氣質和唐訶先生很不相同的一位軍人,空政歌舞團詞作家,高高的個子,身材魁梧,也是一身軍裝,穿著一雙擦得很亮的黑皮鞋。那一刻,他簡直是我心目中的標準軍人了,要是站起來敬一個標準的軍禮,那一定會很威武。但此時,他那張略顯發胖的臉上卻堆滿了謙遜的笑容,就在宋揚介紹他的那幾秒鐘的瞬間,他連連地向左右點了四五下頭。我似乎從他臉上的笑容里,遠遠地聽見了那首歡快的《社員都是向陽花》和另一首深沉而凄美的《十送紅軍》,甚至還有剛剛流行的《蘭花與蝴蝶》。
宋揚先生是按組員們的年齡一一介紹的。接著站起來和大家打招呼的是全國總工會文工團的詞作家王積福先生。王積福寫過一首歌叫《請到我們這方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十分流行,由茅地作曲。茅地是四川人,這首歌的曲調用了四川民歌風,十分好聽。王積福先生稍微有點兒胖,像一個十分溫和的老頭。坐在他身邊的是和他在一個單位的作曲家秦萬林,年齡比他小一點兒,圓臉,胖乎乎的身材,手里總端著一個水杯,不停地喝。后來的日子里他也一直是這樣,很少說話,卻總是面帶一副謙和的笑容。
還有一位年齡比我大的就是云華了,鐵路文工團創作室主任,作曲家。云華那時也就五十多歲,卻是一個老革命了。他十幾歲就參加了新四軍,成為一名文工團演員,解放后學了作曲,一直在鐵路文工團工作。當然,這些都是他后來告訴我的。因為幾天之后,我和他就成了好朋友,因為我倆脾性相投,凡事都總是往后靠。
這群人里,有一個人是比較特殊的。他是金鳳浩,朝鮮族人。黑黑的臉,一看就有鮮族人的特點。他說漢話還不太流利,結結巴巴的。老金比我大一歲,原來在延邊歌舞團拉手風琴,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歌叫《延邊人民熱愛毛主席》,旋律十分好聽,流傳甚廣,那就是他的作品,老金因此被調到了省音協,還給了一個副主席的位子。但他卻一點兒也不像個“副主席”,總是小心翼翼,與人說話時也總是點頭哈腰,顯得比我還拘謹。后來憶及,他那言談舉止一定與民族性格有關。
剩下的三個人中有兩個我認識,因為都是中國煤礦文工團的,一位是詞作家曹勇,比我小幾歲,另一位是作曲家陳錫智,他們年齡不相上下。還有一位來自黑龍江歌舞劇院,詞作家,他參與創作的《烏蘇里船歌》由著名歌唱家郭頌唱紅了整個中國。這位文質彬彬的詞作家和我同年,看上去很穩重,他叫胡小石。
見面,也就是認識一下面孔,或者說叫“對號入座”。因為搞音樂創作的人相互之間可以說是早已相識了。常說“文如其人”,熟悉了他的作品也就熟悉了這個人,所以大家常好說這么一句話:“一見如故。”于是,拘謹之中,我感受到一種久違了的親切。這種親切感不能不說是來自于一種早已就有的相知。
武漢湯包的滋味
午飯由東道主湖北省音協請客,去吃著名小吃“武漢湯包”。endprint
包子本不是什么稀罕吃食,活這么大,好像什么餡兒的都吃過,而且還知道中國最有名的包子是天津的“狗不理”,還有上海的南翔包子,卻未曾聽說過武漢湯包。于是,便總覺得這一個“湯”字,一定獨具風采。
在漢口六渡橋的街面上我們下了車,主人指著右手邊一個不大的門面說,這里就是武漢湯包最著名的老店,有上百年歷史了,要吃最正宗的湯包就得到這里來。
這是一座不起眼的二層樓,正是午飯時分,小小店面門口,有不少顧客進進出出,生意果然紅火。我們跟在主人身后登上二樓,未及走進雅間,便有一股濃香的包子味兒撲鼻而來。記不得餐桌上都有什么酒和菜肴了,好像是什么都沒有,只記得有包子。只記得那湯包咬破皮兒就有一股又香又濃的湯兒流到嘴里,“湯包”也就此變得名副其實了。湯包是小籠蒸的,外表與北京的、杭州的小籠包沒什么大區別,但這一股湯兒確是成就了這一美食的與眾不同,使它成為了武漢的一個品牌,一個驕傲。由此看來,成就偌大一個城市之驕傲的事或物,其實并非要多大,或許就只需指頭肚大的那么一丁點兒就夠了。
這世界上的事,實在太難定什么規矩了。
或許在這一堆人里真的沒人享受過這一口美味,湯包得到了眾口一辭的盛贊,氣氛一時間變得十分地熱乎。于是,主人的臉面上便大放光華。也許是應了那句話:“得意忘形”,不不,也許是主人太實誠了,他隨后說出了幾句實在是不該在這一場合說的話。他說:“實不瞞大家,音協太窮,沒有錢招待大家到大飯店吃頓像樣的飯,吃這頓湯包的錢,也還是把攢了三年的舊報紙賣了才得來的……”
啊?我有點兒懵。即便是這樣,不說也就是了,為什么偏要說出來呢?不知別人聽了此話的感受如何,反正我覺得有點兒尷尬。剎那間,那包子的香味兒就少了一半。短瞬的冷場后,有誰說話了:“實在太難為你們了。各地的音協大都如此,除了人頭費、辦刊費就什么都沒有了……”是呀是呀,大家便都附和,你一句我一句地說著切身體會或道聽途說。但在我聽來,倒像是在為解脫自己的尷尬而說出的一些言不由衷之詞。
不過,這些話倒也句句是實。那時,各個協會都窮得鍋碗瓢盆叮當響。請不起客,吃不起飯是事實。好在那個年代吃喝尚未成風,大家到各地采風創作都是自己掏錢吃飯。此時改革開放雖說也有五六個年頭了,但“文革”前那種根深蒂固的厚樸,還依舊留在人們心中。不過,這句不太合時宜的“請不起”,還是讓吃飯的氣氛冷卻了下來,每個人的胃口也好像突然變小了,沒吃多少,便一個接一個地放下筷子,連說吃好了,吃好了。當然不會忘記謝謝主人。
包子還剩了一些。這是留給主人的顏面,也是客人給自己的留的顏面,還有那份欲說還休的感受。
武漢湯包的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一捆捆的舊報紙,幾位樸素而實誠的湖北人,一頓香香的小小的包子,還有十一位著名的或尚未出名的曲作家和詞作家,共同“創作”了武漢采風的第一個作品——不是寫在紙上,而是寫在心里的。
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我又先后參加過許多次創作采風,說不清是從哪一年開始,風氣就漸漸地變了,變得十分地奢侈了。不管到什地方,吃住行總有人精心安排,為你買單,而且絕對的高檔招待。記得就是這次武漢行的十年之后,我參加又一個歌曲創作組來到武漢,第一頓飯便是在武漢最有名的國際飯店吃的,叫作接風,那個豪華那個排場與十年前自是天壤之別。
時代變了,人的思想變了,行為也變了,唯有那一頓“武漢湯包”的記憶,卻像刀刻般留在了心頭,雖然它早已“逝者如斯夫”。
武鋼,一米七
創作組把采風活動的地點選在了武漢鋼鐵廠、第二汽車制造廠和正在建設中的長江葛州壩。這三個企業在當時來說都是巨無霸級的,每一個名字掛到嘴邊上就能讓你感到心跳。
首訪自然是武鋼了。
對于煉鋼廠,我不算陌生。鞍鋼、太鋼是老廠,包鋼、武鋼是解放后建的,但也算是老廠了,正在建設的是首鋼和寶鋼。陳列在當時中國大地上的大型鋼鐵企業,也就是這些了。而一說起鋼廠,我首先就會想到太鋼。我在太原生活了十八年,北門外頭頂上的那一頂烏煙瘴氣的帽子,就是太鋼的標志。不過那時的人們還不懂得什么叫“污染”,什么叫“霧霾”,甚至還為能戴著那么一頂黑色帽子的太鋼感到幾分驕傲。我父母親當時住在汾河西面山腳下的一個叫石渣廠的地方,那里地勢高,每到夜晚,站在院里就能看到太鋼騰起的沖天紅光,壯麗非凡,那是太鋼又在出鋼了,那場景讓我至今不忘。
當時太鋼有一項在全國叫得很響的技術革新,叫“三槽出鋼”,就是把原來一個槽子出鋼改成了三個槽子同時出鋼,這樣就大大提高了鋼產量。我在西山腳下看到的那個壯觀的場景就是“三槽出鋼”之大手筆。后來,上中學的一個假期,學校組織勤工儉學,我有機會在“三槽出鋼”車間勞動了半個月。走進這個車間,除了看到它的高大雄偉,更讓我感到的是熾熱、汗水、苦、累、臟,那出鋼的時刻,不再是壯麗,更多的是恐懼,還有人和生命的渺小。穿著厚厚的隔熱衣、石棉鞋,站在還發紅的爐渣上干活,那滋味永遠烙進了我的記憶。
我知道,太鋼是閻錫山時期建的廠,而武漢雖有過張之洞創建的漢陽鐵廠寫在中國歷史上,但武鋼卻是一九五五年才建的。到了一九八二年,它已是一座超過太鋼包鋼的巨無霸了。
“到武鋼,去看一米七。”一聽這話,我便一頭霧水了。什么是一米七?宋運昭告訴大家,一米七是武鋼的一個軋鋼車間,專軋一米七寬的鋼板的,全部設備和技術都由德國引進,當時在中國只此一家。
似乎有點兒懂了。其實還是不懂。
到武鋼的頭一件事就讓我長了見識。
我們被一個西裝革履自稱是接待科長的小伙子領進接待室,然后就在一面小銀幕上放電影,用十五分鐘時間把全廠做了全面介紹。這種做法如今已司空見慣,但當時卻感到很現代。我在企業里搞工會,“說拉彈唱,打球照相,迎來送往,帶頭鼓掌”是我本職工作的一部分,常有接待任務,也有介紹企業的環節,卻總是坐在會議室由領導照著稿子念,然后由領導陪同一起參觀。這里卻大不相同,科長陪我們看完小電影便去忙別的了,我們則由一名年輕姑娘領著到車間,而且直到我們參觀結束,也沒有任何一位廠領導出面。這讓我又新奇又佩服,武鋼人的管理真是比我們高出幾個量級啊,它將許多繁文縟節都化作了省略號。endprint
記不清轉了幾個車間,與太鋼那些車間大同小異。留在記憶中的也就是“一米七”了。
這個車間有多長?一里?一公里?反正一眼望不到頭。這個車間有多高?五層樓?六層樓?或許還要高。這個車間有多少人?怎么連一個都看不見?
…… ……
我們在車間一側離地面二十多米高的一條鋼鐵的棧道上慢慢地走著,俯視下面,一根通紅的鋼錠進入眼瞼,第一道工序里,它開始變化,被軋成了一塊還很厚的鋼板,紅紅的鋼板向前傳動,又是一次軋制,鋼板又一次變薄。不知前面還有多少道軋制的過程,反正鋼板傳遞的速度比我們走路的速度要快得多,我們目送著紅色的鋼板紅光漸漸暗淡,轉而遠去,消失在視線的盡頭。
最初產生的那個疑問又浮現出來。這么一個軋制過程是誰在操控?有多少人?人在哪里?我的腦海里又一次浮現出人影忙碌的太鋼三槽出鋼車間。
這時,陪我們參觀的那位姑娘笑容可掬地告訴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都在你們身旁的操作室里,人很少,也就十幾個人。整個生產過程全部在計算機上完成。”
那個年代,電視機尚未普及,家里有個黑白電視機就夠嘚瑟的了,至于計算機,更是聽說過,沒見過。所以,當聽說從一塊鋼錠變成薄薄的鋼板竟然只用計算機就可完成,真的感覺像是天方夜譚。自然,我們都想見識一下這個奇妙的操作過程,但卻被姑娘莞爾一笑拒絕了。
非常遺憾。
我們就在棧道上走啊走啊,終于走到了車間的另一端,看見了被卷成一卷一卷的鋼板,薄薄的,這就是那一塊塊火紅的鋼錠變成的。有吊車將鋼板提起來放到專用的卡車上,拉走了,而后面新的一卷又下線了,這似乎是一個永不停歇的過程,看起來卻又是那么輕松,就像一首樂曲緩緩地流淌著。
這一天,我時不時地便想到礦井下采煤的礦工。昏暗的燈光下,幾十條黑黑的人影揮動著手中的大鐵鍬,把放炮崩下來的煤炭拼命地往傳動著的溜子上攉,煤塵飛揚,汗如雨下,精疲力竭……
這一天,我的腦海里揮之不去的就是那個“一米七”車間的情景。那是一道美麗的風景。
“二十七個羊糞蛋”
到第二汽車制造廠去。
二汽早聽說過,出產“東風”大卡車,但只是前幾天才知道它在湖北十堰。
十堰,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時,很感覺有幾分新鮮。那時它還不是一個“市”,也不是一個縣,只是一個“地方”,顧名思義,一個有著十條壩堰的地方。所以心里就不由得發問:二汽怎么建到這么一個沒聽說過的地方?為什么不建在一個大點兒的城市?比如一汽,不就在長春嗎?
火車在夕陽西下時分到了十堰。很小的一個火車站,很小的一個候車室,一看就是新建的。舉目四望,都是高高低低的山頭,植被卻很好,雖是初春,已是一片蔥籠了。
一位個子不高,說話辦事都十分利爽的青年人來接我們,他自我介紹說他是二汽文聯的,姓鄭,愛好攝影。
太陽下山后,天氣有點兒冷凄凄濕漉漉。汽車拉著我們沿曲曲彎彎的河溝往里走,路面高低不平,時不時還要過河。在跨過一座小橋后,終于看到了一片樓房和平房,無序地坐落在溝溝岔岔里。樓房都不高,但看上去很新。像是一個小鎮,卻沒有古老集鎮的風韻,倒是透露著一股現代企業的氣質,這就是二汽總部的駐地了。
我們被安排在招待所的二層小樓上住宿,非常簡陋。一個房間兩張三張四張單人床不等,床上用品讓人看一眼就會想到部隊戰士的營房。晚飯看來是特別安排的,分兩桌,每桌上了五六個菜。但沒有任何領導作陪。飯廳里涼風透骨,是山里的風。這時,只見唐訶先生不聲不響地走到飯廳里的小賣部,拎來兩瓶白酒,每桌放了一瓶。那個年代,大家都很窮。我剛走出跋涉了十三年的每月五十四塊五還要養活兩個孩子的那段艱難之路,走進了月工資七十多元的檔次,已覺得很不錯了。而金鳳浩剛調到省音協,工資還沒領過,參加這次創作活動,還面臨著能否報銷的問題。年紀大點兒的幾位肯定比我們要強,這大概也就是唐訶先生主動買酒的原因吧,在這伙人里可能他的職別最高。
這是此行頭一次喝酒。酒瓶往桌上一放,我便看出了誰最好酒。一個是曹勇,一個是胡小石。后來在和這兩位朋友的交往中也證明我當時沒猜錯。讀曹勇的作品,你定會看到許多的酒字,而胡小石則是好酒者聚會中少不了的角色。有酒飯也香,話也多,心也暖。酒真是個好東西。舉杯之間,大家的心好像一下子又靠近了一大步。
飯后,二汽的廠長和書記來看望大家。找了一間放著四張床的宿舍,我們就坐在床上,有兩把椅子,讓廠長書記坐。就這么簡單,連杯白開水都沒有。廠長和書記都穿著中山裝,很和藹。但這倆人我們已從接待我們的那位攝影家口中得知,他們都是在籌建這個廠的初期由周恩來欽點任命的,都是國內著名的汽車制造專家。記不清二位的姓名了,只記得廠長一開口便說,這里條件很艱苦,建廠設計是按戰備要求搞的,當時李先念要求,要將各個分廠和車間像撒羊糞蛋似的撒在這一片山溝里。所以,現在的二汽就由“二十七個羊糞蛋”組成。撒在二十七條山溝里。談笑中,二汽的概況我們便大體了解了,懸在心頭的一些疑問也就此釋然。倆人又回答了一些大家感興趣的問題,在一片熱騰騰的氣氛中,會見結束。沒有太多的客套,更沒有任何形式上的鋪排。兩位總理欽點的廠領導和數位全國著名的音樂家的座談竟是這樣的沒有“禮儀”。這是我從武鋼到這里第二次感受到與我們那些企業完全不同的節奏和風格。只是,令我感嘆的是,這樣的情景在后來的這些年再也沒有重現過。
有一種懷念叫“遠方”。遠去了的簡樸,遠去了的純凈,遠去了的人和事。這大概也是我想用這些文字,找回心頭的那些失落吧。
記不清奔波了幾天,看了一些什么車間。只記得每一條山溝都有一個偌大的車間,都有一片住宅;只記得活躍在車間里的面孔都很年輕,無論男女;只記得每一個地方都山清水秀。連“走馬觀花”都談不上,是“跑馬觀花”。但一股清新的氣息不知不覺間注滿了心胸。這是一個現代化的企業,這是一個年輕而富有生命活力的企業,這是一個分工協作嚴絲合縫的現代企業。這種氣息讓我興奮,讓我羨慕,讓我向往。endprint
印象最深的是汽車總裝廠。這個地方不是山溝,在一個平坦的三角地帶。
總裝車間沒有武鋼那個車間長,但車間里有人的操作,這便成就了另一種風光。
這是一條標準的流水線,一輛140大卡車除車箱外的所有大大小小的機件,全都在懸掛中不停地傳動著。流水線上的工人們在固定的距離中各自負責固定的安裝任務,或許是大件,或許是一兩個小小的螺絲,但他必須隨著一輛輛移動過來的將要成型的汽車操作,那物件不會因你的快與慢而停留,哪怕是一秒鐘。所以流水線上的每個人動作都要快,要準確無誤,還要保證質量。工人們熟練而有條不紊,又幾乎是機械地在一個動作中忙碌著,好像永遠也停不下來。這讓我看呆了,倏地便想到卓別林電影中的那個人物形象。這樣工作八小時,肯定非常累,非常單調啊。但看到流水線上作業的那些男女,卻好像干得很輕松。有人告訴我,這些工人都是職工子弟,高中畢業后再經過專業培訓,才能上流水線。他們年輕,他們就是二汽的主力軍。
我們望著一輛輛漸漸成型的汽車慢慢向前走著,觀察著基本看不懂的一道道工序。最后一道工序是為發動機加一點兒油。之后,便會有一名司機跳上駕駛室,將車發動,轟然開走。陪我們參觀的人說,每隔三分鐘,就生產一輛車。啊,一天由多少個三分鐘組成,一時還真算不過來,那該是多大的一片汽車呀。
車間大門口,我們靜靜地目送著沒有車箱的“東風140”一輛接一輛地遠去。
這就是二汽。
夜里躺在床上,旋轉在腦海里的便是那“二十七個羊糞蛋”。青山,綠水,車間,忙碌的人們,一輛接一輛下線的“東風140”……
這就是當年三線建設的一個縮影嗎?我想到早些年從大同坐火車去太原時,總會看到一些和當地人不大一樣的人。他們是北京來的,他們在五寨縣那個傳說中的神秘工廠里工作。那時五寨附近就有了后來叫作“太原衛星發射中心”的地方,人們都說,那個神秘的工廠就是為其服務的,但誰都沒有親眼見過那個廠是什么模樣。車到寧武站,他們會下車,然后到對面的大山里去。人們對這些人也感到非常神秘,甚至不敢上前與他們搭話。若干年后,我從五寨乘車上蘆芽山,車在山溝里繞來繞去,頭頂懸崖峭壁,身旁亂石嶙峋,越走越險。忽地看到左邊山腳下竟有幾棟樓房,都是四五層;走不遠,又是幾棟樓房,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有人說,這就是當年那個神秘工廠的所在地,據說還有山洞。如今,廠子撤了,這些樓房被當地農民用來做羊圈,或存放柴草。一片荒蕪中卻還能讓人想象到當年這神秘大山里的另一番景象。
在一九八二年的這個初春的夜里,我當然也不會想到,幾十年后,二汽也會遷到襄樊。
哦,那“二十七個羊糞蛋”的命運又如何呢?
無論如何,他們在我的腦海里依然還是青山,綠水,車間,忙碌的人群,一輛接著一輛下線的“東風140”……
觸摸夔門
從武當山下來的第二天,創作組便登上了去重慶的火車。淡綠色的漢江水,河面時窄時寬,水流時緩時急。山崖河谷,亂石飛鳥,留在腦袋里的畫面至今呼之欲出。
在重慶只住了一天。重慶市文聯的梁上泉先生全程陪同我們。梁先生的大名久仰,小時便讀過他的長詩《紅云崖》。他還寫過不少好的歌詞,閻維文唱的《小白楊》便是他后來的大作。
我們于黃昏時分上船,在萬縣住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便到了奉節。
奉節是一個小縣城,卻又是一座古城,始建于秦代,叫魚腹,三國時改名永安,唐貞觀年間,為旌表諸葛亮奉劉備“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忠君愛國思想,更名奉節。小城又因擁有白帝城和夔門而聞名于世,史有“踞荊楚之上游,為巴南之喉吭”之稱。
輪船停在江邊,下船,上岸。這岸邊,不見那種像模像樣的碼頭,實際上就是江邊的灘,但一雙腳畢竟是踏上土地了,當然叫岸。抬頭仰望,那座小城似乎坐落在頭頂好高的地方,因為能看到的只是一個城門一段城墻,這小城就又平添了幾分神秘。有路通向城,路上鋪有石階,很陡。據說有這樣的記載:“江邊有石階,如壁陡立”。一步步攀登,喘息之間回看江水,感慨江離城怎么這等遠,那城,為何要建在那么高的地方啊。
走走歇歇,終于到了城門前。回過頭再看那長江,已似細細渾黃的一股水流,似動非動。
城門真的是很古老了,城磚斑駁,門頭上的字跡也看不大清。倒是有一道紅色的標記醒目地橫在城門邊一米多高的地方。來接我們的人告訴大家:“前幾年長江發過一次特大的洪水,水漫上了城門,漫到這里。城門附近的街道都淹了,白帝城也進水了,夔門只留了個山頂。那水太嚇人了,站在這兒一眼望出去,滿世界都是水呀!”這一席話,無疑是一個身臨其境者的導引,讓我們的思緒呆呆地被困在一片汪洋之中。慢慢回過神來才明白,哦,看來古人把這座小城建在這么高的地方還是很有遠見的啊。
奉節是歷史名城,也是文化名城。其實劉備托孤的地方并非在白帝城,而是在奉節城內的永安宮。城內還有杜甫寓址,他就是在這里寫下“無邊落木瀟瀟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千古絕唱。但招待所的人告訴我們,這些地方“文革”中都被毀了,正在修復。
第二天早上,我們租了一只船,去看白帝城和夔門。船不大,也沒有篷,剛好裝得下我們這伙人,船頭上坐了一位為我們導游的姑娘,長得清清爽爽。沿江的風很硬,我們雖都穿著風衣,還是冷得直打哆嗦。那導游姑娘看著我們的樣子卻笑了,說:“這里到白帝城只有八公里,順風順水,很快就到。”又說,“這長江現在看起來不寬,是枯水季節,但到雨季一天一個樣,有時早上起來一看,水就長了幾十米,漫到半坡上了。”聽她這么說,我不由自主地又向岸邊望去,這一看就覺得我們好像在江底了,頭上是幾十米高的水。心里顫顫的。
順水的船,果然飛快。在一個拐彎處,江面寬闊起來。看見白帝城外之字形的臺階了,那城就隱在一片蒼翠之中。
白帝城的大門,土紅色的墻,高高的門樓。站在門前看,斜對面就是夔門。雙眼自然地直奔它而去。似曾相識,來自圖片,而此時卻是真真實實地站在了它對面,感覺到的是一種瞬間的被震撼。endprint
“白帝高為三峽鎮,瞿塘險為百牢關。”
兩山對峙,便是門。一江中開,是為峽。何為“壁立”?何為“千仞”?任何語言的詮釋在這里都會顯得力不從心。瞿塘峽自此開始,成為三峽中最險要的一峽。我們先順著崖邊一條小路下到離江面很近的一處山石上,為的是看一根鐵樁,那樁很粗,似從石頭里長出,牢牢地與山體長在一起。鐵樁是什么時候留下的?肯定是年代久遠了。鐵樁是做什么用的?有人說是用來拴船的,有人說是用來當“鎮”物的。那位導游的姑娘卻笑而不答,不知是故留懸疑,還是她也說不清楚。此時,只見江面上濁流湍急,波濤奔涌。再抬起頭來放眼夔門,兩面對峙的絕壁顯得更高,更陡,更立。藍天一線,江水滾滾,蔚為壯觀。
進入白帝城。
白帝城內有明良殿、武侯祠、觀星亭等殿宇,有劉、關、張及諸葛亮父子的塑像。我不愛看廟,對塑像的藝術價值也是云里霧里,倒是廟里的石碑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據說,這里存有七十多塊碑刻,從隋代到清朝,歷朝歷代均有所留,碑刻為真草隸篆各種字體,堪稱中華書法藝術之珍品。其中尤以鳳凰碑和竹葉碑最為珍貴。那鳳凰碑刻有一株梧桐,一簇牡丹,一對鳳凰,也稱“三王碑”即樹王、花王、鳥王。雕刻技藝精湛,碑石烏黑锃亮,光滑如鏡,歷經幾百年風雨,顏值依然靚亮,令人驚嘆。而那竹葉碑則刻有竹葉疏朗的三株修竹,而仔細看時,發現那枝與葉巧妙地組成了一首五言詩:“不謝東篁意,丹青獨自名。莫嫌孤葉淡,終日不凋零。”字畫相融,渾然一體。據說這碑的作者是清光緒年間的一位工匠,這就更讓此碑有了一種特具的魅力。
然而,白帝城最讓我不能忘卻的是一只猿猴。
在識得李白那句“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之后,又曾讀到《水經注》中“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的句子,從此,在我的腦海里,“猿聲”便與三峽緊緊地連在了一起。聽到三峽的歌,看到三峽的畫,耳邊就會有“猿聲”回蕩繚繞。這時,“猿聲”就變成了詩情中的一段旋律,畫意中的一筆色彩。自到奉節后我便想過,如今的三峽肯定還有猿猴,但我們肯定是看不到的。孰料在白帝城,我竟然看到了。
那只猿猴被關在一間房子里,有粗粗的鐵欄桿。房前有一棵樹,將房子擋得黑乎乎的。當我們走到房子前面時,那猿猴不知從什么地方一下子就撲到了欄桿上,之后便一動不動地望著我們。我們逗它,它無動于衷;我們喊它,它也不理不睬。它只不停地眨著眼睛,目光躲躲閃閃地看著我們。
這是三峽的猿猴嗎?有誰問。
是的。老鄉抓住送來的。工作人員答。
不是峨嵋山的猴吧?怎么認生呢?
它總是這樣。是只老猴了。一直就是這副悲哀的樣子。
為啥不放了它?
就為給客人看嘛。
看來這猴是永遠出不了這間房子了。我忽地對這只老猴生出了無限的同情。如果不是被關在這個黑暗的小屋里,此時它也許正在三峽的云端霧海恣意地發出聲聲長嘯呢。人類真是一群可惡的東西,慣用殘忍的手段剝奪別人的生命和自由,且不知羞恥。
每一種動物都有生存的自由。
每一只猿猴都應該回到屬于它的天地里去,包括眼前這只老猴。
崖壁蒼松,云騰霧飛,崇山秀峰,大江如練。
我們的小船停在了大江南岸的一處礁石旁。
下去看看,這也是此地獨有的。平日水稍大點兒就看不到,你們運氣好。導游姑娘說。
我們看到的是偌大的一片石灰巖,鋪展在江水邊,高高低低的巖石上布滿了大大小小蜂窩狀的坑,坑都圓溜溜的,但有深有淺,坑壁光滑圓潤,每個坑內都有一枚大小不同的石球。一眼望去,真的好看。誰都沒見過,誰都驚奇。
還是聽明白人說吧。
浪打小的石,小石磨大石,年復一年,百年千年,就成了圓的石,圓的坑。這長江幾千里,也只有此一處。導游姑娘為我們釋疑。
哦,這一景,烙入記憶永存。
在岸邊逗留,往高處爬,在長滿綠色小草的地方抬手便觸到了夔門的絕壁。那絕壁與其他懸崖絕壁一樣,冰涼、粗糙、高低不平,但此時的內心卻裝滿另樣的感慨:觸摸夔門,此生此世難得,天下又有幾人能有這樣的機會?內心感慨無需對誰訴說。回過頭來,更壯觀的景色就在北岸,那就是著名的風箱峽了!
褐紅色的絕壁,陡立得讓人望上去就眩暈,頂上有白云飛鳥。
啊,懸棺!一處,又一處。有的在山洞里,或橫或豎,更多的懸于崖外,橫架在幾根伸入巖石中的木頭上。高高低低,無序地陳列于絕壁上,好一幅天下奇觀。
橫船到對面,再上岸。崖底有古時留下的棧道。站在這里再抬頭,直感到天旋地轉。耳邊只聽得導游姑娘在講:這懸棺可說是千古之謎了。是巴人的葬俗。相傳在兩千多年前的戰國時代就有了。這里的懸棺數量不算多,最多的地方在山后大寧河兩岸的崖巖上,有三百多處。
關于懸棺,早有資料涉獵,但只有站在它的腳下時,才更會發出聲聲驚嘆:啊,當時的人們是怎樣把那么重的棺木弄到那樣高的地方去的呢?
過了瞿塘峽就是巫峽了,巫峽風光最美,峽長谷深,奇峰層巒,云騰霧繞,著名的神女峰就在巫峽。再往前是西陵峽,有兵書寶劍、牛肝馬肺等景點,都很神奇。導游姑娘的指點又把我拉回到眼前。順著她指的方向眺望,峽谷蜿蜒,秀峰入云,大江東去。
忽然想起一句古詩:“萬峰礴磅一江通。”說的就是三峽。
葛洲壩外桃花嶺
杜甫當年有詩云:“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翌日,我們便順江而下,興致勃勃地向葛洲壩所在地宜昌市奔去。
一路風光,美不勝收。堪稱大自然刻意造化出的一條畫廊。特別是神女峰,“神女”二字將那座山峰點化得活靈活現,給人以無限的遐想空間和醉美享受。在凝眸神女峰云飛霧繞之中,聽得廣播里解說,那峰的背后是一片更美的山水,叫巫山,也稱小三峽。那里四季如畫,比眼前這些景色都要美,勝似世外桃源。endprint
真有這樣的地方嗎?
沒想到的是,幾十年以后我竟應巫山縣之約,寫了一首歌,《愛上了你,巫山》:
撫摸你的云霧,
那是天和地的纏綿,
敬仰你的神女,
那是守望萬年的情戀,
煙鎖峰巒如夢,
猿鳴峽谷如幻,
抬眼懸崖百仞千仞,
低眉清流一灣兩灣。
啊,
愛上了你,小三峽
愛上了你,巫山,
帶不走你,就把你珍藏心間,
想你的時候,就抱著你入眠。
漫步你的百景,
那是山和水的棋盤,
走進你的秋色,
那是紅葉王國的盛典。
天外詩仙絕句,
迎面千秋畫卷,
醉眼新居云下云上,
留連歌聲山后山前。
啊,
愛上了你,小三峽,
愛上了你,巫山,
帶不走你,就把你珍藏心間,
想你的時候,就回家來看看。
還是話說當年吧。是日,我們便登上了葛洲壩。行走在壩頂再回望三峽,只見霧氣蒙蒙,山影重重,大三峽好像關上了門窗,那一路的景色都被藏在云遮霧罩里了。眼前是一片茫茫水面和大大小小的船舶。峽已不見,水卻成湖。平靜的湖面讓奔騰了一路的浪頭有了一個歇息之地,倒頭便睡了,且以淡淡的綠色呈現出水的溫柔嫵媚。望著平靜的湖面,讓人很自然地會想起那位逝者留下的詩句:“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
極目而望,逝者的理想終是變成了現實。
五十三米高的大壩,全長二千六百多米,壩寬也有幾十米。工程之宏偉壯麗,讓我不知用什么詞句來形容。須知在三峽大壩未建之前,葛洲壩就是長江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也是長江上最大的水電站。全國矚目,世界矚目。這也是我們這個創作組前來采訪的原因。而從壩頂再轉身向東眺望,江面漸寬,江鷗翩翩,更遠處更是水天煙波,浩浩淼淼。大壩上下兩幅畫卷,宛若一曲平緩遼遠而又大氣磅礴的交響,優美渾厚的弦樂中不時出現長笛或圓號飄柔的復調。
猶如突然之間,定音鼓和打擊樂引出了強烈的銅管音符,交響進入了一個新的樂章。這時,我們已站在大壩前方,撲入眼底的不僅僅是一座巍峨的“西江石壁”,更讓人驚心動魄的是那平湖之水從十多孔泄水閘一齊噴薄而出的排山倒海的氣勢。在壩內蓄水巨大的壓力之下,水流在撼天動地的聲浪中被高高地拋向空中,像一條條白色巨龍騰空而起,轉瞬又劃出一條美麗的弧線重重地落入江中,激起轟轟烈烈的浪濤,之后遁入大江一路東去。
大壩共有二十七孔泄水閘,十五孔沖沙閘,不難想象,如若它們全部開放,那是何等壯觀的場面,又是多么氣派的一曲交響啊!
此時,我真想寫一首氣勢礴磅的歌,感覺有一股熱流砰砰地撞擊著胸口,讓我激動,興奮,甚至想流淚,想呼喊。但是,我卻怎么也找不到一個靈感的突破口,好像被這宏偉的工程震暈了,直到采風結束,我依然不知怎樣來表述我的感受。
不過,激情一旦點燃,它就不會熄滅。二○○五年,三峽集團找到中華全國總工會文工團,委托他們寫一首關于三峽工程的歌。文工團創作室主任趙小也先生約我寫這首詞。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任務,新的感受和舊的回憶在腦海里作了一個拼接,便有了一首《高峽平湖頌》。
你橫空出世,好一派大氣礴磅
巫山白云化作你懷中小花一朵
你風光萬千,新畫卷水天一色
綿綿青山勾畫出你俊俏的輪廓
兩岸城鄉映滿你的笑容
橘子花開點綴你的婀娜
風輕輕撫摸你船閘的雄奇
帆悠悠陶醉你碧波的壯闊
啊
高峽平湖,我的奉獻
高峽平湖,我的長歌
我用神話塑造了你的壯美
你用壯美贊頌了我的中國
你風采泱泱,好一筆重彩濃墨
翱翔的江鷗驚嘆你石壁的巍峨
你日月朗朗,歡聲里巨輪穿梭
萬里神州灑滿了你無窮的光熱
猿啼鳥鳴悠揚你的詩情
朝云暮雨回蕩你的歡樂
神女峰高聳你不朽的豐碑
長江水奔騰你嶄新的傳說
啊
高峽平湖,我的奉獻
高峽平湖,我的長歌
我用神奇創造了你的非凡
你用非凡壯麗了我的中國
歌詞由趙小也和胡俊成兩位作曲家分別作曲,并演唱錄制,由三峽集團收藏。
話題再回到一九八二年的葛洲壩。
在震耳的聲浪中,我們被允許進入壩內。這里是大壩的心臟,有如一個地下世界。真想不到,壩內竟如此闊大。拱形的頂,弧形的壁,都是不知多厚的鋼筋水泥。這里有一臺發電機組,看上去是一個龐然大物,有工人在周圍忙碌著,身影顯得那么矮小。我們被告知,這一臺十七萬千瓦的機組運行了還不到一年,它每年能發電一百五十七億千瓦,主要送往千里之外的上海,將來還要安裝多臺機組。
發電機組嗡嗡地響著,聲音是那么和諧。想到千里之外燈火璀璨的大上海,對這些工作在大壩心臟里的人們不禁肅然起敬。
有誰在我耳邊輕輕說:壩內幾十米深,水會不會把大壩突然摧垮呀?
哦,那將是一場多么可怕的災難呀!
我又看看那些在這里工作的人們,他們都從容不迫地做著自己的事。他們中有誰想過這個問題嗎?但世人應該知道,在那座巍峨的大壩里,有一批這樣工作的人,他們也如深深的礦井里那些長年見不到陽光的礦工,他們都是創造光熱和采掘光熱的人。
要看的地方都看過了,武鋼、二汽、葛洲壩。一場“建設者之歌新作品演唱會”已在時間的某個節點上等待著我們的作品呢。endprint
寫,是該寫東西了。
從這天起,我們一個個便很自覺地將自己關了“禁閉”,禁閉在當時宜昌最上等級的桃花嶺飯店中,極其認真地進入了“狀態”。不知所措的痛苦,靈感突然閃光的興奮,有所斬獲的喜悅。正如一位作曲家朋友自嘲的那樣:“遠看是個沒魂兒的,再看是個跳神兒的,哦,原來是個寫詞兒的。”“遠看是個犯傻兒的,再看是個鬧鬼兒的,哦,原來是個寫曲兒的。”
活靈活現的“狀態”。
這伙人還真行,兩天后一件件作品便出爐了。姜還是老的辣,唐訶和張士夑居然寫了好幾首,胡小石和金鳳浩寫了一首車間工人的,我也寫了一首《啊,明珠》,描繪的是葛洲壩。
回到武漢,我們住進了武漢軍區第四招待所,繼續創作。兩位軍旅作家成了大家都愿意請教的老師。我又寫了一首《建設者之歌》,請唐訶先生提意見。唐訶先生說,這首詞不錯,但三段有點兒長了,改作兩段更精煉。于是,我便改成了這樣:
鳥兒飛走了,
給人們留下了什么?
蝴蝶飛走了,
給人們留下了什么?
我們要走了,
留下工廠礦山一座座。
啊,
我們是建設者,
我們是建設者。
鳥兒飛走了,
去尋找舒適安樂,
蝴蝶飛走了,
去追求艷麗的花朵,
我們要走了,
去創造更美好的生活。
啊,
我們是建設者,
我們是建設者。
現在看,這首詞太一般了,但那時卻覺得不錯。金鳳潔為這首詞譜了曲,很好聽。歌詞在《歌曲》發表后,又有鄧玉華、趙遵程等多人譜曲發表。我還寫了一首《小溪與小河》,云華作曲,后發表在《長江歌聲》。
這年秋天,“建設者之歌演唱會”在十堰舉辦,北京來了不少歌唱家。演唱會上李谷一唱了我作詞的歌《年輕的朋友來相會》,還有一位演員唱了我和云華寫的《小溪與小河》。
到此,“建設者之歌”終于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張枚同: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發表歌詞與歌曲作品1000余首,有近百首作品獲全國音樂“金鐘獎”、“五個一工程獎”和“烏金大獎”等多項省部級獎項,其中由谷建芬作曲的歌曲《年輕的朋友來相會》先后四次獲國家級大獎,并在法國、美國、日本出版和演唱,還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為亞太地區優秀音樂教材。出版有歌詞集《年輕的朋友來相會》、《九十九支曲兒九十九道彎》及《張枚同詞作歌曲選》等。
發表小說、報告文學等文學作品200余萬字(與程琪合作),作品多次獲趙樹理文學獎、全國煤礦文學創作烏金獎、山西省文學藝術創作金牌獎等各項大獎,小說《拉駱駝的女人》還被翻譯介紹到國外。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