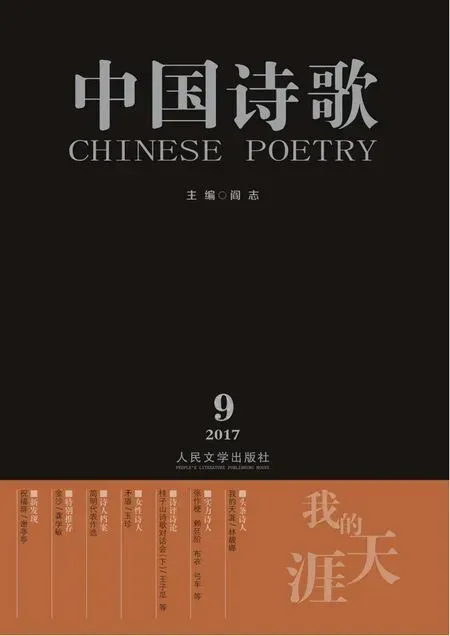詩歌地方性及其他
□趙衛峰
詩評詩論

詩歌地方性及其他
對于詩人,對于詩歌地理性的過度強調與倡揚,也許可將之理解為是一種行動上的文化的田野考古愛好,而在心理上它是個體對知識分子身份的自我確認或期望的一種表現。
---趙衛峰
詩歌地方性及其他
□趙衛峰
A
地方特征或地域意味是詩歌寫作及其理解的暗線.有時它甚至體現于語言的具體運用及錄取方面.它在傳統詩歌領域里相對更為顯態,或以地理表征為顯態,有時,又僅是行政區劃下寫作者群體性詩歌活動,后者的集合無論是為引起注意或性味相投顯然都含有過多詩外因素.從寬泛的文化意義上看,對特定地域的著力的輕重,有時起到的作用又會相反,呈現獨立與特色往往需要相應的前提與參照,這是一個變量,因此參照系的選擇也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由于寫作者常常是以自以為是的個性去"針對"相對的共性參照物,這種選擇(有時亦有與主流意識形態順應或反彈)本身也包含著"投機"(無貶意)式的偶然因素在內。
類若一個人的村莊的精神指向、或相似的依傍情結是一種先外再內的印證過程,這同樣存在一個度的問題.沒有身外物就構不成對"自身"的反省與審視,只是過程中難免出現對"自身"認識的不客觀與不準確而更多地含有拔高、自以為是和示優藏劣習慣,這也反映被知識武裝后的頭腦的復雜性.不只是知識分子,作為復雜而頑固的綜合心理作用,對本鄉本土精神維護的潛意識也貯藏在一般群眾的心中.對于詩人,對于詩歌地理性的過度強調與倡揚,也許可將之理解為是一種行動上的文化的田野考古愛好,而在心理上它是個體對知識分子身份的自我確認或期望的一種表現。
沒人會懷疑地方對個體生命及生活的影響,也沒人能否認一方山水對寫作的有益或無益的作用,這時常見的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暫時"的輕視與忽視地理的影響,另一種是相反.這實際上也是心理作用,有時還可能含有一定"虛"的成分,虛榮,虛偽,甚至虛無---可是,世上應該沒有無根的花朵吧.而這種"虛"的該或不該也不好定論,一個人對地方的認可與否其實也并不重要,地方其實也并不會因此受損害或抬高.在一定時段內,受某一審美趣味的影響和控制都可能使得生長生活在此地的寫作者足踏本地---而其寫作在表面上卻與之無關,但這卻非衡量一個人對本土認可與否的標準.有時由于文學體裁的限制,對地理文化的表面疏離,也可視作是文學形式、形態或個體的心理的調整。
強調地域至上同樣也會趨向不切實際的極端之思.我們生活與寫作肯定會受到特定時間與空間的牽制與作用,并形成一定心理定勢,但寫作以此為核心為主題就值得懷疑寫作的目的,或至少會存在混淆主次的問題.即使特定地方讓寫作有山可循有水可依有特色文化可享之不盡,但寫作并不是以此為最高目的的,文學與文化的地理特色,并不是為特色而特色的,而是為了立此存照---這時,它基本上就完成了任務---它把有效部分呈示出提供了貢獻給時間,并成為其他的參照.如果徽班不進京,它就是地方戲,至多是可能至今還有生命力的地方戲,而京劇如果不兼容并包它又會是什么?
從"樣板戲"這一漸行漸遠的陳詞,不能不讓我們對傳統地理詩歌款式保持一定警惕.由于對詩歌地理性的強調通常與傳統文化的某一凸現部分合拍,與主流意識形態中的某一耀眼部分呼應,它成為了歷來都被認可的另一種"主旋律",問題也一直伴生膨脹,比如過程中就會出現對地理、地域、地方及民族文化的難免的"大"和"空"的宣揚,它還會滋生類似的民族主義地方主義保守主義等,這方面需冷靜和客觀看待。
假定一個國家由幾十個行政板塊組成,如果每一板塊都認為自身是重要、偉大、惟一、優美、獨特---等等,這些思維習慣導致的,大約遠不只是文化心理上的夜郎自大式的狂妄與獨尊.是的,事實上對具體的本土的強調,在強調之時已離開了寫作本身或只限于作者個人因各種后天因素導致的主觀或偏見了.遠古的人們共同體的"圖騰"觀如果是因無知愚昧反而顯得純潔與純粹,現在的鄉土熱風或地理發現論調則遠遠要復雜得多。
B
看:"就廣西而言,作為一個在地理位置及地貌環境上均具有特殊性的省份,理所當然要抓住這些天賦的特征,由此去發掘得天獨厚的獨立性質.……廣西同時是……有獨特的文化傳統和詩歌傳統.……廣西詩人是有福的,因為廣西這個地域為詩歌提供了很多得天獨厚的生長元素,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廣西詩人最應該拋開那種由偏遠、封閉而及狹隘沮喪的心理,正視這些曖昧影響下的可能生長."(引文來自網絡,以下同.)
再看:"湖北是內陸省份中與其他連接地方最多的省……地域文化的多樣化和差異性,熔鑄了詩歌色彩繽紛的審美形態.……當下的湖北詩歌……從創作的方法看,現實主義詩歌、鄉土抒情詩、現代先鋒詩歌和網絡詩歌共在同一時空出現,……從寫作向度來看,當下的湖北詩歌呈現如下特點:其一,以智性思維觀照大千世界,思者之詩與詩者之思共在.其二,詩性與理性共同建構當下詩歌的話語存在.……其三,蒼涼、柔韌與平民悲劇組接的審美追求.湖北詩人大多來自生活的底層,童年的單調、少年的刻苦、青年的遭遇在記憶深處鑿刻出難以磨滅的印記,雖然詩人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從事詩歌寫作,但那種關注平民日常生活,表現生存悲劇的蒼涼之感卻隨處可見……"(粒子)
---其實,將上面引文中的"廣西"換成江西、山西、陜西等板塊都是合適的.將文學貼上地理標簽,從行政區劃、地理文化(之優越感)等角度的這種總結模式多年來并不少見.顯然,各省集中起來的結果,也是由"我省是"或"我市有"之類的堅定不移的自豪感或自信心組成"詩歌大國".這種地理板塊的心理劃分,是中國特色,劃分有時確實又打著過多的投機色彩、政治烙印和模式化語氣并在那一時刻與詩性的距離又悄然拉遠了至少一點。
如果把三十個已有一定歷史與文化特征的板塊通過行政方式再劃分為三百個三千個小板塊,這些小板塊關于詩歌與文學的總結估計仍將是上述模式?!由此是不是可以講"詩歌地理"表面看是類似宏揚獨特的歷史文化,實際上又不算是呢?其實,詩歌可以是但又不是地方歷史文化的呈現與宏揚的最佳工具.再者,如果當事人不再附屬于原有板塊時,他又得調整他的倡揚對象,即使他不否定"隔壁",但作為本能和可理解的種種原因他也必定要先為"自家"說話.譬如遵義如果從貴州劃歸重慶,它以后的類似表達至少又會以"大重慶"為心理出發點了。
不妨再把這個假設繼續下去,把三百三千個板塊細分再細分,到三十億三百億個板塊時,大約最突出的就是自己了---原來,強調"地方"的同時也等于是在強調"自己"?這"個體"當然也不能籠統看待,福克納那一張郵票大的家鄉可以包含無邊的思和事,大大世界,也要終于小小"個體",回歸到內心的小小宇宙,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成為福克納,也并不是在出發時或過程中人人都如是所想.那么,這是不是恰好提示了"詩歌地理"這類概念的內核,并且再次提醒我們,個體重要,"我"重要,如此,就能更好辨識詩歌的主體性之在或不在了。
對地域性的強調必須以相對的地理面積來衡量,一定的"量"是談論地域性的前提,否則難有量變,從這一角度講,將一個城市視為一個具體實在的板塊更為合情合理.雖然我并不贊同某個城市對于詩人的重要和數量有必須性,但得承認有時一個城市的詩歌基本就是或代表一個省的詩歌,或者影響了一個行政板塊的詩歌寫作.作為人類文明的特殊結晶體的城市也更能作為一種時間的相對固定的證據,想想河北,如果它因行政需要被京津分割,行政名稱可能不再,但承德還在,石家莊還在.從地域到地方,也就是從面到點,也許今后充實與更新詩歌地方性傾向的合適方法之一,是用"城市詩歌"現實去更新、去充實明顯帶有傳統守舊與無意地假大空的"地域詩歌"情緒。
C
這種情緒有時也難免逆反和極端.如有人對青海省的詩歌就定義為"弱勢的地域不弱的詩歌",其中憋屈與埋沒感甚是明顯:"……種種現象表明,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中國詩壇對青海詩界的關注、培育……真可謂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那么,這原因能怪"中國詩壇"嗎?或這原因能成為原因嗎?作者繼而敘述道:"首先,青海詩人原籍的多元化是青海詩壇始終不能持續發展和繁榮的根本原因.……當環境改變、退休等諸多原因,這些青海詩人又大多回歸故里安享晚年,或又隨退休的父母遷回家鄉,或下海飄泊世界,等等.無疑,這便形成不了強大的創作群體.""第二,青海省位于中國西部的死角,交通極不便利,文化的傳播直至現在仍圈在自己廣闊的體內,而很少如其發源的長江、黃河般流向全國.""第三,青海詩人的自卑情結左右著他們的創作心態.……第四,中國詩壇對青海詩界有意無意地藐視自然也是迫使青海詩界不能繁榮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五,青海詩壇五十年來缺少領軍人物.在更多的實際情況下,青海詩人似乎更喜歡單干!或者說不得不選擇單干!"(章治萍)."弱勢"原因原來如此?詩人自己是如何理解詩歌的所謂的"繁榮"的呢?
其實,就本文所議,一個五百萬人口的城市可以與一個五千萬人的省區相較,但五百萬人口的青海與一億人口的四川似無可比性,這是不言而喻的客觀事實.而當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到行政區名時,這種比較就更虛妄而不實際.比如說云南詩歌,傳達給受眾的通常是:以云南這個地方為內容的詩歌?關于云南詩人及其作品---幾乎約定俗成的概念也正如此.如此,詩歌之鳥的飛翔其實就受人為劃界限了,它就只能算家禽了.但是,好像眾目關注的有意無意正是家禽,畢竟,那些高高在上的尚未馴服于人的飛禽離我們的肉眼相對遠些---具體說,對"云南省"內的詩人來說,其本土意識(肯定)很大程度又和自然環境(后期則以社會環境、經濟環境為主)關聯得更多更明顯。
關于對地方性的強調,在盲從之外,我們倒也可以將之理解為本土詩人意圖尋找與自然、民族文化和社會環境(現實、現時、現世)的對接的努力,尤其是文化全球化全國化步伐越發緊迫的今天.而且這種努力對于任一文化與自然板塊都是進行時,同時又都是不夠的,多在于重標不重本,臨空蹈虛,故弄玄虛的想象與神經質的盲目膜拜,或是人云亦云的對地表特征、地理現象和簡單的民俗風物事象的克隆式摹寫.故而,這個貌似茂盛的領域事實上是種想當然的泡沫,地域角度的詩歌自古成效就不明顯,想想,古今詩歌把哪一塊地域真正寫活了?離騷把兩湖寫活了?不,已歸于文學史的它更多地提供的是一種文學體裁或形式.它更提醒的可能該是語言的創造及特色運用。
既講到古,問題就還有,古人為什么不像今人這么強調地域(雖然他們也在"思鄉"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實踐著,比如江南詞曲邊塞古風),古人的強調與今人的強調區別何在?這么講多少不公平,古人已去而今人可以古為今用還可洋為中用,更可以享受多種學科和領域結果帶來的便利和合力,但引經據典、隨時接受新學術啟發---可以反復說明地方的重要---并不一定就能證明"地理詩歌寫作"的重要和必要性.因為詩歌---這種文體及其寫作的特殊性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承擔或獨立擔負這一文化任務.詩歌對本土地理的態度,也許要講求一個"平衡"才好,不有意忽視也不著力重視,不在文化園畦里喧賓奪主越位,也不要完全漠然而不涉及.它只是寫作的前提之一,資源之一,也可以并只能是結果之一。
D
談到結果---對詩歌地理意識的強化,在前述的主體性證明與語言探索之外,另種常見的附屬品則是時常疏離寫作本身的"自我中心感"---有時是自大有時自小,有時則是情不自禁的急于尋求參照的心愿,這個心愿有時還會過于強烈.不只是剛才所舉例的青海,各省都存在著欲進入"全國"范疇才能體現自身的愿望,這除了作為本能的認同感,也有話語權欲望摻雜之因,這其實會導致實質上的落后與愿望的落空,還反映出思維的滯后---如果將青海詩歌與全國詩歌對比,這時的全國詩歌是什么,這時的"全國"作為標準或評判體系其實又能是什么呢?其實,也是具體的"省份","省外"而已吧?
如今,天塹不斷變通途,火車早已開到苗家寨,以往所謂的地理差異形成的"隔閡"已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或改善,但對"信息"的接收效果卻是千差萬別,關鍵不是地方,而是人.而說到"省外的"或"外地的"---它當然就不是不變的,也可能不再是最新和最近的,如果傾向于比較,為了比較而比較,地方和民族特色也在這種以中心或主流為潛在標準中失真失重,個體的特色(肯定有)也會失去真正本色。
也正是在這樣的大傳播時空中,就地域及詩歌而言,強勢文化是以傳播為催化劑的以訛傳訛的"紙老虎",所謂強勢通常是意識形態和作為俗文化主要內容的時尚和流行文化,在此,弱勢文化的特性反而自有其獨異與合理性.我們在談論地理詩歌時,必需要以綜合的參照系來尋找優劣對比同異.如果青海是詩歌弱省,廣東按宣傳可謂詩歌大省強省吧,按上述的文化強勢牌子看廣東省,它的背景是"全國"?特色是沿海?那么,何謂強大呢?這前提應該是"廣東"本身能不能成為一種文化形式,這個形式的意義何在?
廣東如今在某些方面確實比其他行政區更能突出地理的"板塊感",其市場經濟發展及由之帶來的種種變化與原有的(傳統文化細節)交融,使得它在中國這個更大的板塊上鮮明而有一定的自身個性."廣東"板塊的凸起,又反過來映現了它本身和其他行政板塊的問題,這個話題較大.簡言之,如果不是經濟的相對明顯發展,廣東板塊的某些不可替代的標識將不會像現在這么明顯,也可說"廣東板塊"出現主要是外力造成,是合力結果,如此看,其他內陸省份對"自身"的強調也有經濟尚不樂觀的原因在內.經濟越發達,文化的融合、同化或整合力度相對而言就越明顯。
但詩歌卻只是文化大樹之枝葉.廣東文化形式,似是一種特定時段(社會轉型后)的中國開放文化(意識形態、商業因素、移民、"拿來"……),它的其他部分則是嶺南原本文化(當地少數民族、原住民和客家人文化).融合后的廣東板塊最明顯的優勢是海洋般的包容,一種主動的吸收與消化能力---這正是一些省區欠缺的.但遺憾的是只呈散兵游勇式的廣東詩歌雖然已有了相當的"量"卻并未因此顯出優勢,仍呈枝葉式的它并未出現有力和真正先鋒的詩歌潮流,沒出現"里程碑"式的詩歌人物,也沒出現科學與有效的重要的詩歌主張,也正由于"地方性"的突出,它只能是一面面彩旗但不是大旗。
這也顯出了它作為特定地方的本來的不足.這個不足當然也是相對的.就如今從詩歌角度看,經濟的發展水平可能形成一種特別的文化場或"語境",但并不是詩文化的真正重要支撐.各省詩人因各種原因會集于廣東,也不代表"廣東",廣東當然也代表不了"全國"(各省),至少我們會覺得要尋找詩歌的廣東的特色是有難度的,它不具人文精神的沖擊力,不像詩歌的江南或上海,具備明顯的人文脈胳和傳統文化資源.當然,一種廣東特有的詩歌精神已初見端倪,譬如精神的自由度、物質化過程里的內心的更新.就這點而言,廣東的詩歌貢獻非常值得肯定。
E
其他"板塊"也是如此,內陸地區對文化特質的強調,仍是一種持續的"內發掘",不同的是一茬茬發掘者的身份的變化---這種身份變化又使得發掘工作確實像一種知識考古,它在每一代發掘者那里都有可能出現些新的東西.當然亦可能是用新瓶裝舊酒。
對地理的強調,潛在的底線肯定是歷史文化因素,延伸出對其的認識和理解后的理性判決,一種精神方面的反復定位.常見的倡導則是因為熟悉、感恩而導致的板塊自豪感與記憶,其中有明顯的感情因素在內,如戀母式的"一邊倒",這種"倒"有時也會顯出失衡,譬如自我中心感、自以為是感、強調人無我有的文化優越感.當然有時也會有"弒父"現象出現---但這種現象更可能出現在一個相對狹小的范圍內,如一個城市。
再如貴州---"山坳上的中國",經濟弱勢、地理復雜、民族眾多(這公文式的既有事實與本文前面引文何其相像),然當下的另種事實卻是因特網和可口可樂依然穿山越嶺像月光一樣涵蓋城鄉,當從地理文學的角度談論這一塊眾所周知的邊地,我們又會發現"標準"這東西突然多余或失效了!就現當代文學而言,作為行政區的"貴州省的文學"其實并不傾向于本土,它更多體現于對主流意識的依靠姿態,有過多的體制文化思維特征.對"貴州"的地理意義上的強調,通常是在對民族民間文化的認識與理性發掘運用方面,就當地多數詩人而言,"貴州"是一種地理心理、地理層面上的共同感,而這種共同感與具體的應該的詩歌寫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是無關的.雖然不排除活用與借用---像當地詩人文本里常見的"溶洞/鐘乳石"意象等多少也與黔地到處的喀斯特地貌有關。
與不少地理板塊一樣,民間文學角度的對地域及民族(少數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和彩繪加工,在很多區域內時常被挪作當代文學尤其是詩歌題材和"主題",尤以史詩情結與神性傾向為主心骨.它當然重要,但不惟一.如果將之當作一種骨氣、一種氣質更好些?生于此處、活于此處、歸于此處,"一方山水"永是環境與背景,這純屬自然(不自然的可能是一味地強調和故作姿態的不屑),它給本土子民的饋贈是與生俱來的氣質,它是"骨肉"而非可換可棄的"衣服"。
每個成熟的寫作者或明或暗都有、都不可能沒有"本地氣質"!而這種植根于又實則超于行政區劃的本土心理,也能解決那種曾經的疑惑,譬如何為湖南文學?只是指湘人創作的文本,還是只是關于該地的文本?在本省媒體上的文本及作者算不算?生活在省外的"老表"又怎么算?屈原算不算?所以,作為一種個人心靈史,鄉情作為一種本能早被深藏心中,既已安放在心,也許合適的態度是---把詩歌的視線與力量移向地方之外、山水之上、人中之人。
如今"現代性、數字化、地球村"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福音,卻也會將人類文化的區域和特異性毫不留情地抹平,這種變化已為眾人所識,也引起有識者的焦慮,從文化心理上是必要堅持本土意識的,關鍵是有度.是保持明智,對本鄉本土應該的自信、認同和親切感是起碼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又怎談得上寬廣與博大?我們總向往遠方,而對遠方的人們,我們這兒也是"遠方",怎能忽略足下,在向外和"拿來"的同時忘了原地尋找和發現.因此,我們隨時需要的是"歷史感",作為鈣質的它是寫作者最易缺少也是最為致命的,沒這種感覺就談不上明智,不明智,就會跟趕時尚而甘讓自己落后,不獨立,讓自己輕易隱沒于人海,沉入板結的公共話語和大眾意識范式之中,寫作意義必然打折。
詩歌地理是一個復雜的命題,事實上即使很簡單的問題要達成共識通常也不可能,甚至達到共識也不等于就完成了命題.因此本文亦只屬零星感悟而并沒有具體針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