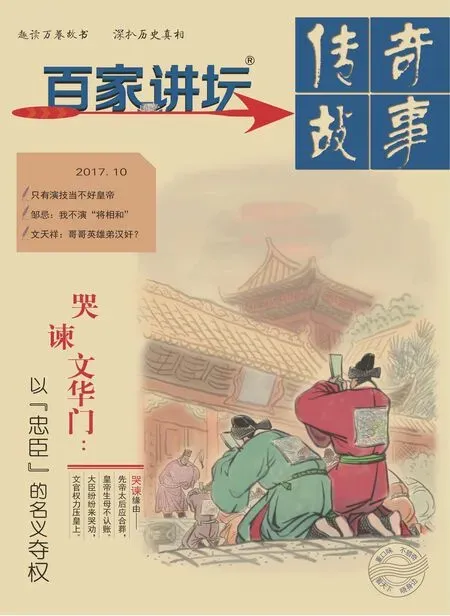宋朝衙內逼死人之后
◎ 吳 鉤
宋朝衙內逼死人之后
◎ 吳 鉤
元祐五年(1090年),京西北路提刑官鍾浚向朝廷舉報了陽翟縣(今河南禹州)知縣趙仁恕。按鍾浚的指控,趙仁恕濫用私刑,私自制造木蒸餅、木驢、鐵裹長枷等非法刑具迫害犯人;用瓦片擦犯人創口,導致犯人大出血;強雇民家女子數十人為奴婢;低價購買紅羅數十匹,然后高價出賣,從中牟利……朝廷立即指示潁昌府成立一個臨時法庭——制勘院,立案調查趙仁恕之事。
按宋朝慣例,趙仁恕的父親趙彥若(翰林學士兼侍讀)理當避嫌,閉門謝客,切不可對此案發表意見。但趙彥若愛子心切,向皇上奏報:他以前當臺諫官時,得罪過王安禮,而鍾浚是王安禮的黨羽,他這次恐怕會挾私報怨,乞請移送別路審理。
考慮到趙仁恕案牽連甚廣,宋哲宗與高太后采取了一個折中的方法:改組制勘院,委任淮南東路宿州符離縣(今安徽宿州)的知縣孟易為制勘院法官,前往潁昌府主持推勘此案。在接受制勘院審訊時,趙仁恕對檢控的罪行多不承認,還提前讓他的妻兒燒毀了登記官錢出納的賬本。孟易也知道趙仁恕背景很深,后臺很硬,最后推勘出來的結論與之前大相徑庭。
宋代司法機構對每一起刑案的審判,都必須有“錄問”的程序。趙仁恕案的錄問官孟正民不同意孟易的推勘結論,提出了反駁:跟原勘差異太大,存在出入重罪的可能,應當重審。于是,朝廷又差官重勘。可轉眼到了元祐六年六月,仍無法結案。檢方控告趙仁恕“非法行杖數,決殺平人”,趙仁恕稱他對此毫不知情;檢方控趙仁恕“買賣剩利”,趙仁恕也稱不知情,這一切都是他妻子所為,趙妻對此也供認不諱……
這一切,讓人不能不懷疑,趙仁恕案的幕后,是不是有高人在暗中指點,替趙衙內洗脫罪名?
于是,朝廷決定將趙仁恕案移送亳州(今安徽亳州)審理。可此時已是盛夏時節,天氣炎熱,除了趙仁恕,受牽連的三百余人也都暫時關押在牢里,苦不堪言;趙妻更是在監獄中病危。因此,潁昌府知府給朝廷發來一份報告,不贊成移路別勘。宰相呂太防與執政的團隊商議后也提出:不如停止制獄,將趙仁恕案全部卷宗調回京師,由大理寺約法裁斷。最終,高太后與宋哲宗采納了這一建議。
大理寺調閱了卷宗之后,只認可趙仁恕強雇民女為婢、其妻賤買貴賣、挪用五貫多錢用于雇人搬家等,認為其犯罪情節輕微。至于其他控罪,則以證據不足為由,不予采信。朝廷根據大理寺的裁定,下敕對趙仁恕做出了處分:革去趙仁恕的官職,并處以罰金。
不料,敕令發布之日,整個御史臺與諫院炸了窩,臺諫官交章上書,奏論朝廷處置失當。迫于壓力,朝廷只好下詔,追加對趙仁恕的懲罰,將趙仁恕押送到陳州(今河南淮陽),監視居住。但臺諫官并未因此罷休,矛頭直指趙彥若妨礙司法公正。

平心而論,趙彥若奏稱鍾浚是王安禮黨人,可能出自挾私報怨之心,確實犯了干預司法之大忌,難逃替兒子脫罪的嫌疑。不過,趙彥若的提議,即本路按發的案件,應當移路別勘,還是有道理的。因為,一起案子如果是本路按發(類似于公訴),然后又由本路司法機關推勘的話,難免會出現司法機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問題。這個問題,要到南宋紹熙元年(1190年)才得以解決。但趙彥若作為趙仁恕的父親,又是皇帝近臣,的確不應該過問案子的審判,所以也難怪臺諫官要彈劾他。
由于臺諫官交章彈劾,趙彥若只好上疏請辭翰林學士兼侍讀之職,領一份閑職。但宋哲宗沒有批準。臺諫官豈肯罷休?又上書彈劾趙彥若的親家——宰相劉摯在包庇他。
面對臺諫官咄咄逼人的攻勢,高太后與宋哲宗自覺已保不住趙彥若,不得不下詔罷去趙彥若翰林學士兼侍讀的職務,改任提舉萬壽觀。過了一個月,又派人送趙彥若到青州,趙彥若隨即雇傭一葉客舟,飄然而去。
對趙彥若的罷職,劉摯是憤憤不平的。他說,趙彥若只不過是一個書呆子,全然不諳世故。他救兒子,純粹是父子之愛,結果卻要受這等處罰,他因為是姻親,避嫌不敢言,每見同僚奏及彥若之事,都先下殿避嫌,但他日必會為他辯白。
然而,此時劉摯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臺諫官對劉摯發起了連環彈劾,稱趙仁恕犯法,而他不秉公處理;阻撓司法公正,暗中結黨營私;身居相位,徇私枉法。如此,劉摯只好再三提出辭職。結果,宋哲宗免去了劉摯的宰相之職,讓他出知鄆州(今山東東平縣)。
趙仁恕一案,盡管在審理過程中,其父趙彥若企圖干預司法、救護兒子,大理寺的約法斷罪也有草草了事之嫌,但是,趙彥若卻因此惹火上身,被臺諫官輪番轟炸,最后不得不解職還鄉;劉摯替趙彥若打抱不平,也受臺諫官彈劾而罷相。那些抗議趙仁恕被輕判、彈劾趙彥若干預司法的臺諫官,在他們的奏疏中再三強調了一個觀點:司法公正。宋人的這一司法觀念,即便過了一千年,也不會過時。
編 輯 / 子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