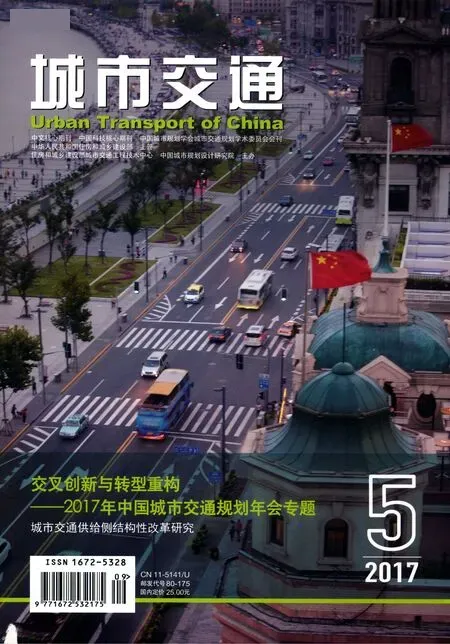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
全永燊,潘昭宇
(1.北京交通發展研究院,北京100073;2.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北京100045)
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
全永燊1,潘昭宇2
(1.北京交通發展研究院,北京100073;2.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北京100045)
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實質是以改善交通供給為著眼點,通過資源配置方式的創新,提升交通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基于城市交通供給的服務產品社會經濟屬性分析,認為當前中國城市交通供給模式存在供給決策缺乏科學依據和法制約束、供給策略失當、發展理念錯位、服務供給與市場需求脫節、交通供給過分依賴資源驅動等問題。指出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合理性、有效性、科學性的衡量標準。提出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目標、方向和當前改革的重點,包括調整交通供給模式、重組交通體系結構、優化交通供給策略等。
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目標;改革重點;供給模式;資源配置
0 引言
過去10年,城市交通在支持中國新型城鎮化總體戰略實施、保障城市經濟社會健康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同時也面臨交通擁堵、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基礎設施建設及經營困難重重等問題[1]。2016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近期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業內討論的熱點。毋庸置疑,中國大城市的交通發展模式已經到了轉型的關鍵時期。需要反思的是,在城市交通形勢日益嚴峻的今天,城市交通供給側的根本問題是什么,改革的突破口在哪里?
1 對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
1.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
為應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產業結構、要素投入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等結構性問題,2016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要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簡稱“三去一降一補”),從生產領域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使供給體系更好地適應需求結構變化[2]。
1.2 城市交通供給模式分析
論及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城市交通供給哪些服務產品?這些服務產品的經濟社會屬性如何?誰是交通服務品的提供主體?誰又是交通服務品的生產者?
1.2.1 城市交通供給產品的社會經濟屬性
文獻[1]就城市交通供給產品的社會經濟屬性進行了論證闡述,根據公共經濟學理論對社會產品屬性的界定,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及所提供的服務基本都屬于準公共產品及私人產品,具有明顯競爭性和排他性,應該按照市場化原則或政府與市場共同分擔的原則提供[1](見表1)。同時,公共產品的提供和生產是兩個不同的行為,政府是公共產品提供的主體(非唯一,社會團體或私人也可以提供),但并非是公共產品生產的主體,公共產品的生產主體是市場[1]。
1.2.2 當前城市交通供給模式
中國城市(專指大陸范圍,以下同)交通服務品現行供給模式建立在公共產品供給制度體系基礎上,而這一制度體系是從計劃經濟體制沿襲而來的。中國公共產品供給制度的主要缺陷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門的過度壟斷。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門規模過大、公共財政負擔過重、公共經濟活動中的交易費用過高、公共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過低,社會公共服務供給不足。

表1 城市交通設施的經濟學屬性Tab.1 Economics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就城市交通供給模式而言,問題的根本在于對城市交通服務產品社會經濟屬性以及公共產品生產與提供主體缺乏科學界定。迄今,中國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經營與服務仍被一概視為公共產品,政府既是提供服務的唯一主體,也是服務生產的主導者。顯然,無論在供給理念、供給制度還是供給機制上均與市場經濟環境下城市交通服務品的社會經濟屬性及資源配置方式要求相悖,已無法適應新的經濟社會形態下交通可持續發展的需要。突出表現在:1)市場主導的城市土地開發與政府主導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走在彼此無交集的兩條軌道上,TOD模式無法實施,交通與城市的協同發展關系從根源上難以建立和維系;2)無法擺脫資源配置效率和效益低下(甚至錯配)、市場價格扭曲、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尷尬困境;3)以公共資源投入為主要驅動力,受制于資本(資源)投入邊際收益遞減規律,最終必然導致供給增長不可持續[1]。
2 現行城市交通供給模式的主要問題
現行政府主導的供給模式的主要弊端在于供給決策缺乏科學依據支持和法制約束、供給策略失當、發展理念的錯位與沖突、與市場需求脫節、供給創新不足等。
2.1 供給決策缺乏科學依據和法制約束
城市交通供給的決策依據是城市未來交通需求與城市互動協調發展的走勢和基本格局。按照中國相關法定規劃制度體系,未來這一走勢與最終格局主要取決于城市規劃的制定與實施。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中國正處于快速城鎮化過程與經濟社會轉型階段,城市交通規劃面對諸多不確定因素。規劃的不確定性既有規劃客體(城市空間形態與功能配置、土地利用、社會人文與經濟等)的不確定性,也有規劃編制與實施過程中不同利益主體意志博弈的不確定性。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新規劃模式還有待探索。另一方面,當下許多城市主政者漠視規劃的嚴肅性和法律約束力。“一任領導一張圖”的現象屢見不鮮。規劃的隨意性導致城市交通供給決策無定式、供給規模無底數、供給方向(策略)飄忽不定。在供給側的無度與無序狀態下,城市交通與城市發展的適配關系難以建立和維系;資源配置的合理性、供給有效性以及社會公平性無法保障。
由于供給決策的監督約束與問責制度體系的缺失,公共資源配置決策者的隨意和任性經常造成資源錯配和資源浪費。北京、上海、杭州、呼和浩特等許多城市曾經提出(或仍未放棄)在城市中心區新建高架或地下快速路。面對有限的通道空間資源,按怎樣的優先級配置不同的交通方式,如何建立經濟資源配置中的公共財政資金使用監管及社會投資收益保障體系等,以避免資源錯配、資源浪費,是亟待解決的難題。
2.2 供給策略失當
長期以來,交通業界學者在檢討城市交通發展歷史教訓時,普遍認為中國城市交通供給是消極被動的需求追隨型模式,即注重資源(自然資源、經濟資源、社會事業資源)投入驅動的外延擴充、忽視基于技術和制度創新驅動的內生增長;注重系統規模,忽視系統結構及整體協同效率;對個體機動化交通無節制的需求挑戰一味遷就姑息,導致資源配置的錯配和低效等。就現實問題的表象而言,上述批判無可厚非。然而就供給的普適性原則而言,問題恐非錯在需求追隨,而是在于對需求是否有科學的判斷以及對供需依存制衡關系的正確理解。
首先,大部分城市并未以需求構成分析為依據,在審慎的科學論證基礎上確定交通供給規模與供給方向。城市交通建設往往出于緩堵的應急需要,甚至挾有彰顯主政業績之雜念,一味追求系統規模的擴充和硬件設施標準的高大全,忽視系統功能、目標和客觀需求的適配關系,忽視系統功能層次級配結構的合理性。例如,城市路網的規模擴充大概每年均不低于3%~4%,而路網次干路、支路不足等先天性結構缺陷數十年依然如故[3]。軌道交通重規模、輕結構的傾向則更為突出。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地鐵規模均躋身世界前列,遠超越歐美幾個大城市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在如此繁榮的發展局面下,一個不容忽視的嚴重失誤卻是無法掩蓋的——龐大的系統規模與失衡的系統功能層次結構在世界大城市軌道交通發展史上少有。許多城市既未對軌道交通合理的服務功能定位及發展目標進行深入論證;更未以不同空間層次出行需求構成類型與相應服務標準要求為依據,合理選擇軌道交通模式與系統技術制式,構建經濟合理的多元化軌道交通結構體系。建設規模上盲目攀比,系統制式和標準一味追求所謂高、精、尖、奇,而支持城市功能疏解、引導城市空間結構優化調整所需要的市域軌道交通快線、市郊鐵路以及提高城市中心區軌道交通可達性所需要的中低運量等級軌道交通系統嚴重匱乏[3]。不僅如此,在道路系統及軌道交通運營網絡規模不斷擴展的同時,對消除既有系統內久已存在的瓶頸或短板未給予應有的重視,以致嚴重影響系統整體協同效能發揮。
其次,公共交通體系內部的結構性失衡問題日漸突出[4]。北京、上海及廣州等大城市在軌道交通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忽視公共汽(電)車系統應有的功能地位與服務資源,公共汽(電)車客運量呈現逐年下降趨勢。
第三,重設施建設、輕系統運營效率的傾向依然存在。不僅城市道路與公路的交通運行管理(路權分配、交通組織、秩序管理、信號標志系統運用等)尚有較大的改善空間,軌道交通和公共汽(電)車服務系統的基本原則——建設為運營服務,運營為乘客服務——也未真正落實[5]。
2.3 發展理念錯位
堅持公交優先發展,對小汽車出行采取適當的限制已成為當代大城市交通發展公認的基本戰略原則。但許多城市由于在交通發展理念上的錯位,交通供給行為恰恰背離了這一戰略原則。例如,許多城市在堅持公交優先的同時,又在為改善小汽車出行條件不斷增加機動車道與停車設施供給。
為推行公交優先策略,發揮公共交通的比較優勢,往往需要在路權分配上向公共交通傾斜,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效率,抑制小汽車出行需求。可以說公交優先與著眼于改善小汽車行駛條件的緩堵本身是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立面。然而,中國許多大城市卻在高峰時段小汽車出行速度已高于公共交通40%~60%的現實情況下,仍不惜損害行人和自行車出行權益,一味地為小汽車拓展行駛空間,甚至不惜損害環境與景觀修建高架或地下快速路。殊不知以小汽車出行需求為導向的治堵措施,不僅會對小汽車出行需求帶來更大的刺激,而且也必將大大抵消公交優先的實施效果。治堵的措施反而成為致堵的禍根[6]。
再以停車設施建設為例,中國大城市停車秩序混亂已成為飽受詬病久治不愈的頑疾。問題根源在于政府對城市停車設施建設與經營服務的商品屬性定位及發展模式一直不明確。一方面要顧及“以靜制動”限制小汽車出行需求過度膨脹的需求管理原則,適度控制停車設施供給規模;另一方面,政府又要應對(屈從)來自小汽車擁有群體的社會輿論壓力,想盡力擴大停車設施供給,卻又苦于財力和資源配置能力而束手無策。這種自相矛盾,相背而行的決策行為必然導致停車問題陷入政府為難、社會資本觀望、市民述求無門的尷尬境地[1]。
2.4 服務供給與市場需求脫節
僅以城市公共交通服務系統的發展歷程為例,中國大城市交通服務與市場需求嚴重脫節的狀況便可見一斑。多年來,盡管公共交通建設與經營的投入逐年持續增長,而邊際收益卻持續遞減,交通結構優化的成效甚微。問題在于長期以來在政府壟斷經營體制下,公共交通經營服務模式的單調與市場客觀需求多樣性之間無法調和的矛盾。2004年之后,中國公共交通經營權陸續收歸國有,發展至今在服務宗旨、經營體制、運力配置及組織方式等關鍵要素上均愈來愈難以適應細分市場的多層次差異化需求,服務吸引力每況愈下(見表2),以致公交優先的戰略實施一再受挫。以北京市“門到門”全程出行速度為例,公共汽車只有小汽車的56%、地鐵也僅為小汽車的79%[7];以極高資本投入和規模空前的軌道交通建設換來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提升的同時,小汽車出行需求急劇膨脹勢頭并未得到預期的抑制,相反自行車出行比例持續萎縮。

表2 中國城市公共交通服務系統特征Tab.2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public transit service system in China
不僅如此,在面對城市日常出行需求的供給方式體系中,幾乎所有大城市竟然漠視占出行構成50%以上的步行和自行車交通需求。在規劃、建設及管理等環節很少顧及步行和自行車交通的出行環境,以致城市步行和自行車出行方式日益萎縮。以北京市為例,2014年自行車出行比例僅為11.3%,從1986年62.7%至今持續下滑(見圖1)。當這部分需求轉向公共交通或小汽車時,必然造成交通資源浪費,給道路交通帶來巨大壓力。
2.5 交通供給過分依賴資源驅動
以政府為主導的交通供給模式過分依賴資源(土地、能源、資本等國有資產)驅動,而忽視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對供給增長的驅動。具體表現在:技術研發投入少、科技研發成果轉化率低、交通服務品生產組織模式一成不變、理論創新及探索成就乏善可陳。

圖1 北京市歷年交通結構變化Fig.1 Travel mode share by year in Beijing
顯然這種供給模式不可持續。首先,依賴資本投入與土地供給的資源驅動力,必然陷入城市空間過度無序擴展—需要更大規模交通基礎設施支撐—繼續增加土地出讓量以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惡性循環;其次,依賴資源驅動也無法擺脫邊際收益遞減的魔咒,難以為繼;第三,政府主導下的科技研發體制嚴重制約了技術創新與成果轉化,不同部門之間的資源無法共享,企業及相關研究機構難以獲得必要的政策與資源支撐。
3 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與方向
3.1 城市交通供給模式變革的要求
城市交通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是在資源與環境承載力允許條件下,以公平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實現供需平衡,其實質是資源配置[1]。近期國家層面再次發文明確指出,從廣度和深度上推進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創新配置方式,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9]。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上就是以改善交通供給模式為著眼點,通過資源配置方式的創新,提升交通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堅持合理性、有效性、科學性的“三性”標準要求:
1)城市交通供給的合理性。
城市交通供給以支撐城市和綜合交通體系的協同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目的。因此,衡量城市交通供給是否合理的標準,就是供給模式是否與城市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戰略相吻合,供給水平是否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配。
2)城市交通供給的有效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是要加強優質供給,減少無效供給。城市交通供給是否有效主要取決于在城市可持續發展要求前提下,是否最大限度改善城市交通供需平衡關系,其衡量的標準在于城市交通供給的投入產出比,即供給的效率和效益,關鍵是創建資源配置方式。
3)城市交通供給的科學性。
城市交通供給的科學性是針對供給的驅動要素而言,亦即是以依賴資本(資源)投入驅動供給增長,還是以技術與生產組織的創新作為驅動力。城市交通供給模式的科學性主要體現在技術創新與建設經營組織方式(制度)創新對于實現資源配置效益和效率最大化的貢獻率。技術和建設經營組織方式的創新主體均在企業和市場。因此,核心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3.2 戰略目標和方向
中國城市交通服務供給制度的主要缺陷是政府及其公共部門過度壟斷,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公共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低、供給不足、公共財政負擔過重。根據前文對城市交通供給的社會經濟屬性分析,結合當前政府主導的城市交通供給模式帶來的系列問題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性”要求,確定改革的戰略目標應以滿足公共服務需求、增加有效供給、提升服務品質為首要前提。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主要在于“三堅持、三提升”:
1)方向一:堅持市場主導與政府引導相結合,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效益。
從深度和廣度上推進市場化,創新資源配置方式,發揮市場在城市交通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在規劃引導、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等方面的職能,構建交通供給服務競爭機制(包括公共部門內部競爭),形成交通供給服務的多元化和適度規模化服務體系,提升交通服務需求實時響應能力,給消費者創造更多的交通服務選擇機會,滿足城市多層次、差異化的交通服務需求。
2)方向二:堅持交通供給的公平與效率兩大標準,提升整體公共服務水平。
堅持公共產品供給模式選擇的公平與效率兩大標準,核心是建設好法治環境與社會誠信體系,通過調節政府供給與市場供給達到公平與效率的博弈與平衡,兼顧城市交通發展的經濟效益,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平,實現各種公共產品的需求與供給平衡,達到整體公共效率最優。
3)方向三:堅持交通供給與城市發展有機融合,提升城市活力。
堅持以人為本的服務宗旨,尊重社會不同群體出行選擇權利的公平與公正性,交通供給要突出與城市功能的有機融合,以滿足城市公共空間功能多元化和包容性為前提,促進城市空間的重構,支撐建設集約、高效、環境友好型的城市,提升城市活力和魅力。
4 改革的重點
4.1 改革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經營體制
1)建立市場主導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體制與經營模式,提高資本運作與資源利用效益。
在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公共交通服務、停車建設與運營等方面全面改革,建立市場主導的新體制。引入社會資本、推行PPP模式,推進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市場化。通過模式創新切實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實現公平高效的服務供給。
當前首要任務之一是全面改革公共客運經營服務系統。從檢討和修正公共交通服務宗旨、轉變經營服務理念入手,推進公共交通服務的市場化,面向社會不同階層各類差異化出行提供可供選擇的服務體系。在停車設施供給上,堅持用者自付的市場交易原則,明確政府、經營者、用戶三者的權責,加快推進停車產業化與服務的市場化發展進程。
2)提高政府在規劃制定、市場監管中的作用,提升規劃嚴肅性和科學性。
政府首先需要保證交通供給基本前提的穩定,即強化規劃的嚴肅性、法定地位,堅決杜絕“一任領導一張圖”。要嚴格按照法律程序修改、調整城市總體規劃,建立規劃的問責機制。
3)建立健全公共治理體系,避免政府和市場雙失靈。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涉及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創新,同時也必然涉及社會治理體制的創新。政府壟斷的社會治理格局受到多元社會治理主體合作治理要求的沖擊,無法適應以市場為主體的供給模式。在城市交通規劃—建設—運營服務領域亟須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新格局,正確處理好政府、市場和社會之間的職能與權益關系,促進交通基礎設施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與需求高效對接。只有這樣,方能真正保障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平,既防止政府失靈,也可有效防范市場失靈風險。
4.2 重組交通體系結構,實現區域與城市綜合交通體系跨界融合
城市綜合交通體系與都市圈、城際、區際交通已日益融為一體,以京津冀為例(見圖2),不同層級之間相互融合、相互交叉、融為一體,特別是相鄰層級在功能、服務上都有所重疊。
城市綜合交通體系的重組改造是當前和未來不可回避的戰略任務,必須打破體制和權屬關系藩籬,重構區域—城市新結構體系,將區際、城際、都市圈交通與城市交通融為一體,滿足一體化發展及資源整合的需要。
4.3 優化交通供給策略,應對城市交通當前的突出矛盾

圖2 京津冀城市群多層級交通示意Fig.2 Hierarchy of multi-level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Beijing-Tianjin-Hebei metropolitan areas
從提升城市交通供給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角度,當前應從城市規模、城市區位環境、城市發展階段的實際狀況出發,制定差異化城市交通供給策略和政策,支撐城市交通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1)把握當前主要矛盾,優化城市交通設施結構。
中國城鎮化率已達56%,經過改革開放近40年基礎設施的建設,特大城市和大城市道路網、軌道交通網架構已基本成型,交通設施的主要矛盾已經由過去的規模不足演變為結構失衡。因此,大城市交通供給應著眼于完善道路網、軌道交通網的系統功能層次級配結構,尤其是強化道路網絡的次干路、支路等微循環,軌道交通網絡的市域(郊)軌道交通、中低運量軌道交通層級,并重視道路網、軌道交通網與綜合交通樞紐及客、貨運場站的銜接協調關系。同時,重點要改善交通設施系統存在的瓶頸或短板,提升系統整體協同效能。
2)服務城市長遠發展需求,優化城市交通結構。
交通結構是城市交通問題的根本和核心。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決定中國城市必須堅持公交優先發展戰略,走綠色、集約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城市交通供給應著眼于城市長遠發展的角度,在投資規模、投資結構、重點建設項目安排等方面必須朝著有利于步行、自行車和公共交通等綠色出行方式和集約化出行方向傾斜。有限的道路資源也要按照步行、自行車、公共交通、出租汽車、小汽車的次序優先原則配置。
3)交通供給側改革與需求管理并重,提高供給應對水平。
實踐經驗證明,供給與需求是交通發展中相互依存與制衡的兩大子系統。維系城市交通的可持續發展既需要供給側改革,也不可忽視需求調控。僅就交通結構優化而言,要想實現小汽車出行方式向公共交通方式轉移,單靠公共交通運力擴充和服務水平改善仍難以如愿。要實現交通結構優化的目標,必須在優先發展公共交通的同時,對小汽車采取必要的需求管理措施。公交優先與需求管理兩大策略務必同時兩手抓,而且兩手都要硬。科學的常態化需求管理體系的建立應符合公平、高效、低成本原則,要把技術手段和經濟手段作為首選,輔之必要的應急行政管制手段[1]。
4)重視交通信息化建設,提升交通供給利用效率。
為更好地發揮交通設施供給利用效率、提升交通供給的科學性,當前還應該重視交通信息化、智能化建設。首要的是建設完善交通信息化的基礎層(覆蓋交通規劃決策、建設與系統運營管理、交通服務全領域的綜合信息平臺),建立滿足交通系統內在結構完善以及與外部環境(主要是城市空間動態演變)相協調的實時信息感知系統。在此基礎上,建設上層信息化應用層面的智能交通。
5 結語
本文通過對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讀,指出當前以政府為主導的供給模式與城市交通設施的社會經濟屬性不符、與可持續發展理念相悖,并指出現行供給模式存在供給決策缺乏科學依據和法制約束、供給策略失當、發展理念錯位、服務供給與市場需求脫節、交通供給過分依賴資源驅動等問題。指出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是提高城市交通供給的合理性、有效性、科學性,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戰略目標、改革方向和當前改革的重點。由于城市交通的系統性、復雜性,未來還需要針對城市交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體系,結合城市交通各行業特點進一步深化研究。
[1]全永燊,潘昭宇.中國大城市交通市場化發展戰略研究[J].城市交通,2017,15(2):1-8.Quan Yongshen,Pan Zhaoyu.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Marketing Transportation System of Chinese Metropolis[J].Urban Transport of China,2017,15(2):1-8.
[2]網易新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根本目的是提高生產力水平[EB/OL].2016[2017-07-15]http://news.163.com/16/0127/07/BEAN7GTE 00014Q4P.html.
[3]全永燊.當前城市交通規劃建設領域值得關注的傾向[J].城市交通,2013,11(2):1-5.Quan Yongshen.Unignorable Trend in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J].Urban Transport of China,2013,11(2):1-5.
[4]郭繼孚.城市公共交通優先發展戰略背景下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點思考”[R].北京:北京交通發展研究院,2017.
[5]全永燊,余柳.北京交通十年發展回顧與反思[J].北京規劃建設,2015(B6):24-27.
[6]全永燊,溫慧敏,潘昭宇.“治堵”還是“致堵”?:對當前治理城市交通擁堵對策的反思[C]//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交通規劃學術委員會.中國城市交通規劃2011年年會暨第25次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城市交通規劃學術委員會,2011:39-43.
[7]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市第四次綜合交通調查報告[R].北京:北京市交通委員會,2012.
[8]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北京市交通運行分析報告(2015年)[R].北京: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2016.
[9]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EB/OL].2017[2017-07-15].http://www.gov.cn/zhengce/2017-01/11/content_5159007.htm.
[10]潘昭宇.城市群交通要解決什么問題[EB/OL].2017[2017-07-15].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701320.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Quan Yongshen1,Pan Zhaoyu2
(1.Beijing Transport Institute,Beijing 100073,China;2.China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Beijing 100045,China)
The essence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i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transportation resources allocation through innovative capital allocation,which focuses on increasing the transportation supply.By analyz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attributes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service,this paper points out several issues in urban transportation supply mode in China,such as lack of scientific base and legal regulations in supply-side decisions,improper supply-side development strategies,mismatched development concept,gap between service supply and market demand,excessive resources-driven policies,and etc.The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should be measured in a rational,effective and scientific way.Finally,the paper proposes the strategic goal,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priorities of the reform,including adjustment in transportation supply model,restructuring transportation system,and optimizing transportation supply strategies.
urban transportation;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trategic goal;reform priority;supply model;capital allocation
1672-5328(2017)05-0001-07
U491
A
10.13813/j.cn11-5141/u.2017.0501
2017-07-21
全永燊(1941—),男,遼寧錦州人,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原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交通規劃、交通工程。E-mail:quanys@bjtrc.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