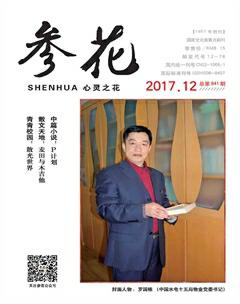試論“四君子”畫藝術意蘊之變遷
摘要:《四君子》系列作品從傳統出發而求變,之于社會生活的意義,一是大眾的,二是個人的。因為就個人來說,藝術的教化作用已然達到。結合個人的創作及論文寫作感受,“四君子”題材依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只是被當下社會太多的嘈雜所遮蓋,藝術家應該以此為職責,創作出能引起大部分觀者共鳴的作品,重新喚起或加強人們對“四君子”所象征品格的重視,使社會風氣有所改善,這是“借古開今”的“成教化,助人倫”。
關鍵詞:“四君子”畫 藝術 意蘊 變遷
一、高尚品格的傳承
創作《四君子》系列作品的第一個理念就是在當下繼續傳遞它們所代表的高尚品格。由于時代的原因,我們迫切需要對傳統文化中積極健康的方面復興并發揚光大。但這里面也存在著諸多問題,比如對于“四君子”的認知,現在大部分的人認為這屬于過時的意識形態。具體表現在:如果家里掛了“四君子”相關的藝術作品,則認為這是附庸風雅,是過時的觀念。不現代、不洋氣。當然我們承認,社會上有部分藝術家的作品流于俗氣,也有大量的相關印刷品等衍生物品的質量也并不高。可它們所承載的文化內涵并沒有變,而我們看見一幅技法純熟、表現生動的“四君子”作品時,能想到高雅高尚,而面對部分技巧拙劣的作品,就對其嗤之以鼻,但從“成教化”的角度講,只要你在看見作品的同時想到它的含義就夠了,便達到了教育作用。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如果部分人在附庸風雅的過程中,藝術作品對其能產生一點點的教化作用,那也是對其品格的升華。
“四君子”的題材可以說與中國花鳥畫的發展同步。早在唐代花鳥畫獨立成科的時候,就已經有很多擅長“四君子”題材的畫家了。不過這一時期,“四君子”這個名稱并未出現,也沒有寓意,只是作為花鳥畫的一個題材而出現,直至明代《梅竹蘭菊四譜》的出現,開始把梅蘭竹菊稱為“四君子”。
“四君子”的藝術品格是在文人畫興起之后不久增加的。文人畫講求畫中的意境,以及畫外之意,借物以言志則是最終的表達。梅花開放在冬季,要經過冰雪的洗禮“凌寒獨自開”,所以其代表傲骨;屈原因追求高尚完美的人格而寄情于蘭,詩歌有太多關于蘭花的贊美。《九歌》共十一篇,就有七篇關于蘭的(相關屈原作品中關于蘭花的研究文章太多,這里不做贅述),因受屈原的影響,蘭花所代表的高潔性格便逐漸成為了文人共同的理想追求,所以關于頌蘭的詩、詞層出不窮。《孔子家語·卷五·在厄第二十》記載:“芝蘭生于深谷,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蘭代表潔身自好,孤芳自賞;竹的寓意也深遠多樣,竹因長青,因此與松一樣象征著生命的頑強,竹子空心,因而也代表著謙虛、虛心的精神。竹干有節,是氣節的象征。竹還有個特質就是彎而不折,折而不斷,即使遇見大風雪也不會彎曲,反而會頂住風雪的壓力及吹打,因此襯托的竹節非常有力度。同時也象征高風亮節以及品德高尚。菊花在嚴寒中盛開,代表著不趨炎附勢。前文提到過,任何藝術都與其時代背景息息相關,梅蘭竹菊被賦予這么多象征意味,是因為文人畫的崛起,加之后來宋的滅亡,使之所蘊含的意味更加深遠高尚,代表了文人的氣節。
元以后至明清,因為政治及經濟原因(資本主義萌芽),繪畫市場化,“四君子”也逐漸地世俗化,所含意寓又進一步增加。但其代表的文人風骨、高尚雅趣未曾改變,一直影響至今。
二、“借古以開今”
《四君子》系列作品的“借古開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即技法與功能。 技法將在第三章詳細論述說明,而功能主要是指教化功能。
張彥遠為繪畫教育功能的定義為“成教化,助人倫”,而我們所知,藝術的教育功能是通過藝術語言來表現的,讓主體的觀念,思想融入在藝術形式之中。前節詳細論述說明了“四君子”所代表的藝術品格的傳承,而我們需要將這些品格繼續發揚光大,因為目前社會需要這樣的品格重新被人們所重視,所以“借古以開今”。
藝術的形式與靈感都是源自生活中的積累與“頓悟”,所以自然反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除了其形式美,藝術有前文提到的教育功能,認知的功能,以及形式審美功能。純審美的藝術形式也是一種非常優秀的意識形態。因此在“借古以開今”時,我們不能以偏概全,太過武斷。因為藝術的教育功能有顯性的也有隱性的。顯性的如“四君子”、二十四孝圖等,無論觀者是否有太高的藝術修養,抑或沒有,其通過生活常識的判斷便能領悟其中所含的教育意義。隱性的如抽象畫作,這就需要觀者有一定的藝術修養,通過對抽象形式的領悟,產生審美共鳴,使自己的審美、人格等都得到了升華,這是優秀作品的共性。
三、《四君子》系列作品的意象賦彩
“六法論”中說隨類賦彩,是要隨“類”而“賦”,就是根據物體本有的色彩來畫。宗炳在《畫山水序》中就講“以色貌色”,但文人畫興起之后,講“繪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追求繪畫的神似,這一點與顧愷之的“傳神論”相呼應。但作為意象表現,即使是“隨類賦彩”,也會不自覺地摻雜作畫者的主觀情緒。
在傳統的“四君子”作品中多用墨,自近代多為墨彩結合。《四君子》系列作品中,鳥都用傳統的寫意形式,用“墨色”表達,而主體梅蘭竹菊選擇用色彩來表達。《四君子》中《梅》《蘭》《菊》均以墨與酞青藍的混合色為主色,色墨交融,顯得恬靜淡雅,富有文人氣質。《竹》亦是用同等方法所畫,當然歷史上以墨竹為主流,如文同的《墨竹圖》,也有“紅竹”的例子,如蘇東坡用朱砂畫竹,近代亦有很多紅竹作品。但在《四君子》系列中,色彩需要以破而立。從系列作品的整體來看,色彩需要“破”,因為全部為同一色調,畫面會顯得平,進而產生呆板,雖然雅致但缺乏變化。所以《梅》《蘭》《菊》《竹》中鳥的暖色形成呼應過度,再與印章相呼應,使整個系列作品更加富于變化與統一,色彩上冷暖相對,形式上破中求立,具有更強烈的視覺效果。
《四君子》系列作品在題材與表現形式,甚至筆法等都為傳統的情況下,在“賦彩”這一項選擇了創新,在傳統中求創新。王原祁說,“設色即用筆、用墨意,所以補筆墨之不足,顯筆墨之妙處”;方薰在《山靜居畫論》中說“設色不以深淺為難,難于彩色相和,和則神氣生動,否則形跡宛然,畫無生氣”。這兩段話雖在原文中是為山水設色做鋪墊,可作為“賦彩”,花鳥畫中運用更為廣泛。前段說過,文人畫“四君子”多以墨為主,而《四君子》系列作品用“色”與“墨”的交融來創作,以求達到山水畫中“和則神氣生動”,即氣韻生動。這是花鳥與山水技法的互動,在傳統中創新而又不脫離傳統,所以也更進一步地豐富了其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因為“四君子”意象所代表的精神屬于崇高之列,但究其本源,亦以人為本,太過高雅崇高則遠離生活。無論是藝術家還是平常百姓,都是有血有肉的鮮活人物。因此,在當下藝術創作中,我們既尋求傳統的崇高精神,也應該使其更加融入生活,無論從形式還是內容上都該如此。這也就是前文中所說,藝術應表現生活。
任何人都無法脫離自己所處的時代背景,尤其當下社會信息發展速度驚人,人與人之間聯系緊密,但藝術家們又都有各自的認識,自己的生活理想以及生活問題。因而,他們在藝術創作時,就必然受這些因素的影響。就這個系列作品的創作來說,自己本身才是被“借古以開今”最多的人。因為“四君子”相關的藝術作品、生活用品對于社會意識形態能起到多大作用,我們不得而知。當然對于社會來說,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四君子》系列作品,讓其發揮更多的教育作用。或許成效卓著,也或許絲毫沒用。但對于創作這些作品的藝術家來說,是一個不斷升華的過程。
參考文獻:
[1]周積寅.中國畫論輯要[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1985:414.
[2]張彥遠,俞劍華.歷代名畫記[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24.
[3]石濤,劍華.石濤畫語錄[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43.
(作者簡介:史海洋,女,研究生,黑龍江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助講,研究方向:北方花鳥畫研究)(責任編輯 劉冬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