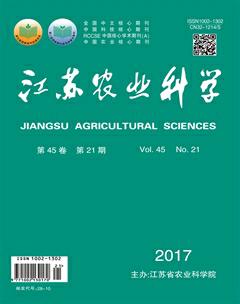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協(xié)同度分析
蔡瑞林 唐焱
摘要:在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進(jìn)程分析基礎(chǔ)上,構(gòu)建兩者協(xié)同推進(jìn)的計(jì)量模型,運(yùn)用面板數(shù)據(jù)測(cè)算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工規(guī)模雖然持續(xù)擴(kuò)大,但出現(xiàn)增幅收窄的趨勢(shì);政府主導(dǎo)著農(nóng)地征地、拆遷安置,推動(dòng)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進(jìn)程,造成不均衡的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開(kāi)發(fā)利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沒(méi)有與市民化形成高效協(xié)同,這種不協(xié)同性不僅體現(xiàn)在區(qū)域之間的協(xié)同度與其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不存在相關(guān)性,而且縱向演變過(guò)程同樣不存在穩(wěn)定的協(xié)同趨勢(shì)。進(jìn)而提出以下5點(diǎn)對(duì)策建議:界定征地的公共利益,明確征地的范圍;適度、可持續(xù)提高農(nóng)民征地補(bǔ)償;完善征地程序和征地糾紛解決機(jī)制;加強(qiáng)城鎮(zhèn)存量建設(shè)用地收益征收管理;縮短建設(shè)用地使用權(quán)租賃期。
關(guān)鍵詞: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土地征用;土地有償使用;協(xié)同度
中圖分類號(hào): F3236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 A
文章編號(hào):1002-1302(2017)21-0337-04
收稿日期:2016-06-05
基金項(xiàng)目:國(guó)家自然科學(xué)基金(編號(hào):71573132)。
作者簡(jiǎn)介:蔡瑞林(1970—),男,江蘇常州人,博士研究生,教授,主要從事土地經(jīng)濟(jì)與政策研究。E-mail:cairuilin@163com。
國(guó)家“十三五”規(guī)劃綱要和新型城鎮(zhèn)化規(guī)劃均提出加快推進(jìn)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的階段性目標(biāo)。中國(guó)人多地少的國(guó)情決定了只有“減少農(nóng)民,才能富裕農(nóng)民”,探討新型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人口與土地的協(xié)同流轉(zhuǎn)、測(cè)算市民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協(xié)同程度,對(duì)于揭示土地城鎮(zhèn)化與人口城鎮(zhèn)化的失衡現(xiàn)象、構(gòu)建和諧人地關(guān)系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1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進(jìn)程
11人口的城鄉(xiāng)流動(dòng)
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加快了市場(chǎng)化改革下的工業(yè)化進(jìn)程,中國(guó)逐步依照市場(chǎng)規(guī)則從國(guó)外引進(jìn)資金、技術(shù)、人才、設(shè)備及管理經(jīng)驗(yàn)等,讓農(nóng)民進(jìn)城參與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建設(shè),逐步改革封堵農(nóng)民進(jìn)城的戶籍制度成為大勢(shì)所趨。但由于農(nóng)民過(guò)多且城鎮(zhèn)就業(yè)崗位有限,加上城市偏向政策既得利益者的固化和排斥,戶籍和其他福利制度的改革相對(duì)滯后,出現(xiàn)了“非城非農(nóng)、亦工亦農(nóng)”的特殊農(nóng)民工群體,進(jìn)城農(nóng)民經(jīng)歷了由排斥歧視到限制進(jìn)城、再到有序引導(dǎo)、直至保護(hù)進(jìn)城農(nóng)民權(quán)益和促進(jìn)融入城鎮(zhèn)的演變1]。為了更好地掌握農(nóng)民工流動(dòng)的基本情況,國(guó)家統(tǒng)計(jì)局于2008年建立了農(nóng)民工監(jiān)測(cè)調(diào)查制度,由國(guó)家統(tǒng)計(jì)局農(nóng)村司組織農(nóng)民工輸出地大規(guī)模抽樣調(diào)研。結(jié)果顯示,全國(guó)農(nóng)民工總量呈現(xiàn)持續(xù)增加趨勢(shì),數(shù)量從2008年的22 542萬(wàn)人上升至2014年的27 395萬(wàn)人,但增速出現(xiàn)回落趨勢(shì);根據(jù)農(nóng)民工戶籍所在鄉(xiāng)(鎮(zhèn))地域不同,農(nóng)民工又分為外出農(nóng)民工和本地農(nóng)民工,這2類農(nóng)民工的數(shù)量同樣呈現(xiàn)持續(xù)遞增趨勢(shì)(表1)。
從輸出地分析2014年農(nóng)民工的區(qū)域分布,東部地區(qū)農(nóng)民工數(shù)量最多,達(dá)10 664萬(wàn)人;其次是中部地區(qū),達(dá)9 446萬(wàn)人;最CM(25]少是西部地區(qū),達(dá)7 285人。盡管農(nóng)民工規(guī)模總量穩(wěn)步遞增,但隨著區(qū)域經(jīng)濟(jì)一體化推進(jìn),特別是城鄉(xiāng)一體化步伐的加快,農(nóng)民工數(shù)量的增速呈明顯放緩的節(jié)奏。
但是,進(jìn)城農(nóng)民面臨社會(huì)身份轉(zhuǎn)變、政治權(quán)利平等、城市公共服務(wù)覆蓋、文化意識(shí)融合等現(xiàn)實(shí)問(wèn)題,必須跨越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文化、政治等多種障礙,才能“進(jìn)得來(lái)、留得下、過(guò)得好”,真正實(shí)現(xiàn)城鎮(zhèn)化;否則進(jìn)城農(nóng)民可能選擇被迫逆城市化流動(dòng)。蔡瑞林等指出,中國(guó)當(dāng)前新出現(xiàn)的人口逆城市化流動(dòng)不同于西方城市化成熟階段的逆城市化,同時(shí)受經(jīng)濟(jì)因素、社會(huì)因素、土地因素、親情因素等綜合影響2]。也就是說(shuō),進(jìn)城農(nóng)民可能因?yàn)殡y以真正市民化而被迫選擇逆城市化流動(dòng),也有可能受上述4種因素主動(dòng)選擇返鄉(xiāng)定居,甚至原有市民也可能會(huì)主動(dòng)選擇“逃離城市”的逆城市化流動(dòng)。
12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的演進(jìn)
由表1可知,盡管農(nóng)民工規(guī)模的遞增速度逐步收窄,但整體規(guī)模還處于遞增狀態(tài),大規(guī)模的農(nóng)民工市民化促進(jìn)了城鎮(zhèn)化水平,加上政府主導(dǎo)下的征地拆遷,大量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進(jìn)城上樓。張玉林在比較中國(guó)與英國(guó)的圈地運(yùn)動(dòng)時(shí)指出,中國(guó)1990年以來(lái)的征地拆遷浪潮,已經(jīng)吞噬了約55569萬(wàn)hm2耕地,產(chǎn)生了約12 7451萬(wàn)失地農(nóng)民3]。無(wú)論是經(jīng)濟(jì)利益驅(qū)使下農(nóng)民的主動(dòng)市民化,還是政府征地拆遷導(dǎo)致的被動(dòng)市民化,均加速了城鎮(zhèn)化進(jìn)程(表2)。
由表2可知,“六五”期間(1981—1985年)、“七五”期間(1986—1990年)、“八五”期間(1991—1995年)等3個(gè)時(shí)期,中國(guó)的城鎮(zhèn)化進(jìn)程整體呈溫和增長(zhǎng)態(tài)勢(shì),年均城鎮(zhèn)化率不到1%。然而,“九五”期間(1996—2000年)直到“十二五”期間(2011—2015年)等4個(gè)時(shí)期,城鎮(zhèn)化進(jìn)程明顯加快。究其原因主要有2個(gè)方面:一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財(cái)權(quán)分配得到根本性轉(zhuǎn)變,誘發(fā)了土地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特別是地方政府主導(dǎo)下土地征用帶來(lái)的拆遷安置大幅蔓延,許多失地農(nóng)民被迫進(jìn)城上樓;二是1996—2015年中國(guó)經(jīng)濟(jì)保持持續(xù)高速增長(zhǎng),雖然2015年GDP增長(zhǎng)率略有下降,為69%,但整體工業(yè)化進(jìn)程明顯加快,東部沿海等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地區(qū)甚至進(jìn)入后工業(yè)化時(shí)代,2015年服務(wù)業(yè)占GDP比重首次超過(guò)50%,吸引了大量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進(jìn)入現(xiàn)代工業(yè)或服務(wù)業(yè)。表2還說(shuō)明中國(guó)的城鎮(zhèn)化進(jìn)程呈現(xiàn)明顯的階段性變化,就目前561%的城鎮(zhèn)化率而言,筆者認(rèn)同簡(jiǎn)新華等的觀點(diǎn),即中國(guó)的城鎮(zhèn)化滯后于國(guó)內(nèi)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也滯后于國(guó)外同等發(fā)展水平國(guó)家或同樣發(fā)展階段的城市化水平,中國(guó)目前的城鎮(zhèn)化推進(jìn)速度基本適中4]。
2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進(jìn)程
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是指政府通過(guò)公權(quán)力強(qiáng)制將農(nóng)用地轉(zhuǎn)為建設(shè)用地使用,即政府通過(guò)土地征收改變了農(nóng)用地的使用性質(zhì)。按照《土地管理法》《征用土地公告辦法》等規(guī)定,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使用須要堅(jiān)持以下幾點(diǎn):第一是為了公共利益需要,政府可以依法征收農(nóng)用地并給予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或農(nóng)民相應(yīng)的征地補(bǔ)償;第二是農(nóng)用地的使用性質(zhì)發(fā)生轉(zhuǎn)變,即農(nóng)民集體所有的農(nóng)用地轉(zhuǎn)變?yōu)榻ㄔO(shè)用地;第三是按照被征收土地的農(nóng)用地用途收益給予補(bǔ)償,主要包括土地補(bǔ)償費(fèi)、安置補(bǔ)償費(fèi)及地上附著物或青苗費(fèi)的補(bǔ)償。分析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征用制度,可以發(fā)現(xiàn)存在以下3個(gè)方面的問(wèn)題:一是征地項(xiàng)目的公共利益界定問(wèn)題。征地公共利益的界定存在廣泛的爭(zhēng)議,雖然侯海軍對(duì)此進(jìn)行了專題研究,認(rèn)為可以從征收后的用途為公眾所需;征收后的新建設(shè)施是否為公共所用;征收行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和要求等3個(gè)基本要素進(jìn)行甄別5],但事實(shí)上土地征用的主體為政府,而政府即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主導(dǎo)的征地項(xiàng)目自然被理解為追求公共利益。進(jìn)一步分析可知,許多項(xiàng)目的公共利益屬性與土地開(kāi)發(fā)者的私人利益屬性交融在一起,特別是伴隨著公私合作制(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項(xiàng)目的推進(jìn),征地的公共利益屬性很難在現(xiàn)實(shí)中得到貫徹執(zhí)行。二是土地使用主體和使用性質(zhì)的轉(zhuǎn)變問(wèn)題。就農(nóng)用地非農(nóng)化而言,雖然法律規(guī)定村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村民委員會(huì)、村民小組、鄉(xiāng)(鎮(zhèn))集體經(jīng)濟(jì)組織行使農(nóng)村集體土地所有權(quán),但村民委員會(huì)是當(dāng)前情景下現(xiàn)實(shí)意義上的集體產(chǎn)權(quán)代理人;同時(shí)新時(shí)期村民委員會(huì)具有“群眾性自治和基層政府代理人”這一“政社合一”的特性6]。當(dāng)前,由于村民委員會(huì)“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定位和農(nóng)村空心化現(xiàn)象的加劇,使得原本脆弱的集體土地所有權(quán)更加虛化,政府順利成章地成為農(nóng)村集體土地使用權(quán)主體的代理人。從土地性質(zhì)轉(zhuǎn)變分析,由于集體土地轉(zhuǎn)變?yōu)閲?guó)有建設(shè)用地,而國(guó)有土地的代理人為各級(jí)政府,使得政府可以較隨意地成為土地征用的操縱者,并將國(guó)有建設(shè)用地使用地出讓給土地開(kāi)發(fā)商。三是土地征用補(bǔ)償歧視問(wèn)題。政府以公共利益為由主導(dǎo)推進(jìn)農(nóng)用地非農(nóng)化,將農(nóng)用地轉(zhuǎn)變成建設(shè)用地進(jìn)而轉(zhuǎn)讓給土地開(kāi)發(fā)商,必然產(chǎn)生土地征用公平補(bǔ)償問(wèn)題,由此引發(fā)“漲價(jià)公私歸屬”爭(zhēng)議。由于土地征用補(bǔ)償以農(nóng)地使用為基準(zhǔn),而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后建設(shè)用地的出讓更多以“招拍掛”的市場(chǎng)價(jià)值為基準(zhǔn),這種價(jià)值衡量的不對(duì)稱使得政府可以操控土地一級(jí)開(kāi)發(fā)市場(chǎng)。為了防止農(nóng)地過(guò)度非農(nóng)化,應(yīng)調(diào)整現(xiàn)有土地補(bǔ)償方式及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后的土地收益分配機(jī)制,明晰土地產(chǎn)權(quán),讓農(nóng)民最大限度地分享土地增值中的收益,過(guò)上更加有保障、有尊嚴(yán)的生活7]。endprint
分析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征地制度,不難發(fā)現(xiàn)現(xiàn)行制度賦予政府強(qiáng)制、低價(jià)的征地權(quán),由此決定土地城鎮(zhèn)化的瘋狂擴(kuò)張。另外,城市建設(shè)用地供給的主要來(lái)源是政府主導(dǎo)下的土地征用(表3)。
由表3可知,城市建設(shè)用地面積從2000年的22 114 km2持續(xù)上升至2014年的49 983 km2,年均增長(zhǎng)率高達(dá)812%,城市新增建設(shè)用地面積得益于城市征用土地面積,2000—2014 年新增城市建設(shè)用地面積達(dá)29 1055 km2,同期城市征用土地面積達(dá)24 04179 km2,征地面積占新增建設(shè)用地面積的826%。可見(jiàn),大規(guī)模的土地征用使得農(nóng)地轉(zhuǎn)變成國(guó)有建設(shè)用地,農(nóng)村土地持續(xù)圈入城市版圖,導(dǎo)致攤大餅式的城市面積高速擴(kuò)張,歷年批準(zhǔn)建設(shè)用地面積中農(nóng)用地轉(zhuǎn)用的占比見(jiàn)圖1。由圖1可知,批準(zhǔn)建設(shè)用地的主要來(lái)源始終是農(nóng)用地轉(zhuǎn)用,政府作為農(nóng)地征收的唯一主體將農(nóng)村集體土地轉(zhuǎn)變?yōu)閲?guó)有建設(shè)用地,加快了土地資源的城鄉(xiāng)重新配置。
3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協(xié)同
31協(xié)同度模型構(gòu)建
德國(guó)物理學(xué)家哈肯的《協(xié)同學(xué)導(dǎo)論》標(biāo)志著協(xié)同論成為自然科學(xué)領(lǐng)域研究系統(tǒng)演化的重要方法,特別是用來(lái)揭示非均衡系統(tǒng)在時(shí)間、空間、功能和結(jié)構(gòu)等方面的自組織過(guò)程8]。在城鎮(zhèn)化進(jìn)程中,市民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協(xié)同涉及最核心的人地關(guān)系系統(tǒng),該系統(tǒng)受戶籍制度、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與升級(jí)、福利制度等多種外部因素影響,必然經(jīng)歷動(dòng)態(tài)的協(xié)同過(guò)程。借鑒殷小菲等關(guān)于江蘇城市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研究成果9],選擇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變化速度代表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的推進(jìn)速度,殷小菲等選擇建設(shè)用地中的耕地占用代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速度,與之不同的是本研究用審批建設(shè)用地中的農(nóng)用地轉(zhuǎn)用占比變化速度代表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進(jìn)程,顯然,農(nóng)用地的范疇涵蓋耕地,更切合研究需要。因此,構(gòu)建如下計(jì)量公式:
Xi=(Ui+1-Ui)Ui;JZ)]JY](1)
Yi=(Ei+1-Ei)Ei。JZ)]JY](2)
式中:Xi表示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變化速度;Yi表示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變化速度;Ui表示i年份(橫向比較時(shí)代表i地區(qū))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Ei表示i年份(橫向比較時(shí)代表i地區(qū))批準(zhǔn)建設(shè)用地總面積中農(nóng)用地的面積占比。
借鑒Engle等的研究成果及協(xié)同度計(jì)量模型10-11],設(shè)計(jì)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之間的協(xié)同發(fā)展模型:
Ci=(Xi+Yi)KF(](X2i+Y2i)KF)]。JZ)]JY](3)
式中:Ci的取值范圍為-1414~1414,協(xié)同度的類型劃分根據(jù)Ci及Xi、Yi的變化(表4)。顯然,當(dāng)Xi>0,Yi<0時(shí),說(shuō)明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速度加快,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速度降低,這種不協(xié)同反映農(nóng)地的節(jié)約集約使用;當(dāng)Xi>0,Yi>0時(shí),則Ci大于0,說(shuō)明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速度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速度均呈現(xiàn)同步增加,Ci指數(shù)的不同說(shuō)明兩者之間呈不同程度的協(xié)同增加。
32協(xié)同度測(cè)算結(jié)果
協(xié)同度測(cè)算過(guò)程有3個(gè)步驟:首先,收集全國(guó)31個(gè)省(市、區(qū))1999—2015年的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批準(zhǔn)建設(shè)用地面積、批準(zhǔn)建設(shè)用中農(nóng)用地面積的原始數(shù)據(jù);其次,用公式(1)、公式(2)計(jì)算相應(yīng)年份(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變化速度、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變化速度;最后,用公式(3)進(jìn)行協(xié)同度CM(25]的測(cè)算。2014年全國(guó)各地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與農(nóng)地非其中,2011年西藏自治區(qū)的批準(zhǔn)建設(shè)用地面積、批準(zhǔn)建設(shè)用中農(nóng)用地面積數(shù)據(jù)空缺,采用2010、2012年平均數(shù)補(bǔ)缺的方法替代。
農(nóng)化的協(xié)同指數(shù)見(jiàn)表5。由表5可知,2014年全國(guó)不同區(qū)域之間的協(xié)同度與地區(qū)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不存在相關(guān)性。其中,吉林、上海、江蘇、浙江、河南、湖北、湖南、四川、陜西等9個(gè)省(市)的協(xié)同度指數(shù)為負(fù)值,這些地區(qū)的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均在提高,但審批建設(shè)用地農(nóng)用地面積占比卻在下降,說(shuō)明這些地區(qū)的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速度低于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速度,體現(xiàn)出這些地區(qū)農(nóng)地的集約開(kāi)發(fā)利用。西藏自治區(qū)的城鎮(zhèn)化水平提高86%,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速度下降31%,協(xié)同度指數(shù)位于基本調(diào)和區(qū)間,說(shuō)明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速度滯后于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速度。北京、河北、山西、遼寧、安徽、福建、廣東、青海、寧夏等9個(gè)省(市、區(qū))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和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呈同方向增加,協(xié)同度指數(shù)位于基本協(xié)同區(qū)間。天津、黑龍江、內(nèi)蒙古、山東、廣西、海南、重慶、貴州、云南、甘肅、新疆等11個(gè)省(市、區(qū))的協(xié)同度指數(shù)位于較協(xié)同區(qū)間,說(shuō)明這些地區(qū)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遞增速度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速度較協(xié)同,而江西省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實(shí)現(xiàn)協(xié)同的遞增。整體而言,Xi=0019,Yi=-0001,說(shuō)明2013—2014年中國(guó)整體城鎮(zhèn)化水平環(huán)比上升19%,同期審批建設(shè)用中農(nóng)用地占用的比例下降了1%,說(shuō)明在城鎮(zhèn)化小幅增加的同時(shí)基本實(shí)現(xiàn)了農(nóng)用的集約節(jié)約利用。
縱向?qū)Ρ?000—2014年全國(guó)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協(xié)同情況可以看出(圖2),13年間協(xié)同度指數(shù)最大值為2008年的1406,最小值為2014年的-0980,整個(gè)期間協(xié)同度指數(shù)圍繞均值05上下振蕩,且振幅沒(méi)有明顯的放大或收窄趨勢(shì)。說(shuō)明整個(gè)期間全國(guó)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演變還沒(méi)有形成明顯的趨勢(shì),這是由于全國(guó)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農(nóng)地資源稟賦、城市建設(shè)用地需求存在較大的差異,雖然北京、上海、天津等市當(dāng)前的常住人口城鎮(zhèn)化率均超過(guò)了80%,但廣西、安徽、湖南、四川、貴州等省(區(qū))2013年的城鎮(zhèn)化水平還不到50%,西藏自治區(qū)的城鎮(zhèn)化水平甚至還不到30%。新型城鎮(zhèn)化整體上要從土地城鎮(zhèn)化向人的城鎮(zhèn)化轉(zhuǎn)型發(fā)展,但土地城鎮(zhèn)化的慣性和地區(qū)之間的客觀差異,使得全國(guó)區(qū)域尚沒(méi)有形成明顯、穩(wěn)定的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市民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協(xié)同趨勢(shì)。
4結(jié)論與對(duì)策建議
41結(jié)論
改革開(kāi)放之后的城鄉(xiāng)人口流動(dòng)政策總體逐漸解除了制度性藩籬,鼓勵(lì)農(nóng)村人口向城鎮(zhèn)遷徙定居轉(zhuǎn)移,加上農(nóng)地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yíng)和二三產(chǎn)業(yè)比重的持續(xù)提高,推進(jìn)了市民化和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進(jìn)程。就農(nóng)民工群體而言,盡管增幅出現(xiàn)收窄的趨勢(shì),但總量仍在持續(xù)增長(zhǎng)。政府主導(dǎo)的征地拆遷一方面使得大量農(nóng)業(yè)轉(zhuǎn)移人口進(jìn)城上樓,另一方面使得農(nóng)地持續(xù)圈入城市版圖,導(dǎo)致城區(qū)面積攤大餅式地?zé)o序擴(kuò)張。但無(wú)論是農(nóng)民工的自主市民化,還是政府主導(dǎo)下的拆遷安置式的政策性被動(dòng)市民化,市民化進(jìn)程并沒(méi)有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進(jìn)程形成高效協(xié)同,這種不協(xié)同不僅體現(xiàn)在區(qū)域之間的協(xié)同度與地區(qū)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不存在相關(guān)性,而且體現(xiàn)在縱向演變過(guò)程中同樣不存在穩(wěn)定的協(xié)同性。endprint
42對(duì)策建議
421界定征地的公共利益,明確征地的范圍
首先,須要強(qiáng)化農(nóng)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quán),允許農(nóng)村土地所有者與開(kāi)發(fā)商進(jìn)行直接談判,擴(kuò)大農(nóng)民在征地范圍與規(guī)模、征地補(bǔ)償與安置、征地生態(tài)與環(huán)境等事項(xiàng)中的話語(yǔ)權(quán)。其次,須要設(shè)置城市擴(kuò)張邊界,通過(guò)城鄉(xiāng)土地合理規(guī)劃、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供給機(jī)制、加強(qiáng)黨政領(lǐng)導(dǎo)干部城鄉(xiāng)規(guī)劃管控審計(jì)等途徑治理征地范圍限定政策的失靈,把政府征用農(nóng)地的特權(quán)限制在制度的籠子里。最后,還要縮短征地年限,目前的土地出讓金實(shí)質(zhì)上是土地所有權(quán)出租的一次性租金,本屆政府可以在政策框架內(nèi)足額使用,而不是按照年限分?jǐn)偸褂米饨穑纯梢圆活櫦昂笕握?cái)政收入的可持續(xù)性供給,使得本屆政府熱衷擴(kuò)大征地范圍。
422適度、可持續(xù)提高農(nóng)民征地補(bǔ)償
第一,要建立補(bǔ)償標(biāo)準(zhǔn)的調(diào)整機(jī)制,就調(diào)整頻率、調(diào)整幅度、糾紛解決、監(jiān)督實(shí)施等問(wèn)題逐一明確,特別要突出農(nóng)村集體土地所有者的主體地位,享有部分級(jí)差地租Ⅱ。第二,要兼顧政府農(nóng)地開(kāi)發(fā)和財(cái)政收支平衡,結(jié)合地方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升級(jí),控制市民化和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進(jìn)程,高度重視政府債務(wù)危機(jī)化解和地方經(jīng)濟(jì)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不能盲目加快城鎮(zhèn)化進(jìn)程。第三,要建立完善多元補(bǔ)償安置機(jī)制,要充分考慮進(jìn)城農(nóng)民的職業(yè)發(fā)展和長(zhǎng)遠(yuǎn)保障,鼓勵(lì)因地制宜采取就業(yè)安置,預(yù)留物業(yè)、股份、收益返還等方式滿足進(jìn)城農(nóng)民的長(zhǎng)期保障。第四,要加強(qiáng)農(nóng)村集體土地增值收益資金管理,強(qiáng)化農(nóng)村集體土地資產(chǎn)、土地增值收益財(cái)務(wù)監(jiān)管,保證集體土地資產(chǎn)保值增值,具體而言,須要建立農(nóng)村集體資源、資產(chǎn)的配套管理制度,探索征地補(bǔ)償資金預(yù)留制度。
423完善征地程序和征地糾紛解決機(jī)制
首先,須要改變政府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進(jìn)程中“管經(jīng)合一”的特權(quán),通過(guò)強(qiáng)化農(nóng)村集體所有權(quán)主體地位、擴(kuò)大被征地農(nóng)民應(yīng)有的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談判權(quán)與監(jiān)督權(quán),約束和規(guī)范政府的征地特權(quán)。其次,在征地過(guò)程中須要建立必要的征地補(bǔ)償安置談判機(jī)制、征地項(xiàng)目公示制度、征地項(xiàng)目評(píng)估制度,規(guī)范征地項(xiàng)目的全程推進(jìn)。最后,要完善相關(guān)的制度設(shè)計(jì),健全矛盾協(xié)調(diào)化解機(jī)制,健全行政復(fù)議、行政訴訟制度,維護(hù)農(nóng)民合理的土地權(quán)益抗?fàn)幮袨椤m氁a(bǔ)充的是,無(wú)論是完善征地程序還是建立征地糾紛解決機(jī)制,均要突出農(nóng)村集體所有權(quán)的主體地位,目前可行的辦法明確到底誰(shuí)是農(nóng)村集體所有權(quán)的代理人,并讓代理人、農(nóng)民代表參與征地程序的制定過(guò)程,進(jìn)入征地糾紛解決機(jī)構(gòu)。
424加強(qiáng)城鎮(zhèn)存量建設(shè)用地收益征收管理
由于機(jī)構(gòu)合并、用途更改、投資主體變化等眾多原因,原有基礎(chǔ)設(shè)施和各類社會(huì)事業(yè)的存量建設(shè)用地使用情況可能發(fā)生變化,須要加強(qiáng)城鎮(zhèn)存量建設(shè)用地收益征收管理,岳雋以廣東省深圳市為例,研究了不同二次開(kāi)發(fā)模式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方面的主要差異,從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的視角,提出實(shí)施利益總量調(diào)控、統(tǒng)一拆遷補(bǔ)償指導(dǎo)標(biāo)準(zhǔn)、統(tǒng)籌平衡調(diào)控手段的三大基本策略12],這對(duì)深圳、上海等特大城市,對(duì)江蘇、浙江等建設(shè)用地指標(biāo)稀缺的地區(qū)具有積極意義。下一步改革中,對(duì)于使用國(guó)有劃撥土地從事經(jīng)營(yíng)性行為的主體,可以通過(guò)補(bǔ)收年租金的方式對(duì)存量建設(shè)用地征收土地使用租金;對(duì)于用途性質(zhì)變更的, 政府應(yīng)明確存量建設(shè)用地使用主體應(yīng)繳土地租金的義
務(wù),確保國(guó)有資產(chǎn)的保值增值。
425縮短建設(shè)用地使用權(quán)租賃期
政府通過(guò)低價(jià)征收、高價(jià)出讓的方式獲得土地出讓金,在現(xiàn)行土地有償制度下,土地出讓金實(shí)質(zhì)是國(guó)有建設(shè)用地40~70年的土地使用租金,這種制度安排存在2個(gè)顯著的弊端:一是刺激了本屆政府土地城鎮(zhèn)化的熱情,本屆政府更多關(guān)注任期內(nèi)的政績(jī)和土地出讓收入,直接后果就是任期政府如同開(kāi)發(fā)商那樣采取“撈一把就走”的短期行為;二是刺激了開(kāi)發(fā)商倒賣土地的投機(jī)行為,開(kāi)發(fā)商往往采用延期開(kāi)發(fā)、等待漲價(jià)、伺機(jī)轉(zhuǎn)售的方式倒賣土地使用權(quán)獲得土地增值收益,丟掉了當(dāng)初獲得建設(shè)用地開(kāi)發(fā)的初衷。在下一步改革中,須要加入對(duì)建設(shè)用地使用權(quán)獲得者土地實(shí)質(zhì)性開(kāi)發(fā)能力的評(píng)估,采用先租賃后出讓的方式有償使用建設(shè)用地;對(duì)于消極開(kāi)發(fā)、伺機(jī)倒賣等土地交易投機(jī)行為,須要通過(guò)限定期限開(kāi)發(fā)等政策加以控制。
參考文獻(xiàn):
1]ZK(#]楊黎源 權(quán)利回歸:改革開(kāi)放以來(lái)農(nóng)民進(jìn)城就業(yè)政策嬗變及啟示J] 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xué)報(bào),2013(4):106-111
2]蔡瑞林,陳萬(wàn)明,王全領(lǐng) 農(nóng)民工逆城市化的驅(qū)動(dòng)因素分析J] 經(jīng)濟(jì)管理,2015(8):161-170
3]張玉林 大清場(chǎng):中國(guó)的圈地運(yùn)動(dòng)及其與英國(guó)的比較J] 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5,32(1):19-45
4]簡(jiǎn)新華,黃錕 中國(guó)城鎮(zhèn)化水平和速度與實(shí)證分析與前景預(yù)測(cè)J] 經(jīng)濟(jì)研究,2010(3):28-39HJ175mm]
5]侯海軍 城市化進(jìn)程中房屋征收補(bǔ)償?shù)摹肮怖妗苯缍↗] 南京社會(huì)科學(xué),2014(5):85-90,98
6]蔡瑞林,陳萬(wàn)明,葉琳 從農(nóng)村土地確權(quán)看新時(shí)期村委會(huì)的地位和功能J] 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2015(4):90-95
7]鐘國(guó)輝,郭忠興 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經(jīng)濟(jì)機(jī)制分析J] 江蘇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4,42(3):368-371
8]Haken HVision of synergeitcsM] London:Elsevier Science Ltd,1997
9]殷小菲,劉友兆 城市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協(xié)調(diào)度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 西北人口,2015(5):26-30,36
10]ZK(#]Engle R F,Granger C W JCo-integration and error correction:representation,estimation,and testingJ] Econometrica,1987,55(2):251-276
11]Liu Y,Lu S,Chen YSpatio-temporal change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China and its driving factor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13,32(32):320-330
12]岳雋 深圳原農(nóng)村土地二次開(kāi)發(fā)模式統(tǒng)籌研究——基于土地增值收益合理分配的視角J] 地域研究與開(kāi)發(fā),2015(5):153-156,176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