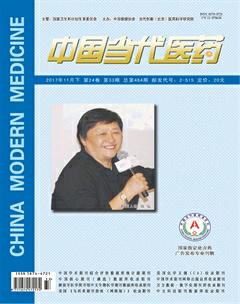建立精神疾病全程治療和康復模式
潘鋒
精神衛生問題既是重大公共衛生問題,也是較為突出的社會問題,已經成為影響人類健康及社會發展最為突出的問題之一。在10月10日世界精神衛生日到來前夕,2017年9月24日,由白求恩公益基金會發起的“尚善精神-白求恩·全國精神衛生高峰會”在北京舉行。國家精神衛生項目辦公室副主任、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馬弘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高復發是當前精神分裂癥等精神疾病治療的主要難題和挑戰,聯動醫院和社區力量,共同推進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治療和康復管理十分重要。”
治療率低,復發率高
馬弘教授從1983年自愿開始從事精神衛生的醫療和科研工作,她不僅對這個職業很感興趣,而且很富有同情心。馬弘教授說,只有非常有同情心的人才能做好精神科醫生。
據馬弘教授介紹,目前我國治療精神疾病主要是在兩個場所,一個是在醫院,一個是在居家社區。《2016中國衛生和計生統計年鑒》顯示,2004年全國精神病院平均住院日50天,門診人次1122.5萬人次;2014年全國精神病院平均住院日48.5天,出院185萬人次,門診人次2970.7萬人次;2015年全國精神病院平均住院日49.8天,全國醫療機構精神科出院201.9萬人次。由此可見,1年當中,除了住院的50天以外,患者315天都是在家里治療的。但住院與居家最大的不同是,如果患者住在醫院,每天24小時都有醫生護士的治療和看護,治療效果肯定是好的;如果患者出院回家、回社區,那么只有社區繼續為其提供良好的精神衛生服務,才能保證患者出院后的繼續治療,保持好的療效。
但實際情況卻不容樂觀。馬弘教授引用的《亞太地區精神衛生綜合評價指數研究報告》的數據展示了一個真實的情況。此《報告》由經濟學人智庫完成。2014年經濟學人智庫對歐洲30多個國家進行了精神衛生領域的調研和評估,發布了歐洲精神衛生整合指數。2016年3~5月,經濟學人智庫對亞太15個國家和地區在精神疾病治療和社區整合方面的情況做了一次評估。評估共包括4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環境,即精神疾病患者過上正常生活所需的環境;二是治療的可及性,即精神疾病患者獲得所需的醫療幫助和服務的程度;三是機會,指向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的就業相關機會;四是管理,即為消除歧視所做的努力。
研究數據顯示,亞太地區精神疾病接受治療的患者明顯少于發達國家,15個接受調查的國家和地區都存在這一問題。與全世界相比,發達國家約有50%的患者沒有接受治療,而亞太地區卻有高達90%的患者沒有接受治療,只有10%的患者得到了治療。馬弘教授特別強調說,由于公眾認知和社會歧視,在中國,精神疾病診斷和治療的比例還是比較低的,只有8%的患者得到了治療,92%的患者從未接受過治療。由于未接受治療或中斷治療,導致精神疾病的復發率非常高,平均復發時間是6個月,約1/3的患者出院后半年復發,40.8%的患者在出院1年后復發,這些復發的患者又要重新入院治療,如同“旋轉門”一樣,一個門出去一個門又回來,在醫院里取得的療效幾乎喪失殆盡。
馬弘教授分析道,精神疾病容易復發的最主要原因是患者在家里或社區不能堅持服藥,不愿意服藥,因為315天都在家里,就需要家屬來監督服藥,但家屬監護能力弱是不爭的事實;另外就是患者以各種理由和各種方式減藥或藏藥,患者會認為“我沒病,我覺得藥有副作用,我的癥狀告訴我不應該服藥”等;或者患者認知功能減退,記不住服藥時間等,這些都成為患者拒絕服藥的理由。停藥的結果就是病情的復發,患者反復不斷地住院,給家庭和社會帶來諸多問題。
馬弘教授以精神分裂癥為例介紹說,據WHO估計,目前全球約有4.5億精神疾病患者,其中精神分裂癥患者的人數約2100萬。精神分裂癥如果反復發作或不斷惡化,患者病情就會不斷加重并最終喪失社會功能。流行病學調查顯示,精神分裂癥致殘率高達62.2%。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自殺危險是無精神分裂癥者的23.8倍,至少10%的患者最終死于自殺。此外,多數精神分裂癥患者身體狀況不佳,平均壽命縮短,遭受意外傷害的概率也高于常人;精神分裂癥患者中,男性比一般人群的死亡時間要早20年,女性早15年。
應初步建立社區管理和治療模式
馬弘教授強調,精神疾病的治療不僅僅在醫院,同樣在社區。精神疾病的全程治療和康復模式主要是指,要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一個連續的、全面的醫療服務,服務場所不僅在醫院,更重要的還在社區。
但馬弘教授認為,目前多數醫院的精神科在治理觀念上還是偏重于醫院治療,不太關注社區治療,“重醫院輕社區”現象還比較普遍。如果這一觀念不能改變,僅僅依靠醫院而不樹立醫院和社區一體化的治療和管理理念,就會出現患者住院期間療效很好,病歷中的預后分析千篇一律,基本是“本次住院預期療效較好,但遠期療效不佳”的現象。所以,患者出院后治療效果直線下降其實醫生是知道的;而患者反復住院,不僅治療的自信心越來越小,生命和健康也會浪費在這種無休止的“旋轉”中。所以,精神科臨床醫生不僅要對住院患者負責,也要為社區患者提供同樣的醫療服務,這也是每個精神科醫生應該做到的。
近年來,為促進和提高全球精神衛生管理水平,國際社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世界衛生組織的西太平洋區域辦事處2015年發布了詳細日程表和明確目標,旨在落實世界衛生組織的2013~2020 年全球精神健康行動方案。2011年起,東盟成立了一個多政府的精神健康行動小組,旨在鼓勵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更好的醫療和社會心理服務。亞太經合組織也發布了2014~2020 年健康亞太精神健康促進路線圖,并開始了與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旨在進一步促進全球精神衛生健康的發展。多個亞太國家出臺精神衛生的立法和相關政策:印度2014年制定了首項精神衛生政策;日本2009年和2013年將精神疾病列為重大疾病;新加坡2012年制定了社區精神衛生主方案,并正在醞釀第三階段的改革,聚焦人口精神健康;韓國2016-2020 年的精神衛生計劃覆蓋了100多個具體實施項目,旨在為嚴重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更好的醫療和社會服務協調工作。endprint
近20年來,中國精神衛生工作也得到了高度重視。1999年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布倫特蘭博士訪問中國,2001年召開第三次全國精神衛生工作會議,2004年啟動“中央補助地方嚴重精神障礙管理治療項目(因為啟動首年中央財政撥出686萬元培訓資金,該項目又稱‘686項目)”,支持開展社區精神衛生服務。在2009年啟動的我國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中,納入了嚴重精神障礙的社區隨訪管理。2013年5月1日,《中國精神衛生法》開始實施。為進一步貫徹落實《精神衛生法》,2015年國家衛生計生委、中央綜治辦、公安部、民政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中國殘聯6個部門聯合啟動了“精神衛生綜合管理試點”項目,我國精神衛生工作再上新臺階。
馬弘教授以“686 項目”為例介紹說,這一項目是原衛生部主導的嚴重精神障礙醫院社區一體化服務項目,執行辦公室設在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項目的目標是“打破醫院壁壘,將治療擴展到社區”。該項目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我國社區精神衛生服務現狀。2004年社區精神健康治療在中國還不存在,所有治療都由數百家精神專科醫院承擔。該項目從2005年的60個試點開始,到2014年年底已經覆蓋了中國87%的行政區,最終將覆蓋全國。這期間,該項目共登記了430萬例嚴重精神疾病患者。到2014 年年底,已為315萬例患者提供了以社區為中心的精神衛生管理和服務。
馬弘教授說,“686項目”的成功源自多種因素,如政府的資金支持,包括按需分配的治療費用資金;政府和部分國際專家的支持以及根據中國傳統文化因地制宜地采納國際最佳實踐等,最重要的是以中國精神科醫師為主的專家組和政府部門的緊密配合。此項目努力建設了以患者為中心、以康復為目標的治療由社區診所的多學科團隊負責管理。這些團隊包括醫生和護士,還包括社工、病例管理人員、當地警方以及家庭和患者代表。每家社區衛生中心或村醫室還會受到臨近精神病醫院的專家支持,患者可以在診所和醫院之間按需轉院。近年來,北京、武漢、上海、深圳和杭州等地已積極嘗試社區康復模式,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績。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精神疾病社區治療方面開展得比較早,1995年在全國第一個開展了心理衛生進社區項目,在2000年實現了全覆蓋,覆蓋到了所有社區健康服務中心。深圳市全市精神科只有700多張床位,以700張病床的規模承擔全市服務1800萬人口的精神衛生服務任務,靠的就是搞好了社區精神衛生服務工作。
必須培訓足夠的專業人員
馬弘教授說,目前我國醫院社區一體化精神衛生服務體系經過十多年的建設,已經基本覆蓋全國,“686項目”的收獲和經驗是:如果想創造社區精神衛生的相關服務,必須培訓專業人員。
馬弘教授認為,當前,醫療資源分布不均,基層社區康復體系不完備,重院內治療、輕社區治療的態勢正在有所改變,但人力資源不足仍是制約社區精神衛生事業發展的一大重要因素,并且這一情況在世界上多個國家都存在。精神衛生服務機構少,專業人員數量短缺,服務資源供需存在很大的缺口,已經成為制約各國社區精神衛生發展的主要障礙。據《亞太地區精神衛生綜合評價指數研究報告》披露,精神科醫生人數過少導致患者治療的困難和不便。如香港大多數精神病醫生是私人醫生,首次約診等待時間需要三年后;不僅如此,每次約診也只有 5-10 分鐘;而且,香港的精神衛生綜合社區中心待處理病例堆積如山,工作人員疲憊不堪。日本雖然擁有較高的人均精神科醫生數量(每10萬人有20.1 名醫生),但門診也經常只能持續10分鐘。泰國的精神病醫生數量還不到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中高收入國家醫生數量的一半,而馬來西亞則大約只是四分之一。泰國和馬來西亞的心理學家和職業理療師更加稀缺,導致以團隊為基礎的精神護理幾乎無法實現。中國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我們現有精神科醫師2萬多名,平均每10萬人僅有1.49名精神科醫師(全球中高收入水平國家平均2.03名/10萬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級和地市級城市。由于精神科醫生的數量嚴重不足,社區精神衛生服務顯得力不從心。
馬弘教授說,中國的醫療服務體系從國家到社區共有六個層級,越接近基層,實踐人員從培訓和教育中接收的信息數量就越少,最基層所接收的知識可能寥寥無幾。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政府正采取各種方法解決該問題,例如,向每個參與社區精神健康服務的工作人員發放一本包含必要核心信息的手冊等。“686項目”采用種子培訓師策略,以期能迅速擴大知識普及速度,培訓對象也包括臨床醫生。項目的培訓方式使其成功打造了一支隊伍,能夠為數百萬患者提供有效的、以社區為中心的護理,到2014年,已經覆蓋了中國所有精神專科醫生的 86%,以及全國精神健康護士人數的69%。他們所接受的培訓內容不僅有社區精神衛生基礎,還包括病例管理、如何編寫并監督個人治療方案、如何與多功能團隊合作,以及如何與社區建立連接;培訓數量最多的是社區的非專業人員,大多數是當地農村和社區委員會成員。他們參與項目的主要方式是參與精神健康倡導活動,引導潛在患者接受診斷。2005~2014年間受培訓人員中還包括5%左右的社區民警,旨在幫助他們在處理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的病例時進行危機干預。這些不同行業的個人是廣義范圍上的臨床病例管理的貢獻者,并且在資源不足地區還介入基層治療團隊的工作。
提高患者服藥依從性
馬弘教授認為,導致精神疾病復發的一個重要因素與患者服藥的依從性有關,如首次發作的精神分裂癥患者中,75%可以達到臨床治愈,但反復發作或不斷惡化的比率較高,是否進行系統抗精神病藥治療是關鍵;但目前常用的口服抗精神分裂癥藥物治療方案依從性普遍不佳。研究顯示,超過一半的患者出院30天內就會改變醫生的處方,甚至自行停藥,74%的患者在18個月內會中斷口服藥治療,所以口服藥物很難確保患者完全遵照醫囑持續治療。
馬弘教授說,高復發是精神分裂癥治療的主要難題和挑戰,服藥依從性低是復發的主要原因,因此,患者接受全病程、系統性的治療至關重要。提高精神分裂癥患者依從性的重要策略之一是使用長效針劑。長效針劑注射后,藥物從注射部位緩慢釋放,從而可以一次注射便保持長時間相對穩定的血藥濃度水平。長效針劑抗精神病藥與口服藥物相比具有多重優勢:包括提高患者的依從性,避免反復提醒患者用藥,更容易安全地實現最低有效劑量原則(逐步降低劑量),避免胃腸吸收等問題;不存在肝臟首過代謝效應,降低意外或故意的過量服藥風險等。在提升患者治療依從性方面,長效針劑抗精神病藥物具有重要作用。研究顯示,長效針劑可以顯著改善精神分裂癥陽性癥狀及降低復發率。因為使用方便,患者好管理,全球社區長效針劑的使用比例達到20%~40%,此前由于價格等方面的因素,中國的使用率只有1%。
馬弘教授最后表示,當前,我國需要進一步提升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規范化治療水平,提高疾病的治療率,包括長效針劑在內的方便社區使用的治療藥物,以及醫療機構對社區治療的主動指導,這將保持出院患者的療效,降低復發率、降低疾病負擔,幫助患者適應和回歸社會。
專家簡介
馬弘,女,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主任醫師,研究生導師,教授。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副主任,國家衛生計生委疾病預防控制專家、國家衛生計生委應急辦專家,國家精神衛生項目辦公室副主任及中國醫師協會首任總干事(2006-2016年)、中國醫師協會副會長(2008-2017年),全國衛生計生先進工作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