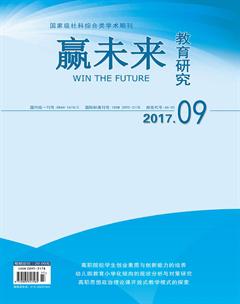紳權之基本理解:概念、關系與意義
摘要:紳權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曾經在中國社會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紳權作為一種紳士對地方的控制權,與國家權力有著緊密的聯系:明清時期紳權既是國家權力的延伸也是鄉村社會防御國家權力的屏障;但到了清末民初,紳權的愈發膨脹,統治者不能再予以放任而開始打壓,紳權日漸衰微最終消亡。同時,紳權的意義重大,它不僅促進了中央集權的進一步強化,還由此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家族關系,并且紳權的主體——紳士還起到了連接中央與基層地方的作用。
關鍵詞:紳權,國家權力,影響
一、何為紳權
(一)士紳階層的產生
在幾百年前的中國,基于當時的社會、人文環境,中國的傳統社會形成了二元社會控制結構,[1]即國家的管理一方面要依靠官僚、政府的治理,另一方面又要依靠當時一些有文化有威望的人所形成的地方勢力來進行治理。這些地方勢力在明清時便發展為我們紳士。他們非官而近官,非民而近民,在中國社會和歷史的舞臺上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那么這些非官非民的紳士是如何登上政治管理的舞臺呢?
1、科舉制度為紳士的產生奠定了基礎
隋煬帝開創的科舉制度大大削弱了當時的貴族力量,一些通過科舉考試獲得頭銜的人逐漸形成了一個穩定的社會團體——士紳階層。到了明朝,皇帝更加注重學校在教育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有意建構出一種由學校通往科舉及仕途的道路。[2]明朝的舉人可以終生享受舉人身份,如果不能為官,回到家鄉后,仍然可以享受舉人身份多帶來許多權利。這便為他們擁有權威、控制地方埋下了伏筆。由于明代統治者對舉人控制嚴密,再加上仕途艱難,許多舉人回鄉,在類似的經歷背景之下,他們漸漸抱團形成了紳士階層。
2、鄉村權力真空與士紳管理地方社會
“國權不下縣,縣下惟宗族,倫理造鄉紳。”[3]馬克斯?韋伯認為:“正式的皇家行政,事實上只限于市區和市轄區的行政。一旦出了城墻,皇家行政的權威就一落千丈,無所作為了。”[4]也就是說,國家權力在農村地方幾乎無法施行和貫徹。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建立了中央集權君主專制制度,這種制度將對國家的管理權統一收歸回國家,但它仍存在著不足之處——對基層社會的統轄力較弱。
3、紳士階層具有資源優勢
政治上,紳士享有政府給予他們諸如自由見官的特權,還在法律上享有與平民截然不同的優待,[5]他們憑借著自身的身份,加之又與科舉同榜或為師生或為同年的關系,在鄉里又可為同鄉關系,紳士可以對鄉民實行經濟管制,有的甚至可以控制地方官員。經濟上,由于擁有政治資本,而“在農業社會,用政治權力獲取財富比用財富去獲取權力來得更容易”,[6]所以對財富的占有具有絕對優勢。同時,紳士大都是具有一定聲望的人,人們總是會對有聲望的人產生信賴和尊從心理,加之紳士的樂施好善,和睦鄉黨,讓普通百姓更愿意服從他們。
總之,在科舉制度的奠定下,由于國家權力難以滲透到基層社會、紳士階層具有資源優勢,地方百姓又需要紳士,紳權得以登上了政治管理的舞臺。
(二)士紳與紳權
有人認為紳士是代表廣大鄉民百姓說話的,以維護人民利益為己任的組織,這樣說來,紳權可以算作是中國歷史上的代議制,民權即紳權;還有人認為紳權是皇權的延長,紳士與官僚一樣,表面為人民服務,實則都是剝削人民的存在。
1、紳權代表民權
紳士與他所在地的百姓同為一鄉,他們通常與百姓有著共同的利益,一般來說他們樂意充當鄉民們的代言人,盡力維護本鄉的利益,“一個鄉紳不會無情地剝削他的同鄉,相反,他經常要盡最大的努力為當地群眾說話”。
2、紳權是皇權的延伸
在傳統社會中,紳權和中國古代的其他權利一樣,也是從與皇權共存到共治,到最后被收服。在紳權與皇權共存共治的這段過程中,由于紳權的主體——紳士,以特定地區為范圍,以官、民之間的社會空間為運動場所,形成了一種具有權勢的地方社會控制力量,[7]他們憑借著絕對的聲望掌握了對基層社會的控制權。并且,土地是一名紳士所必備的物質基礎,但是土地又是掌握在君主手中的,故而紳權大都與皇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由此可以看做紳權是皇權的延伸或是變形,它們的根本目的都是在維護社會穩定、平穩運行的前提下,通過一些緩和階層矛盾的做法,來為自己獲得最大的利益。
綜上所述,紳權是以維護百姓利益為外衣,為著自身謀取利益為本質而存在的事物。
二、紳權與國家權力的關系
(一)明清紳權與國家權力
紳權作為一種紳士對基層地方的控制權,嚴格來說,是對中央集權制度的一種沖擊,毋庸置疑的,紳權就與國家權力產生了種種聯系,他們之間的內在聯系,即鄉紳之治是國家權力在鄉村治理中的延伸,另一方面,鄉紳之治也是鄉村社會防御國家權力的屏障。[8]
按理說統治者不應允許其他限制其權力的權力的存在,但是皇權無法深入中國的每一寸土地,因此在“天高皇帝遠”的農村,紳士階層充當了地方的實際控制者。既然無法消滅,那么統治者也就容忍了這種現象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皇權作出讓步的真正原因在于鄉紳之治的目的是正當的,即是協助而不是背離皇權——鄉紳之治是國家權力在鄉村治理中的延伸。[9]
要維持一個具有強控制力的行政系統,不僅成本高昂,同時也沒有必要,因為政府對重要的地方會重點控制,但是鄉村主要是生產和治安問題。統治者只需要保證他整個政權的穩定,而不需要事無巨細的管理。因此統治者在基層安排了州縣官承擔管理中國基層社會事務的責任。
中國封建社會,保證皇權安定和賦稅征收是基層官僚最關心的事。為了穩定治安,從宋朝開始施行保甲制度,由保長負責保甲內的安定,同時施行里甲制來保證賦稅征收。雖然保長和甲長承擔著履行國家事務的職責,但是鄉村穩定和賦稅征收多靠鄉紳階層得以實現。這也就是鄉紳之治是國家權力在鄉村治理中的延伸的體現。
在明代,鄉紳階層擁有特權,逐漸成為農村社會真正的領導者,給皇權帶來了一定威脅,因此清代統治者取消了鄉紳在保甲制度中的特權。但是統治者一心想削弱鄉紳在農村的勢力,忽視了鄉紳難以動搖的權威。鄉紳實際上掌握了選任保長的權力,可以說,鄉紳是鄉村的潛在領袖。[10]因此紳士階層是封建官僚的特殊組成部分,是鄉紳之治是國家權力在鄉村治理中的延伸的體現。
在統治者接受了紳權存在的情況下,紳士階層實則是在協助統治者管理他們難以干預的農村,紳權也無意威脅皇權,就這樣,紳權與皇權共存共生。
(二)清末民初紳權與國家權力
太平天國運動后,清末政府推行“地方自治”,紳權變得組織化。在地方自治的制度中,形成了一些具有公共權力性質的組織機構,例如州縣、城鎮鄉自治機構、地方保衛機構。這些機構的首領正是各地紳士,警務等區鄉行政機構、社會團體組織的領導人員都有士紳階層擔任。可見,士紳滲透在地方自治的方方面面。
紳士階層的組織化讓紳士可以更好貫徹自己的治理理念,就這樣紳權逐漸“膨脹”:清末民初,士紳甚至可以“把持財政,抵抗稅捐,干預訴訟,妨礙行政”,“私設法庭,非刑考訊”,“私受詞訟,濫用刑罰”,[11]并且自治機構大都有自己的武裝,也就是說士紳擁有武裝,本該代表民權的士紳成了一個“小政府”。同時,擔任著自治機構領導人員的士紳們抱團形成了“團紳”,他們可以負責自治機構的選舉、負責轄區內的治安、財政。有的自治機構的領導人不是士紳,但是士紳可以憑借自己的權威決定這些機構的大小事務。
紳權“膨脹”后,政府打壓紳權的行動開始了。清統治者頒布“太學臥碑刻文視集群結社為厲禁”的命令;袁世凱下令各地停辦自治會;國民黨開始“打倒土豪劣紳”……并且紳民間矛盾凸起,士紳階層腐敗等問題,紳權逐漸衰落,最終消亡了。
三、紳權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
首先,紳權促進了中央集權的進一步強化。在古代中國,中央集權主要受到兩種權力——官僚階層和地方勢力的制約,而這兩種權力都在中央權力的打壓下不斷削弱。在地方勢力壯大之前,官僚階層由于其貴族身份在政治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們甚至可以與皇帝共治。然而紳權出現后,它逐漸取代了官僚勢力,那么官僚的地位必定會下降,這便從側面促進了中央集權的鞏固。雖然紳權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集權,但是它畢竟是依附于皇權的。同時鄉紳出現后,他們享有的權利都是由皇帝賦予的,即使在基層享有一定控制權但是沒有軍隊,鄉紳終無法發展成地方割據勢力,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促進。
其次,紳權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家族關系。紳權出現之前,具有強大實力的大家族與其一脈相承的庶民家族幾乎沒有來往,后來在鄉紳出現后,是無論貧賤都可以躋身鄉紳階層,逐漸也形成了兩種人群:“一極是貧困無告的人,另一極是那些已取得了上層身份的人”。[12]由于他們具有血緣關系,紳士便可以對普通農民實行更加嚴密的控制。
最后,紳士起到了連接中央與基層地方的作用。由于中央集權難以滲透到各大農村,難以對農村進行有效的統一管理,這時紳士便充當起地方的管理者,維護了社會安定,同時民眾有所需時紳士也承擔與官府溝通的任務,緩解了地方與中央間的矛盾。
參考文獻:
[1] 傅衣凌:《中國傳統社會:多元的結構》: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第3期。
[2] 宋代的學校以京城的國子監為主,雖幾次興學,欲在州縣設立學校,但未成規模。而元代重武輕文,選官以門蔭為主。則不甚重視科舉選官。參見王炳照、徐勇:《中國科舉制度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56頁。
[3] 秦暉:《傳統中華帝國的鄉村基層控制》,載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一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2頁。
[4] [德]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工容芬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45頁。
[5] 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98頁。
[6] 格爾哈斯·倫斯基:《權力與特權:社會分層的理論》,浙江人民出版社,第252頁。
[7] 王先民:《論民權即紳權》。
[8] 徐祖瀾:《鄉紳之治與國家權力以明清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為背景》,《法學家》2010年第6期,111-127頁。
[9] 徐祖瀾:《鄉紳之治與國家權力以明清時期中國鄉村社會為背景》,《法學家》2010年 第6期,111-127頁。
[10] 從翰香:《近代冀魯豫鄉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頁。
[11] 《政府公報》,上海上海書店1988出版。
[12] 吳晗、費孝通等:《皇權與紳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頁。
作者簡介:
曹璇,女,1994.07-,江蘇南京人,南京工業大學憲法與行政法專業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