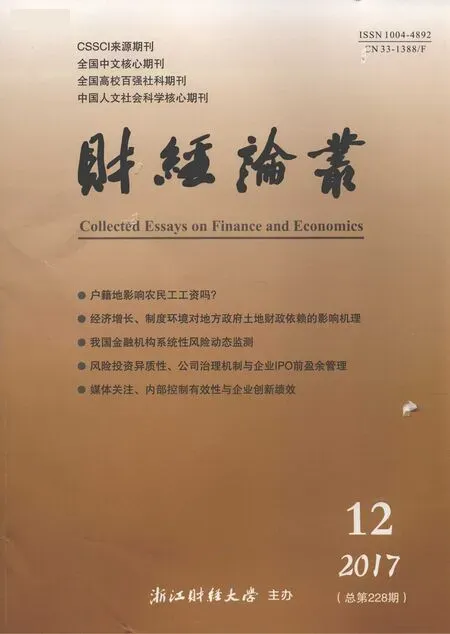財政分權背景下的經濟增長質量地區差異
——基于系統GMM及門檻效應的檢驗
林 春,孫英杰
(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財政分權背景下的經濟增長質量地區差異
——基于系統GMM及門檻效應的檢驗
林 春,孫英杰
(遼寧大學經濟學院,遼寧 沈陽 110036)
財政分權在中國經濟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基于此背景下,本文選擇我國29個省(市、自治區)2000~2015年的面板數據,構建動態面板和門檻面板模型,對財政分權與我國經濟增長質量進行實證檢驗,結果發現:一是財政分權對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并且會因地區發展的差異性而表現出不同的促進效果;二是財政分權對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最后,針對上面結論,得出繼續強化地區財政分權力度是實現我國經濟增長質量提升的重要啟示。
財政分權;經濟增長質量;地區差異;系統矩估計;門檻效應
一、文獻回顧與評述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方向過渡,而作為發揮國家重要職能的財政分權體系必然會助推這種階段的過渡,其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便備受關注。國外有關財政分權理論較早可追溯到Tiebout(1956)的“以腳投票”理論,他通過用腳投票模型檢驗了地方政府根據居民偏好提高供給公共產品的效率,從而提高社會福利水平[1]。這點與Musgrave(1959)認為地方政府利用居民偏好進行資源合理配置來穩定經濟增長的結論[2]和Oates(1972)在分權定理中提出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更有效率的結論不謀而合[3]。同樣,Brennan & Buchanan(1980)論證了收入約束角度下不同級別政府的競爭會提高公共物品的生產效率,以此來促進經濟增長[4]。隨著經濟發展過程的不斷演進,催生以Weingast(1995)、Qian & Weingast(1997)為代表的第二代財政分權理論,他們認為財政分權能夠促進經濟激勵機制和地方政府競爭機制的產生,并以此來推進地方經濟的增長[5][6]。為了進一步驗證這一結論的準確性,學者們采用不同的面板數據進行了相關的檢驗:Iimi(2005)利用跨國數據(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實證檢驗,發現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呈現正向相關關系[7];Akai & Sakata(2002)利用美國50個州立數據的實證檢驗,發現財政分權對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8];Thiessen(2003)利用OECD高收入國家的實證檢驗,發現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存在正負兩種效應,在某個臨界值以內是正效應,而超過這個臨界值便成了負效應[9]。由此可見,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是值得肯定的。
國內有關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研究頗為豐富,作為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中國,張晏和龔六堂(2005)認為財政分權賦予地方政府的經濟激勵會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能動性,進而提升經濟實力[10]。林毅夫和劉志強(2000)、沈坤榮和付文林(2005)通過省級面板數據也驗證了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11][12]。對此結論,張軍等(2007)從促進基礎設施建設的角度、張璟和沈坤榮(2008)從優化資源配置的角度、范子英和張軍(2009)從經濟增長效率的角度、田超(2016)從城市經濟的角度等都給予了一致的回應[13][14][15][16]。而殷德生(2004)卻認為該結論是在最優分權結構下才可以實現的,否則分權所帶來的高成本會抑制經濟增長[17]。同時,周業安和章泉(2008)以1994年分稅制改革作為實證研究節點,發現分稅制改革后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才是較為顯著的[18]。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王永欽等(2007)注意到分權化改革對中國經濟成功轉型的重要性[19],并能夠提升地方政府的財政激勵強度[20],相應的地方經濟發展狀況也會得到有效改善。但基于各地區(東部、中部和西部)包括地理位置、經濟結構等多方面的不同,導致促進效果也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并得出促進效果與地區的發達程度成正相關關系[21]。因此,實現有效的財政分權改革對提升當前中國經濟實力是至關重要的。
通過對上述的文獻梳理與回顧,我們非常值得肯定的就是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但這里的“增長”主要指增長的速度而非增長的質量,質量作為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內生動力,如果不能與其速度齊頭并進,那么經濟增長很快就會進入到了“疲軟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緩慢的表現也恰恰體現在這里,由此推斷,提升我國目前經濟增長質量是至關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為“十三五”規劃下穩步于中高速經濟增長目標提有效保障。
二、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動態面板模型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方法估計
為了檢驗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關系,并考慮到被解釋變量滯后期對當期的影響以及內生性問題,本文擬建立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如下:
lnTFPit=β0+β1lnTFPit-1+β2lnFDit+β3∑θjlnCVit+εit
(1)
其中,TFP代表以經濟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的經濟增長質量;FD代表財政分權水平;CV代表控制變量;ε代表隨機擾動項;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j代表控制變量種類。
考慮到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控制變量因素有對外開放程度(Open)、經濟發展水平(Economic)、政府干預程度(Government)以及市場化程度(Market),本文將最終動態面板數據模型確定如下:
lnTFPit=β0+β1lnTFPit-1+β2lnFDit+β3lnOpenit+
β4lnEconomicit+β5lnGovernmentit+β6lnMarketit+εit
(2)
對于方程(2)的估計,不可回避的就是存在內生性問題和短面板數據的局限性。財政分權相對于經濟增長質量可能是內生的,即同當期的誤差項無關且與誤差項的一階滯后及更高階滯后相關。鑒于文中被解釋變量滯后項的存在會導致采用傳統OLS估計產生偏差,此時選擇的最佳方法就是廣義矩估計。廣義矩估計具體分為差分矩估計(DIF-GMM)和系統矩估計(SYS-GMM)兩種。Arellano & Bond(1991)提出一階差分矩估計的方法,將其變量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引入差分方程,并通過差分消除固定效應,這樣就可以獲得對文中存在內生性問題的有效解決[22]。此時,一階差分矩估計的矩條件為:
E(εi,t-εi,t-1)Zi,t-j=0j=2,3,…;t=2000,…,2015
(3)
其中,Zi,t為方程中任一變量,變量的二階滯后項作為差分方程的工具變量。
Arellano & Bover(1995)和Blundell & Bond(1998)進一步提出,引入差分變量的滯后項作為水平方程的工具變量[23][24]。此時,水平方程的矩條件為:
Eεi,tΔZi,t-j=0j=1,2,…;t=2000,…,2015
(4)
此時,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相結合的矩條件便構成了系統矩估計(SYS-GMM)。限于系統矩估計對矩條件所要求的苛刻性,故其估計出來的結果也相對更為準確。
采用系統矩估計方法必須要通過Hansen檢驗和AR(2)檢驗,Hansen檢驗值是用來判斷是否存在工具變量的過度識別,AR(2)檢驗值是用來判斷殘差項是否自相關,這樣才能保證估計結果的科學性。因此,本文擬采用系統矩估計方法對其設定方程進行有效估計。
(二)變量定義與數據來源
被解釋變量選取方面:鑒于對經濟增長質量的衡量,學者和專家們給出了不同的詮釋,但趨于一致被認可的就是將經濟全要素生產率指標作為其代理變量[25][26],這與提高經濟增長質量重在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結論完全吻合。故此,本文這里也采用經濟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對經濟增長質量的衡量。具體計算過程參照林春(2016)[27]。
解釋變量選取方面:通過對現有相關文獻的查閱,有關財政分權指標的衡量,大致分為三大類,分別從收入角度、支出角度和自有收入角度進行衡量。鑒于本文著眼于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影響的全面考察,其對財政分權指標衡量的準確性是至關重要的,又考慮到所獲得實證結論的科學性,故本文也將從三個角度來衡量財政分權指標。具體指標定義:一是用地方財政收入分成度來衡量收入角度下的財政分權指標(FD1),即地方財政收入分成度=人均地方本級財政收入/(人均地方本級財政收入+中央本級人均財政收入);二是用地方財政支出分成度來衡量支出角度下的財政分權指標(FD2),即地方財政支出分成度=人均地方本級財政支出/(人均地方本級財政支出+中央本級人均財政支出);三是用地方政府收入自給率來衡量自有收入角度下的財政分權指標(FD3),即地方收入自給率=各地區本級自有財政收入/(該地區自有財政收入+中央轉移支付)。
控制變量選取方面: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筆者發現主要集中對外開放程度、經濟發展水平、政府干預等以下幾個方面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具體指標定義如下:對外開放程度(Open),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導致各地區的融資環境呈現較大的差異,進而影響經濟增長質量的提升,故這里采用各地區進出口總額與GDP的比值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Economic),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越好,其經濟效益水平越高,相應的經濟質量也就越高,故這里采用各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與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來衡量;政府干預程度(Government),政府的相關行為會對地區企業生產具有較大的影響,包括企業的年終產值和投資動向等等,間接地波及到地區經濟增長的發展活力,以此來影響地區經濟的增長質量,故這里采用各地區財政支出與GDP的比值來衡量;市場化程度(Market),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市場化程度在不斷加深,對地區資源配置效率的要求也越來越高,進而影響到地區經濟增長質量,故這里采用樊綱等(2011)測算的市場化指數來表示各地區市場的發展程度[28]。限于現有市場化指數數據只有2000~2009年的,筆者基于已有市場化指數得分數據運用回歸方法得到外插值2010~2015年的數據。
本文采用的面板數據均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財政年鑒》《中國環境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國家統計局網站、各省(市、自治區)統計年鑒和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
(三)動態面板模型實證分析
1.收入角度下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結果分析
從收入角度下的估計結果表1來看,控制了其它變量以后,財政分權(全國)的系數為0.4351,并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全國)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財政分權(東部)的系數為1.1302,并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東部)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財政分權(中部)的系數為3.0923;并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中部)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財政分權(西部)的系數為0.3930,并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西部)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由此可見,收入角度下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點同徐國祥等(2016)[29]結論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并因地區發展的差異性而表現出促進效果的不同,其中,東部促進效果最強,西部次之,中部較差。收入即財權,地方政府應該逐步下放財權,并通過財政激勵政策來驅動地方經濟活力,以此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質量。控制變量方面:只有經濟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質量表現出較好的促進作用,這與經濟發展理論也是非常吻合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經濟增長質量提升越快;而對外開放、政府干預和市場化等都對經濟增長質量起到了抑制作用,這個主要歸因于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國情,外加地區資源稟賦的差異,造成很多方面出現了較大的失衡,包括地區的對外開放、貿易往來、政府行為和市場制度等等都給經濟增長帶來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

表1 收入角度下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估計結果
注:*、*** 、*** 分別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顯著;括號內數字為Z統計量。下同。
2.支出角度下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結果分析
從支出角度下的估計結果表2來看,控制了其它變量以后,財政分權(全國)的系數為2.9434,并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全國)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財政分權(東部)的系數為2.2732,并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東部)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財政分權(中部)的系數為4.8634,并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中部)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財政分權(西部)的系數為1.9588,并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西部)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由此可見,支出角度下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點同鄧明和王勁波(2014)等研究結論保持一致[30]。并因地區發展的差異性而表現出促進效果的不同,其中,中部促進效果最強,東部次之,西部較差。支出即事權,通過地方政府事權不但可以提高投資規模,還能夠創造更多的投資機會,進而推動地方經濟增長。故此,中部地區更應該加強政府事權力度,激發新的投資活力,以獲得快速的經濟崛起。控制變量方面: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干預對經濟增長質量都具有促進作用,并且政府所發揮的主導作用比較明顯,這點也是符合當下市場發展環境需要;而對外開放和市場化因其地區差異所導致的失衡仍然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產生負面效應。
3.自有收入角度下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結果分析
從自有收入角度下的估計結果表3來看,控制了其它變量以后,財政分權(全國)的系數為1.7021,并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全國)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財政分權(東部)的系數為5.5601,并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東部)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財政分權(中部)的系數為1.3710,并且在5%水平顯著,說明財政分權(中部)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財政分權(西部)系數為3.3690,并且在1%水平上顯著,說明財政分權(西部)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由此可見,自有收入角度下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這點同陳碩和高琳(2012)等研究結論不謀而合[31]。并因地區發展的差異性而表現出促進效果的不同,其中,東部促進效果最強,西部次之,中部較差。同時,彰顯了地方財政自主度對經濟增長的顯著性促進作用。對此,陳碩和高琳(2012)[31]提出了側重于財權方面的改革,即從大規模的轉移支付轉向給予與地方政府支出相匹配的自有收入。控制變量方面:經濟發展水平和政府干預對經濟增長質量都具有促進作用,這點同上面的結論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原因不在解釋;而對外開放和市場化的抑制作用依然表現較強,警示了政策制定者一定要考慮地區發展的協調性和均衡性,避免產生“馬太效應”的悲劇,以此來全面提升地區經濟增長質量。

表3 自有收入角度下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估計結果
(四)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實證結果的準確性和科學性,筆者從以下兩個方面對前文的結論進行穩健性檢驗:一是替換市場化指數變量進行結果估計,二是分時間段進行結果估計。
1.考慮替換變量
筆者采用王小魯等(2016)最新公布的市場化指數對前文采用外插值法計算的市場化指數進行變量替換[32],結果發現替換市場化指數變量并沒有改變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促進作用,同前文結論保持高度一致性。
2.分時間段進行回歸
考慮到我國不同時期的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存在差異性,筆者選取具有代表性的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作為穩健檢驗節點,分別對2000~2008年和2009~2015年兩個時間段進行有效估計。結果發現,分區間段并沒有改變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促進作用,同前文結論保持高度一致性。
三、財政分權對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門檻效應分析
(一)模型設定
上述動態面板模型回歸結果表明,不同角度衡量的財政分權對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均具有顯著的影響。那么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受財政分權的影響是否存在門檻特征呢?為此,筆者繼續對其進行檢驗,主要參照Wang(2015)的研究方法構建門檻效應模型[33],由于具體門檻數不知,筆者先將模型設定為單一門檻模型,模型設定如下:
lnTFPit=a01+a11lnFD1it(qi≤r)+a12lnFD1it(qi>r)+
(5)
lnTFPit=a02+a21lnFD2it(qi≤r)+a22lnFD2it(qi>r)+
(6)
lnTFPit=a03+a31lnFD3it(qi≤r)+a32lnFD3it(qi>r)+
(7)
其中,qi為門檻變量,上述方程分別選擇收入角度、支出角度和自有收入角度的財政分權指標作為門檻變量,r為未知門檻值。
(二)門檻回歸結果分析
1.門檻效應的檢驗
為了保證門檻估計的精度,分析收入角度、支出角度和自有收入角度下的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門檻特征,本文依次檢驗模型的門檻數,得到F統計量和P值,具體數值見表4。結果表明,收入角度下的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單一門檻、雙重門檻和三重門檻的P值分別為0.00、0.00和0.76,其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非常顯著;支出角度下的財政分權對中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單一門檻、雙重門檻和三重門檻的P值分別為0.00、0.24和0.97,其單一門檻非常顯著;自有收入角度下的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單一門檻、雙重門檻和三重門檻的P值分別為0.00、0.00和0.72,其單一門檻和雙重門檻非常顯著。

表4 門檻效果檢驗
注:** 和*** 分別表示在5%和1%的顯著水平上顯著,P值為采用Bootstrap方法反復抽樣300次得到的結果。下同。
收入角度、支出角度和自有收入角度下的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門檻估計值和相應的95%置信區間列示于表5。

表5 門檻估計結果
2.門檻回歸結果
從表6可以看出,收入角度下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通過了雙重門檻模型檢驗。當FD1≤0.6960時,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質量在1%的顯著水平上呈負相關,這說明地方財政分權水平每提高1%,會使經濟增長質量下降0.5169,此時降低財政分權水平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當0.690

表6 收入角度下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質量雙門檻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表7 支出角度下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質量雙門檻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從表7可以看出,支出角度下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通過了單一門檻模型檢驗。當FD2≤0.7057時,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質量在1%的顯著水平上呈負相關,這說明地方財政分權水平每提高1%,會使經濟增長質量下降0.6954,此時降低財政分權水平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提高地方財政支出在總支出的占比會降低經濟增長質量,降低地方財政支出是有利的。當FD2>0.7057時,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質量不存在顯著影響,此時每提高1%的財政分權水平會引起經濟增長質量提高0.0039,也就是說提高地方財政支出在總支出中的占比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即增加地方財政支出是有利好效應的。
從表8可以看出,自有收入角度下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通過了雙重門檻模型檢驗。當FD3≤0.4830時,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質量在1%的顯著水平上呈負相關,這說明地方財政分權水平每提高1%,會使經濟增長質量下降0.6191,此時降低財政分權水平有利于提高經濟增長質量。當0.4830

表8 自有收入角度下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質量雙門檻模型參數估計結果
綜上可以發現,財政分權對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在財政分權水平較低時,降低財政分權水平有利于提高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在財政分權水平較高時,提高財政分權水平有利于提高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從我國財政分權體制的發展演化歷程來看,我國的財政分權體制是從集權到分權的過程,將中央主導與地方輔助相結合,并通過規范稅制、優化稅制結構、擴大財政補貼以及降低稅負等手段擴大消費和投資需求,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優化資源配置效率,最終實現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因此,要想提高我國的經濟增長質量,就要綜合考慮我國財政分權所處的階段以及現實的客觀經濟環境,不能單純盲目的僅提高或者降低財政分權水平。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選擇我國29個省(市、自治區)2000~2015年的面板數據,構建動態面板和門檻面板模型,采用系統GMM方法與門檻面板估計方法對其進行估計,以此來探討財政分權對我國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一是財政分權對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支出角度和自有收入角度下的財政分權對其促進效果更為明顯,并且各地區的促進效果會因其地區發展的不同也表現出較大的差異性。二是財政分權對我國經濟增長質量存在顯著的門檻效應,收入角度和自有收入角度下的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通過了雙重門檻模型檢驗,而支出角度下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通過了單一門檻模型檢驗。在財政分權水平較低時,降低財政分權水平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而在財政分權水平較高時,提高財政分權水平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通過實證結論得出如下政策啟示:第一,為了提高新常態下我國經濟增長質量,應該進一步完善財政分權體制改革。從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質量關系來分析,應適當提高地方的財政分權強度,給予地方政府擁有的信息優勢,實現最為優化的區域資源配置。第二,應加強地方政府的激勵制度設計,摒棄“唯GDP論”的傳統舊觀念,必須將經濟增長質量納入到重點考核體系當中,著力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全面提升地區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動能,加速實現新時代下小康社會的步伐。第三,鑒于財政分權對經濟增長質量的影響會受到對外開放程度、經濟發展等諸多因素的束縛,故各地區(東部、中部和西部)必須依據自身的發展特征來設計相應的財政分權政策,這樣才能保證財政激勵相容制度的有效發揮,促進財政分權與地區資源配置的良性互動,實現地區經濟增長質量的本質提升。
[1] Tiebout C. 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6,64(5),pp. 416-424.
[2] Musgrave R. A. 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 A Study in Public Econom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9, 99(1),pp. 213-213.
[3] Oates W. E. Fiscal Federalism [M]. New York:Harcout Brace Jovanovich,1972.
[4] Brennan H. G., Buchanan J. M. The Power to Tax: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A Fiscal Constitution [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5] Weingast B. R.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1995,11(1),pp. 1-31.
[6] Qian Y., Weingast B. R.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er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7,11(4),pp. 83-92.
[7] Iimi A. De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An Empirical Note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05,57(3),pp. 449-461.
[8] Akai N., Sakata M.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ntributes to Economic Growth:Evidence from State-Level Cross-Section Data for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2,52(1),pp. 93-108.
[9] Thiessen U. Fiscal Decentralis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High-Income OECD Countries [J].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2003,24(3),pp. 237-274.
[10] 張晏, 龔六堂. 分稅制改革、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 [J]. 經濟學(季刊),2005,(4):75-108.
[11] 林毅夫,劉志強. 中國的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 [J]. 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4):5-17.
[12] 沈坤榮, 付文林. 中國的財政分權制度與地區經濟增長 [J]. 管理世界,2005,(1):31-39.
[13] 張軍, 高遠, 傅勇,等. 中國為什么擁有了良好的基礎設施? [J]. 經濟研究,2007,(3):4-19.
[14] 張璟, 沈坤榮. 財政分權改革、地方政府行為與經濟增長 [J]. 江蘇社會科學,2008,(3):56-62.
[15] 范子英, 張軍. 財政分權與中國經濟增長的效率——基于非期望產出模型的分析 [J]. 管理世界,2009,(7):15-25.
[16] 田超. 財政分權:轉移支付、稅收優惠與首位城市增長 [J]. 財經論叢,2016,(7):30-39.
[17] 殷德生. 最優財政分權與經濟增長 [J]. 世界經濟,2004,(11):62-71.
[18] 周業安, 章泉. 財政分權、經濟增長和波動 [J]. 管理世界,2008,(3):6-15.
[19] 王永欽, 張晏, 章元,等. 中國的大國發展道路——論分權式改革的得失 [J]. 經濟研究,2007,(1):4-16.
[20] 傅勇. 財政分權改革提高了地方財政激勵強度嗎? [J]. 財貿經濟,2008,(7):35-40.
[21] 王文劍, 覃成林. 地方政府行為與財政分權增長效應的地區性差異——基于經驗分析的判斷、假說及檢驗 [J]. 管理世界,2008,(1):9-21.
[22] Arellano M., Bond S. Some Tests of Specification for Panel Data: Monte Carlo Evidence and an Application to Employment Equations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2),pp. 277-297.
[23] Arellano M., Bover O. Another Look at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ion of Error-Components Model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5,68(1),pp. 29-51.
[24] Blundell R., Bond S. Initial Conditions and Moment Restrictions in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s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1998,87(1),pp. 115-143.
[25] 蔡昉. 中國經濟增長如何轉向全要素生產率驅動型 [J]. 中國社會科學,2013,(1):56-71.
[26] 吳敬璉. 以深化改革確立中國經濟新常態 [J]. 探索與爭鳴,2015,(1):4-7.
[27] 林春. 中國經濟全要素生產率影響因素及收斂性研究——基于省際面板數據分析 [J]. 云南財經大學學報, 2016,(2):71-80.
[28] 樊綱,王小魯,朱恒鵬. 中國市場化指數:各省區市場化相對進程2011年度報告 [M]. 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
[29] 徐國祥, 龍碩, 李波. 中國財政分權度指數的編制及其與增長、均等的關系研究 [J]. 統計研究,2016,(9):36-46.
[30] 鄧明, 王勁波. 財政分權與中國的地區經濟增長效率 [J]. 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6):26-36.
[31] 陳碩, 高琳. 央地關系:財政分權度量及作用機制再評估 [J]. 管理世界,2012,(6):43-59.
[32] 王小魯,樊綱,余靜文. 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 [M].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33] Wang Q. Fixed-Effect Panel Threshold Model Using Stata [J]. The Stata Journal,2015,15(1),pp. 121-134.
RegionalDifferenceofEconomicGrowthQualityUndertheBackgroundofFiscalDecentralization—TestbasedonSystemGMMandtheThresholdEffect
LIN Chun SUN Yingjie
(School of Economics,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to a high-quality stage. This article makes use of the dynamic panel model and panel threshold model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29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5 in China.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For one thing,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varies in different regions;for anoth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has a significant threshold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it is concluded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regional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growth.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System;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Regional Difference; SYS-GMM; Threshold Effect.
2017-01-28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 (17FJY008);遼寧省社科規劃基金重點項目(L17AJY008)
林春(1985-),男,遼寧黑山人,遼寧大學經濟學院講師,博士;孫英杰(1987-),遼寧瓦房店人,遼寧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
F810.4
A
1004-4892(2017)12-0033-10
(責任編輯:風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