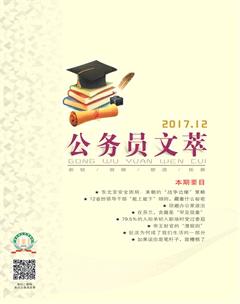古代官員選任得與失
楊陽
夏商周時(shí),實(shí)行封建采邑制,與之對(duì)應(yīng)是“世卿世祿”制,王室和諸侯國主事職官,由其下屬封君貴族擔(dān)任,多數(shù)官職在特定家族內(nèi)部世襲。春秋戰(zhàn)國之際,封建采邑制瓦解,“世卿世祿”制逐漸解體,至秦漢,遂為新的官員選任制度所替代。
從推舉到科舉
戰(zhàn)國時(shí),秦實(shí)行“耕戰(zhàn)”政策,官員選拔專任軍功,統(tǒng)一之后,則開始“推擇為吏”“考試取吏”“通法入仕”,但尚未形成系統(tǒng)的職官選任制度。到了西漢時(shí)期,逐漸形成了征辟和察舉兩種職官選任辦法。
征辟又稱“辟除”“辟舉”等,是各級(jí)官府任用屬員的制度,由各官署和地方政府自行組織完成,聘任對(duì)象為椽史以下的低級(jí)官吏。察舉由中央政府主持進(jìn)行。公元前165年,漢文帝下詔,要求各郡國舉薦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并親自主持了對(duì)推薦人選的測試。漢武帝以后,察舉成為定制。除“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外,還有孝廉、秀才、文學(xué)高第等十多種名目,大體是平均20萬人口推薦1人。由各郡國負(fù)責(zé)遴選,送到京城,再由皇帝主持測試。對(duì)諸生考其章句,合格者按其成績委以文職。
曹魏時(shí),征辟和察舉演變?yōu)榫牌分姓啤V醒胝x派“賢有識(shí)鑒”的官員到各州郡,充任中正,根據(jù)家世、才、德三項(xiàng)標(biāo)準(zhǔn)遴選人才。
九品中正制與兩漢察舉制類似,不論是鄉(xiāng)里推薦,還是有關(guān)部門考察,都更注重“鄉(xiāng)邑清議”。選拔標(biāo)準(zhǔn)的客觀化程度不足,會(huì)使某些沽名釣譽(yù)之徒有可乘之機(jī)。魏晉在標(biāo)準(zhǔn)中加入家世,當(dāng)然有利于標(biāo)準(zhǔn)的客觀化,但也因此使才、德兩條很難量化的標(biāo)準(zhǔn)退居到次要或無足輕重的位置。到西晉,朝廷派駐各地的中正多為地方豪族控制,遴選的人才多為世家子弟,出現(xiàn)“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察舉、征辟和九品中正制還有一個(gè)共同特點(diǎn),那就是選拔、推薦的權(quán)力重心在地方,中央只是根據(jù)地方推薦的結(jié)果行使任用權(quán),這與中央集權(quán)的國家結(jié)構(gòu)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沖突。隨著中央集權(quán)體制的不斷強(qiáng)化,人才遴選權(quán)的上移也是應(yīng)有之義。公元587年,隋文帝下令設(shè)立“秀才科”,每州每年選派3名貢士參加考試。公元606年,隋煬帝定制以十科舉人。兩漢以來的薦舉制遂為科舉制所代替。
鄉(xiāng)試、省試與殿試
唐朝科舉分為常科和制科兩類。常科每年舉行,分為秀才、明經(jīng)、俊士、進(jìn)士等科目,其中明經(jīng)、進(jìn)士兩科最為重要。明經(jīng)主要考經(jīng)義,進(jìn)士主要測詩賦。制科是根據(jù)需要臨時(shí)設(shè)置的科目,有唐一代,先后設(shè)置過120余種。制科考試,官吏和平民都可以參加,凡考中,官吏可升遷,平民則委以相應(yīng)官職。但因制科科目多針對(duì)特殊技藝設(shè)置,以農(nóng)、商、醫(yī)、土木營造最為常見,故不為士人所重,制科出身被稱為“雜色”或非“正途”。
常科考試參加者是生徒和鄉(xiāng)貢。生徒是各級(jí)學(xué)校學(xué)生,經(jīng)學(xué)館考試合格,可送尚書省參加科舉。鄉(xiāng)貢是指自學(xué)或私塾學(xué)習(xí)的人士,州縣考試合格,可送至京城參加考試。考試由禮部主持,合格稱及第。結(jié)束后,禮部要將及第人員造冊(cè)登錄,交給吏部,再由吏部主持考試,合格者由吏部根據(jù)成績、名次等提出任用建議,報(bào)請(qǐng)皇帝批準(zhǔn)。
兩宋時(shí),科舉科目出現(xiàn)較大變化,但進(jìn)士科仍最為重要。考試內(nèi)容不再以詩賦為主,而是測試對(duì)儒學(xué)義理的掌握程度。北宋科舉分鄉(xiāng)試、省試、殿試三個(gè)層次。鄉(xiāng)試由州府主持,中試者由州府推薦到京城,參加禮部會(huì)試,會(huì)試結(jié)束,合格者再由皇帝主持殿試,排定最終的名次。
明朝有省級(jí)建制,鄉(xiāng)試遂改為在各省省府舉行,正常情況下三年一次,時(shí)間固定在秋季八月,稱“秋闈”。鄉(xiāng)試雖在各地舉行,但主考官、副考官卻由中央選派。大凡在府州縣考試通過的秀才都有資格應(yīng)試,考試通過者稱“舉人”,有資格參加會(huì)試。會(huì)試由禮部主持,但主考官、副考官都由皇帝臨時(shí)委任。會(huì)試也是三年舉行一次,時(shí)間在鄉(xiāng)試結(jié)束后的第二年春季二月,稱“春闈”。考試名次也分三甲,要到殿試之后才能確定。明清時(shí),一甲只取前三名,稱狀元、榜眼、探花,合稱“三鼎甲”,賜進(jìn)士及第。二甲、三甲均無定額。
古代官員選任制度的得與失
秦漢的征辟和察舉,往往訴諸于鄉(xiāng)里輿論,看似有一定的民主意味,但輿論本身帶有模糊性和主觀性,很多時(shí)候未必能體現(xiàn)民眾的真實(shí)意愿,很容易被地方豪強(qiáng)所操縱,故而當(dāng)時(shí)遴選的結(jié)果往往反映地方實(shí)力派的意愿。
科舉制最大的優(yōu)勢(shì),不是能夠更精準(zhǔn)地發(fā)現(xiàn)和錄用人才,而是使人才的遴選有了更客觀化的標(biāo)準(zhǔn)和流程,從而使官員的遴選和錄用能最大限度地?cái)[脫地方勢(shì)力的影響,完全為中央所掌控,這顯然更符合中央集權(quán)政體的本質(zhì)要求。同時(shí),科舉制也為寒門子弟躋身社會(huì)上層提供了更多的機(jī)會(huì),相應(yīng)地,也極大拓寬了國家官員遴選的范圍。更重要的是,科舉制的定期舉辦,造就了一個(gè)數(shù)量相當(dāng)龐大的特殊身份階層。他們因科舉取得功名,因功名而享受包括做官在內(nèi)的各種法定特權(quán),成為儒學(xué)明教和王朝政治的忠實(shí)擁戴者,即便沒有機(jī)會(huì)晉身為官,也會(huì)作為“準(zhǔn)政府成員”(士紳)自愿擔(dān)當(dāng)社會(huì)治理者的角色。從政治學(xué)角度看,科舉制的實(shí)施有效擴(kuò)大了王朝政治的合法性資源。
但是科舉制測驗(yàn)的都只是應(yīng)試者的文才或理論水平,而不是實(shí)際的行政能力。從行政人才的選拔來說,這種考試的有效性和準(zhǔn)確性自然是很成問題的。事實(shí)上,科舉大盛的兩宋和明朝,其官僚系統(tǒng)的運(yùn)轉(zhuǎn)效率和治理能力,比之漢唐很難說有所提高,以至于到清朝,一些皇帝有意重用異途出身的官員,對(duì)科甲出身的官員卻心存歧視。也正因如此,唐宋以后,官員的晉升政績?nèi)跃哂袥Q定意義,畢竟政府中大多數(shù)崗位真正需要的,是實(shí)際的行政能力。
(摘自《人民論壇》)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