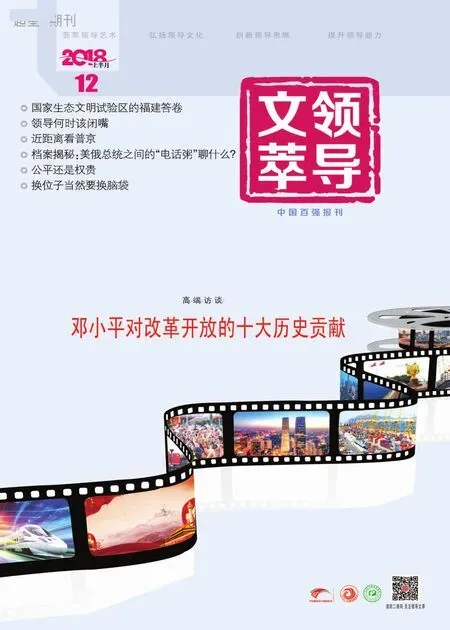曹劉論英雄
新垣平
青梅煮酒論英雄,是幾千年來人們津津樂道的三國故事。曹操和劉備兩位歷史主角,在最親密的一刻,照見了彼此的內心,從此走向一生的對立。但其中的真意,卻不是那么容易說清楚。
青梅與煮酒,是《三國演義》中的噱頭,歷史上是否有過不得而知。但曹操和劉備的確是在一起飯局的時候討論英雄的。《三國志》說:“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裴松之的注解引《華陽國志》,增添了重要的下文:“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圣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
看上去,歷史記載和小說描寫只不過是詳略程度的不同,但是其間卻有不可忽視的差異。小說里,曹操還說了一段著名的話:“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這個定義看上去很牛,其實大為可疑。要打天下,胸懷大志本來是必要條件,如果不是抱有“大志”去努力打拼,絕對沒有成功的可能。這個條件劉備自然是符合的,可群雄中符合的人也不少。試問袁紹、袁術、孫策等人難道沒有“大志”嗎?
再說“腹有良謀”,這個玄德公很抱歉就談不上了。到論英雄時為止,劉備打拼十幾年,到頭來還得依附曹操,雖然有客觀條件的問題,但劉備也曾拿過一手好牌,有兩個萬人敵的兄弟,還占有過徐州,只是才能平庸,屢戰屢敗,是難以否認的事實。反過來講,諸葛亮、郭嘉等的確腹有良謀,又似乎不能算“英雄”。那曹操為什么說劉備是英雄?而且唯有他和自己是英雄?
答案很簡單,這個“英雄”的定義是演義所杜撰,為最后拋出“使君與操”的包袱做鋪墊,文學技法上很好看,但經不住推敲。曹操這么說,是另有理由。
從曹操的視角看,劉備雖然實力遠不如自己和其他諸侯,但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奇跡制造者”。他明明出身低微,卻在復雜混亂的時局中日益壯大。先是得到大商人資助,拉起義兵發跡;中間丟官亡命,卻又靠上了何進的勢力,咸魚翻身;此后雖然被農民軍所敗,但投奔公孫瓚,地位有增無減;救援陶謙,居然得到了素昧平生的陶謙的信任,當上了徐州牧,成為封疆大吏之一;后來聯合他曹操,又滅了呂布;如今到了許都,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關系網,連他也不易控制了……
為什么劉備能做到這些?從《三國演義》的小說和電視劇里怕是找不到答案。在后代的藝術形象中,劉備的成功靠的無非是兩個要素:高貴的血統和仁義的精神。這符合平民社會的審美需求,但在真實的漢末亂世,這些恐怕沒什么實際作用。
但從殘存的歷史資料中,卻依稀可以看到另一個劉備。他確實有一種特殊能力:一種極具魅力的領袖型人格,能令人衷心信任、熱愛和歸附。真實的劉備并不是小說中的迂腐君子,靠一場莫名其妙的結拜而發家。《先主傳》中說他年輕時“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關羽和張飛就是他結交的豪俠。劉備出道時早已不是賣草鞋的攤販,而是地方上聲名赫赫的“黑道”大哥。
劉備善于禮賢下士,《三國志》說:“備外御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眾多歸焉。”但這種同甘共苦中仍帶有領袖的尊嚴,譬如“怒鞭督郵”的壯舉,按正史記載是劉備親手所為,隨后棄官而去,瀟灑之至。如果沒有一點決斷的果敢,殺伐的狠辣,要折服關張趙這樣的一流豪杰,是不可能的。
劉備的這種才能,近似于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謂的“克里斯瑪型權威”,是一種近乎宗教教主的氣場和感染力,能令人衷心信從。依靠這樣的稟賦,以后的劉備在和袁紹、劉表、孫權、劉璋等人打交道的過程中,還會多次死里逃生,遇難成祥。
甚至曹操自己,也一度中了劉備的“克里斯瑪”,對劉備非常欣賞,“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好得蜜里調油。但曹操自己也是領袖人物,很清楚劉備這種能力的危險性,這也就是謀臣勸他殺劉備而他始終躊躇不決,難以下手的原因,其論英雄之語也就帶有了相愛相殺的意味。
但曹操為什么說這句話?演義里說是存心試探,十分牽強。試想即便劉備庸碌,聽到曹操把他和自己相提并論,又如何能不驚不怕?反過來說,如果劉備鎮定如恒,不也證實了他的英雄之姿?既然兩面說都可以,能試探出什么呢?《華陽國志》中記載了這段對話,但補充說“(曹)公亦悔失言”,大概這個念頭在曹操腦海中轉了太久,終于情不自禁吐露了出來。劉備嗅到了其中的危險,很快借故逃走。從此,二人一生對敵,卻再也沒有見過面。
(摘自《南方周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