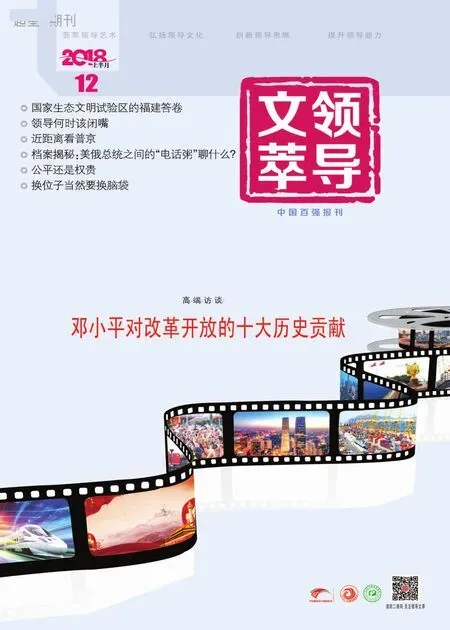禮節不疏
貞堯仔
中國人歷來注重禮節,中華民族,素有“禮儀之邦”的美譽。禮節是人們社會交往的禮儀規矩,是恭敬他人的善行,應當通達踐履。周朝設“九賓之禮”,是我國古代最隆重的禮節,是周朝天子專門用來接待天下諸侯的重典。現在國家元首訪問放禮炮,檢閱儀仗隊,是國家交往所行的國禮。國與國邦交需要禮節,人與人交往同樣需要禮節,正像俗話所說:“人熟禮不熟。”
古人說,人生而有欲,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則不能不爭,爭則亂,故制禮儀以分之。人在社會生活和交往中要明“禮”,人無“禮”無以立,社會無“禮”則滋亂生。“天地者,生之時;禮義者,治之時。”“故禮義者也,人之大端也。”“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孔子說得更徹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影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官事師,不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詞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成不莊。人得處處講禮尊禮守禮。
古人說“禮不踰節”。“好廉自克曰節”。這里講的節,主要指人們行為的節度。節度,就是有節制,有約束,人們在社會生活與交往中保持應有的節度,不能逾出社會道德規范。“禮”注重于人與人社會交往的外在的形式,“節”則注重于人與人在社會交往中的內在的節制、自律。把“禮”與“節”結合在一起,有內又外,內外兼修。
禮節要堅持尊重、遵守、適度、自律。尊重,就是在交往中以相互尊重為前提,尊重對方,謙恭有禮,不傷害對方的利益,同時保持自尊;遵守就是遵守社會道德規范,守時守信;適度就是不卑不亢,有分寸;自律就是自我節制,時時反省自己行為是否符合禮儀規范要求。
《史記》記載,孔子問禮于老子,老子答說:“當今之世,聰明而深察者,其所以遇難而幾至于死,在于好譏人之非也;善辯而通達者,其所以招禍而屢至于身,在于好揚人之惡也。為人之子,勿以己為高,為人之臣,勿以己為上。”講禮節必須遵守社會規范,友善對待他人,不“好譏人之非”、不“好揚人之惡”;擺正自己的位置,“勿以己為高”“勿以己為上”。不能不顧他人的意愿喜好而強為,要謙虛自律,“去子之嬌氣與多欲”。即便有才有德,也要“深藏若虛”“容貌若愚”,不擺譜,不顯耀自己。
朋友之間,上下級之間,禮節也不能疏忽。適度的禮節是友情的添加劑,也是朋友的黏合劑。據《后漢書·樊宏列傳》記載,樊宏,系光武帝劉秀之舅。每逢朝會,樊宏總是提前到達,俯伏待事,到時候才敢起來。樊宏上書陳述應辦的事情及其得失,總是親手書寫,而將草稿毀掉。盡管樊宏是劉秀的長輩,但作為臣子的他始終敬畏皇帝劉秀,劉秀也因此更加敬重他。樊宏病逝,劉秀“謚為恭侯,贈以印綬,車駕親送葬。”反例如明朝宦官魏忠賢在熹宗朱由校在位期間,極受寵信,被稱為“九千九百歲”,結黨營私,排除異己,專斷國政,以致人們“只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崇禎帝朱由檢繼位后,打擊懲治閹黨,治魏忠賢十大罪,命逮捕法辦,魏自縊而亡,其余黨亦被肅清。
自然物態自有其合理的排列組合,相對穩定的結構秩序。人與人之間社會交往,猶如物質的結構秩序,必須遵循一套共同認可且符合社會規范的禮節,以禮相交,如車沿道而行,直至長遠。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