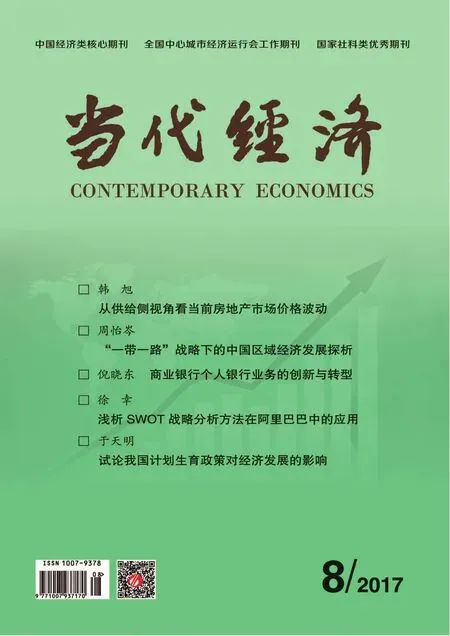習近平“兩山論”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綠色發展
(中央黨校哲學部,北京 100091)
習近平“兩山論”與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綠色發展
薄海
(中央黨校哲學部,北京 100091)
經濟欠發達地區有著自身的生態特征和發展困惑,在發展過程中面臨著經濟壓力與生態壓力雙重限制。習近平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論”)的重要論斷,在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之間建立關聯,有效解決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以“兩山論”為指導,經濟欠發達地區應該堅持經濟與環境兼顧,積極調整產業結構,走向生態環境要效益的綠色發展之路。
“兩山論”;經濟欠發達地區;綠色發展
一、“兩山論”的豐富內涵
首先,“兩山論”體現出人類社會存在的自然環境基礎。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人類“本來就是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同時,“人雙重地存在著:主觀上作為他自身而存在著,客觀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這些自然無機條件之中”,[1]“歷史可以從兩方面來考察,可以把它劃分為自然是和人類史。但這兩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是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2]可以看出,人類的存在與發展也是以自然環境為前提的,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是與自然環境不可分割的。這就是說,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條件,是以“綠水青山”為代表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而人類社會發展所追求的“金山銀山”也只是自然環境價值的一種外在體現。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初就是依賴于環境,對自然資源的一種加工和制造。如果將綠水青山置于社會發展的基礎規約之外,那么人類的生存及社會的發展也將是不可持續的短視追求。可以說,如果脫離了整個生態系統,人類社會的發展也就成為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實質上,“兩山論”指明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自然觀下人類生存、發展的前提基礎與價值歸宿的關系。
其次,“兩山論”挖掘出社會生產力當中的生態要素。生產力的變遷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自然條件是一種生產力。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認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3]而習近平則進一步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的基本理論,創造性地將以“綠水青山”為代表的自然環境等生態要素也視為推動社會財富積累的生產力的一部分。習近平同志曾指出,“要正確處理好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牢固樹立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的觀念。”[4]因此,我們說生態環境既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也是推動經濟發展的生態生產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兩山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的基本理論,將社會生產力當中生態要素的重要性進一步明確并提升至新的高度。
再次,“兩山論”揭示出經濟社會發展所追求的生態價值。人類社會的發展始終沒有離開對價值的追求,而這種價值追求一直都表現出人類中心主義的特征。原始社會,人類的發展囿于技術所限,人類發展的一切為了生存與種族的延續;農業社會,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發展,社會發展的目標仍以溫飽為主;工業社會,科學技術煥發出巨大的威力,人類社會進入到大規模、高投入的線性發展模式。在人類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都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對于生態環境內在價值的追求,更多地以人類的需求為根本導向,自然環境因此不堪重負,爆發出當前嚴重的生態危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也經歷了一個對于生態價值追求的過程,從“以綠水青山換取金山銀山”,到“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再到現在我們所熟悉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樣的邏輯過程,反映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從最初的對于經濟價值的有限追求,到經濟價值受到生態價值的制約,再到對于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的兼顧的歷史進得程。從哲學的觀點看,這是對于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從“二元對立”到“內在同一”的一種轉變,也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辯證轉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不僅僅是一個邏輯命題,更是一種體現對于生態價值追求的哲學命題,其所揭示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系,是從“兩點論”到“重點論”,再到“統一論”的一個過程,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之間關系的辯證思考和生動實踐。
二、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生態特性與發展困惑
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總體上經歷了東南沿海開發、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四個階段。地區間、省域間的發展形成了較為明顯差異,東南沿海與中西部存在巨大的發展不平衡現象,同時在中西部地區間也存在著嚴重的城鄉差距問題,形成了大范圍的經濟欠發達地區,這些地區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人均財政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三項主要經濟指均標低于平均水平。一些地區雖然地域廣闊資源豐富,但經濟發展卻遠不及東部沿海地區,也被稱為經濟欠發達地區。而文章中所提及的經濟欠發達地區主要是指中西部地區。
經濟欠發達地區有著明顯的生態特性,也面臨著特殊的發展矛盾。一般來講,經濟欠發達地區具有資源豐富、人均占有率高、環境承載量大、人口密度小等特征。以西部地區為例,西部能源資源非常豐富,特別是天然氣和煤炭儲量,占全國比重分別高達87.5%和39.0%;在全國已探明儲量的156種礦產中,西部地區有138種,在45種主要礦產資源中,西部占24種,占全國保有儲量的50%以上,另有11種占33%-50%;西部土地面積占全國的71.4%,人均占有耕地2畝,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3倍,耕地后備資源總量大,未利用土地占全國的80%,其中有5.9億畝適宜開發為農用地,適宜開發為耕地的面積有1億畝,占全國耕地后備資源的57%;西部地下水天然可采資源豐富,水資源占全國的80%以上,其中西南地區占全國的70%。這些地區通常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條件、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后,其豐富的資源得不到開發,導致工業化程度不高,其工業污染程度也相對較輕,加之西部地區的人口密度小,地域面積大,可納污的水體和大氣范圍大,因而其生態環境承載能力也優其他地區。
同時,經濟欠發達地區有著迫切的發展訴求,在發展過程中也面臨著特殊的困境。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成為擺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面前的一個首要問題。經濟欠發達地區要發展,這是不容置疑的,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發展。實際上,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困境背后隱藏著一種對價值的判斷,是看重單純發展的經濟價值還是認同自然環境的生態價值,或者是找到二者之間的內在價值關聯,走一條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兼顧的綠色發展可持續之路。受二元論思維影響,傳統的發展模式將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對立起來,以GDP的增長作為衡量經濟水平的唯一標準,許多欠發達地區出現了重經濟發展、輕環境保護的現象。只要推動經濟增長,提高就業率,增加稅收,引進什么項目,項目環評是否達標、有沒有構成對生態環境構成破壞,成為次要問題。不可否認,我國大多數欠發達地區都面臨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的雙重壓力。壓力之下如何妥善處理二者關系,全面實現綠色崛起,是這些地區無法回避的現實難題。實踐表明,追求經濟增長與生態保護的協調發展,是當前我國欠發達地區的最優選擇。
三、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建議
首先,經濟與環境兼顧,避免先發展后治理錯誤模式。經濟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對環境產生影響,這對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發展來說可能會更明顯,但不是說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就一定處于嚴重對立的狀態,近代西方的“先發展后治理”的工業化發展模式,也不是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所不可回避的發展路徑。近代西方工業化模式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產生的,天生帶有資本逐利的貪婪本性以及制度上的缺陷,是在產業技術并不發達的情況下的一種歷史選擇。因此,對于這種錯誤的發展模式,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內,借助于當今綠色科技的所取得巨大成就,我們完全具有一種兼顧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綠色發展的后發優勢。
其次,產業結構性調整,淘汰不利于發展的落后產能。調整產業結構是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重要措施。一般意義上的產業結構調整是指均衡三次產業在國民經濟貢獻中的比例,使得國家經濟結構穩健、具有內生活力,在國際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和風險抵御能力。而生態問題上,從經濟發展綠色化角度去考慮產業結構調整,更重要的是增加各產業對于經濟發展的有效供給,淘汰污染大,資源、能源轉化率低的落后產能,使得產業結構更適合于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目前工業在我國的產業結構中仍占主導地位,特別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更是把優先發展工業作為脫貧致富的突破口,有時甚至不惜環境代價。而生態視角下的未來產業結構發展趨勢,應該是結合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結構性調整,實現產業之間的共生發展。
最后,向生態環境要效益,走綠色發展的可持續道路。習近平提出:“生態環境優勢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游等生態經濟的優勢,那么綠水青山也就變成了金山銀山。”這就為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綠色發展指明了一條向生態環境要效益,走綠色發展的可持續道路。綠色發展理念下的可持續發展道路,要求將生態環境視為生產力的基本要素。某種意義上,人類社會發展的過程就是生態要素、環境資本不斷融入經濟發展的過程。經濟欠發達地區在從“綠水青山”到“金山銀山”轉換的過程中,要認識自身的比較優勢,把生態環境作為經濟發展函數的自變量,最大效用地進行經濟發展過程中生態要素的挖掘,提高經濟發展當中生態要素的有機構成。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91.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6.
[3]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3.
[4]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209.
(責任編輯:宋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