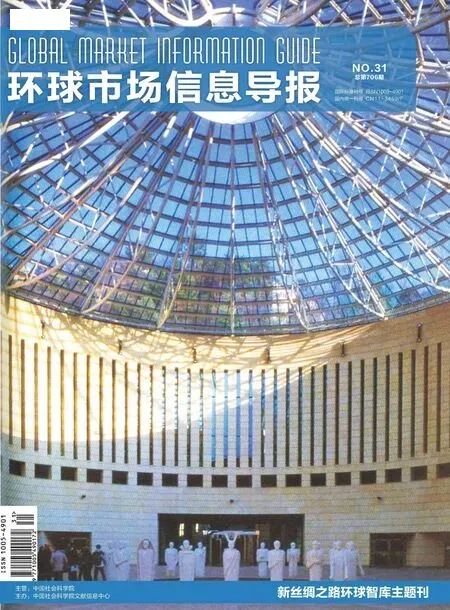存款名義人掛失取走他人存款行為的定性
牛敏
存款名義人掛失取走他人存款行為的定性
牛敏
近年來,存款名義人掛失取走他人存放在自己賬戶下存款的案件屢見不鮮,其行為的性質如何界定,在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都有較大分歧,而爭論的焦點則集中在存款占有的歸屬以及代為保管關系的認定方面。就存款的占有來說,存款現金由銀行占有,存款債權在民法上由存款名義人占有,然而結合刑法的性質來說,其保護的是更為實質的占有及所有關系,因而最終認定存款債權是由實際存款人占有。另外,從保管關系的認定方面來說,實際存款人與存款名義人并不存在委托保管關系。那么,就該類案件來說則屬于將他人的占有轉變為自己占有及所有,應當成立盜竊罪。
基本案情
被害人蘇某與被告人晏某系朋友關系。2005年5月,蘇某借用晏某的身份證到某工商銀行開設個人存款賬戶,并存入10余萬元。蘇某自己持有銀行卡及密碼,以支取賬戶內的錢款。不久,晏某產生非法占有上述錢款的目的,遂獨自用自己的身份證向銀行申請掛失、重新補辦存折并設置密碼,然后分兩次取走賬戶內的全部錢款。
案件爭議
在本案中,對晏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不同觀點:
第一,認為晏某構成詐騙罪。理由是:晏某在明知銀行卡內的存款屬于蘇某所有的情況下,積極編織理由,虛構事實,向銀行謊稱自己不慎丟失了銀行卡,致使銀行受騙,為其辦理掛失、補卡等業務,導致蘇某的財產受到損失,其行為完全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另又由于在本案中,財產處分者并不是受害人,不符合傳統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所以此類案件屬于三角詐騙,受騙人為銀行,受害人為蘇某。
第二,認為晏某構成侵占罪。理由是:一方面,蘇某借用身份證的行為,致使晏某和蘇某之間保管關系的成立。其次,從存款的占有來說,晏某在法律上占有著存款債權。因此,晏某的行為符合侵占罪中將他人的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數額較大,應成立侵占罪。
第三,認為晏某構成盜竊罪。理由是:在本案中,晏某在明知卡內的存款屬于蘇某所有且被害人沒有任何意思允許其非法動用,行為人雖以實名掛失,但卻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秘密的方法轉移、占有銀行卡內的現金,其非法占有意圖明顯,而且此類行為是在自認為不會被被害人當場發覺的情形下實施的,完全符合“秘密竊取”的法律特征,故應成立盜竊罪。
案件評析
筆者支持以上第三種觀點,認為晏某構成盜竊罪,理由如下:
晏某的行為不構成詐騙罪。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在詐騙罪中,存在特定的行為鏈條,即行為人實施了欺騙行為—受害人陷入了錯誤認識受害人基于認識錯誤處分財產—行為人取得財產—受害人遭受財產損失。結合本案,晏某是否構成詐騙罪要根據詐騙罪的行為鏈條判斷。首先,晏某向銀行謊稱卡丟失、密碼遺忘并且沒有告知銀行款項的實際所有人為蘇某,符合詐騙行為的第一步。其次,就銀行是否受騙的問題,根據1999年《關于儲蓄存單、存折密碼更換手續有關問題的批復》,儲蓄機構對儲戶提供的身份證明只進行形式審查,即審查身份證明所用材料和記載的內容在表面上是否符合身份證明管理部門的規定。另根據儲蓄合同的性質,在合同的相對人晏某出示相應材料的情況下,銀行必須為其辦理相應的業務。因此可以說銀行為晏某辦理相關業務是按規定辦事,其并沒有受騙。最后,鑒于銀行沒有受到欺騙,詐騙罪的因果鏈條中斷,所以晏某最后取得財物的行為并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認為晏某的行為屬于三角詐騙的觀點缺乏合理依據。
晏某的行為不構成侵占罪。判斷本案中晏某能否成立侵占罪,問題的關鍵在于確定蘇某和晏某之間是否存在委托保管關系。關于“代為保管”產生的依據,法律無明確規定,理論上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有人認為,“代為保管”是以委托保管關系為基礎;有人認為,“代為保管”是基于委托合同行為,或者根據事實上的管理以及習慣而成立的委托、信任所擁有的對他人財物的持有、管理,將其理解為一切引起非所有的管理關系的行為。就第一種觀點來看,可以說是不當限制了“代為保管”成立的范圍,因為其將“無因管理”等情況下存在保管義務的情形排除在外。就第二種觀點而言,將事實和習慣的管理都理解為代為保管,明顯擴大了侵占罪的適用范圍,擴大了刑法的打擊面,與刑法的謙抑性原則相悖。筆者認為,就保管關系的成立來看是以存在保管合同為依據。這里的保管合同不管是書面的還是口頭的在所不論,但合同的前提性條件(具有雙方的合意)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換言之,成立保管關系,必須在晏某和蘇某之間存在保管的合意,而結合本案來看,顯然不存在委托保管關系。因此,晏某的行為不構成侵占罪。
晏某的行為成立盜竊罪。從上文中可以得出晏某的行為并不符合詐騙罪和侵占罪的構成要件,筆者綜合案件的具體情況,最終認定晏某構成盜竊罪。理由如下:
首先,就存款的占有問題來看,分為存款現金和存款債權的占有。一般認為存款現金是由銀行占有,主要是基于貨幣的本質屬性——占有即所有,而對于存款債權來說,由存款人基于存款合同而占有。在民法上,根據存款實名制,存在誰的名下就應當歸誰所有。換言之,根據民法的相關規定,存款債權是由晏某占有。筆者認為該分析思路在民法上并無問題,但這一規則卻不適用于刑法,原因在于刑法側重保護的是更為實質上的占有及所有關系。具體到本案,蘇某存放在卡內的現金是由銀行占有的,而蘇某實際上是憑借銀行卡和密碼享有其對銀行的債權,所以晏某實質上對該筆現金是沒有支配力的,該存款實質上仍屬于蘇某所有。
其次,從占有的二要件來看,晏某并沒有占有存款債權。刑法上占有狀態的成立,必須考察行為人客觀上的占有事實和主觀上的占有意思,兩者必須同時具備才可成立占有。經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晏某并沒有占有事實的結論,存款債權是由持銀行卡和密碼的蘇某來進行事實上的控制支配。另由于蘇某借用晏某身份證辦卡,只憑卡與密碼就可以實現對卡內錢款的控制,而就晏某來看,其基于同樣的認識也不會產生要替蘇某保管錢款的意思,進而認定其主觀上并沒有占有的意思,最終認定晏某并沒有占有存款債權。
最后,晏某掛失取款的行為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盜竊罪的行為方式是通過平和的手段將他人占有的財物轉移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而在本案中,存款債權由蘇某占有,晏某在產生非法占有目的后,利用自己是存款名義人的便利條件,經過銀行掛失,進而使蘇某的存折和密碼歸于無效,排除了蘇某對錢款的占有,建立自己對該筆款項的占有,可以說晏某的行為完全符合盜竊罪的行為類型。
綜上,筆者認為在存款名義人掛失取走他人存款的案件中,存款名義人的行為屬于將他人占有的財產轉變為自己占有及所有,應以盜竊罪論處。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