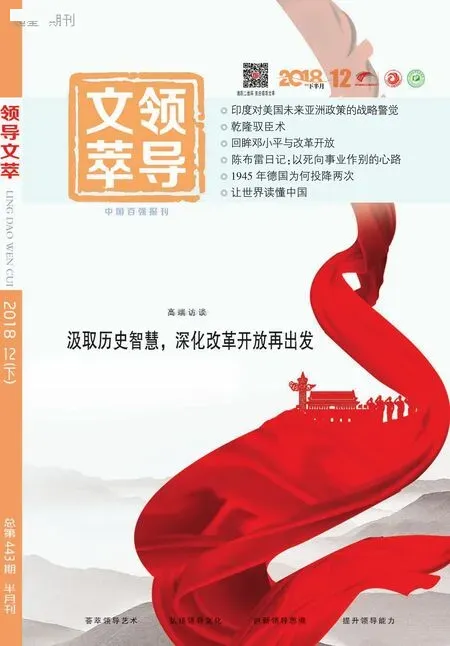那個見證天朝從停滯到崩潰的小男孩
周淮安
1
伏爾泰說,歷史中既充滿了國王的見證,也同樣充滿了他們的仆從的見證。國王的豐功偉績永載史冊,但最接近歷史真實的往往是那些恰好在場的仆從們。
11歲時作為英國派往北京的第一個使團的見習侍童,在乾隆面前秀中文獲得賞賜;35歲時作為英國使團的副使進京,和23年前一樣拒絕下跪磕頭;59歲時成為英國議員,以“中國通”的身份極力主張進行鴉片戰爭。
從“乾隆盛世”到鴉片戰爭的半個世紀內,那些改變世界歷史的重大事件中,這位叫托馬斯·斯當東的英國男孩既是親歷者,也是見證者,有時甚至是推動者。
如同從現代穿越回去的人物一樣,他總是站在歷史恰當的位置,充當那個戳穿皇帝新衣的小男孩。
2
1792年9月26日,英國樸茨茅斯港,一支近700人的龐大使團啟航前往中國,希望與中國進行自由貿易,并建立正常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系。
使團中最小的成員是一名11歲的孩童——副使喬治·斯當東的兒子托馬斯,充當大使馬戛爾尼的侍童,負責在覲見乾隆時給大使提著騎士斗篷的下擺。
在10個月的航行中,托馬斯·斯當東展現了兒童的語言天賦,跟幾位搭船回國的中國神父學習中文,成為使團唯一一個懂點中文的英國人。
進入中國后,一個看起來不太重要的禮節——英使堅持不愿意像奴才一樣下跪磕頭——引發了文明的沖突。前來朝貢的“番邦”竟然不遵循天朝禮儀,乾隆大動肝火,作出重要批示:“朕無求于任何人,爾等速速收起禮品,啟程回國。”
幾經周折,1793年9月14日,使團終于在承德避暑山莊見到了乾隆,行單膝下跪禮,遞交了喬治三世國王的國書。
聽說使團有位“小生番”會講中文,乾隆饒有興趣地讓托馬斯·斯當東走近身邊,可愛的“小生番”用中文講恭維話讓老皇帝很高興,緩解了英國人不愿下跪磕頭的尷尬,乾隆解下隨身攜帶的一個香包送給了他。一個孩童受到了大清皇帝幾乎不可能的青睞與禮遇。
當時的中國,正是乾隆盛世,歷史沉淀形成的“天朝上國”觀念更加強化,視中國為“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不承認與之平等的國家存在,外國近的是“番屬國”,遠的是“化外蠻夷之邦”。學者茅海建在其著作《天朝的崩潰》中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天朝對外體制,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前來朝貢的“英吉利貢使”竟然不下跪,這是有損天朝顏面的事,進一步證明“蠻夷不可教化也。”
英國的外交目的全盤落空,從北到南穿越中國大陸的旅程也戳破了18世紀以來歐洲對中國的美好幻想:一個沒有教會,沒有宗教控制,由開明君主與賢明文人治理的理想國。他們看到的真實景象是老百姓普遍貧困、麻木、愚昧與自私,活得如同螻蟻;上層官吏顢頇、無知、貪婪,腐化墮落。
3
使命雖然失敗了,使團中那個不起眼的小孩托馬斯·斯當東,卻繼續研究中國問題。
從17歲開始到35歲,他長期呆在廣州。18年間,他一直在觀察中國,了解中國,從東印度公司的職員一直當上廣州特別委員會主席。
從1800年19歲開始,托馬斯·斯當東開始研究和翻譯《大清律例》,并于1810年出版,這是第一本從中文翻譯成英文的著作。他在譯著前言中說:“馬戛爾尼勛爵和他的使團在中國的短暫逗留足以使他們發現,中國人所吹噓并得到許多歐洲歷史學家承認的中國對其他民族的優勢全是騙人的。”
很快,他成為最了解中國人的英國人,日漸洞悉中國官場權術與中國人思考方式,成為廣州官場忌憚的老外。
1816年,為了再次嘗試建立正常貿易關系的可能性,英國派出了阿美士德勛爵率領的使團去北京,35歲的托馬斯·斯當東子承父業,成為副使,繼續父輩未盡的事業。
雖然23年過去,乾隆早已作古,大清的統治者已經換成了嘉慶,但“是否磕頭”依然成為雙方沖突的焦點。
因像上次一樣拒絕磕頭,英國使團還沒有見到嘉慶,就被轟出了北京。嘉慶的憤怒從事后的詔書中都能感受到:“中國為天下共主,豈有如此辱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國,不治重罪。”
有意思的是,也許嘉慶怕“外夷”滋生事端,在嚴厲訓斥后,又意外給了英國人糖吃——頒布了幾個有利于西方商人經商的條款。
托馬斯·斯當東根據兩次使團的經驗認為,在中國,“屈服只能導致屈辱,而只要捍衛的立場是合理的,態度堅決卻可以取勝。”
4
24年后,當年的“小斯當東”已經變成了“老斯當東”。大清的統治者變成了道光皇帝。
與托馬斯·斯當東幾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中國不同,大清對外面的世界依舊茫然無知,連英吉利這個“番邦”在哪里都不清楚。
即使如林則徐這樣的杰出人物,也認為英軍打了綁腿,膝蓋不能彎曲,一旦倒地就爬不起來,并斷定“知彼萬不敢以侵凌他國之術窺伺中華……”
鴉片戰爭前夕,1840年4月,英國下議院就是否派出遠征軍展開激烈辯論。59歲的托馬斯·斯當東的發言起了決定性作用,因為大家都知道,在英國沒有人比他更了解中國。
乾隆當年種下的“因”,在47年后結出了“果”。
(摘自“凱迪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