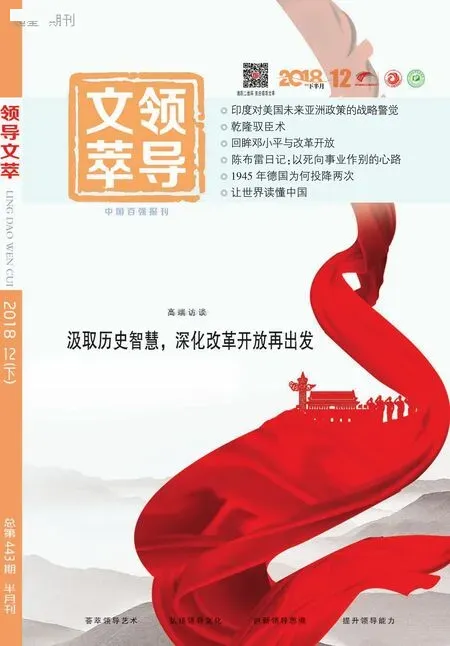避諱:兩千年來那些“你懂的”
李夏恩
在中國古代禮法中,尊者、長輩的名是不能直呼的,由此產生了一種今天看來既有趣又嚴酷的規矩——避諱。有的避諱是被動的,如皇帝名字;有的卻是民間主動創造的“避諱”,特別是那種朝廷不許說,百姓們又很想說的人或事。
政治隱語是被恐懼和憤怒逼出來的無可奈何的“藝術”
手在甲骨上雕刻和在帛紙上書寫的感覺肯定不一樣,前者只能一刀一刀費力刻畫,后者卻可以運筆如飛,書寫自如。但甲骨文和紙上文字最大的區別卻并非省力或費力,亦非字形,而是內容——前者秉筆直書,直言不諱;后者卻時時曲筆諱飾,遮遮掩掩。所謂筆不由心,口是心非。
也許恰恰是因為甲骨刻畫費力,所以上古先人才懶于制造出各式各樣的避諱來隱藏自己的意圖。所謂“夏之政忠”,翻看記載上古王臣言論的《尚書》就會發現,不僅君主的名字可以叫來叫去,不必避諱,就連恐嚇威脅也是赤裸裸不加修飾的:“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如果不聽話,不僅殺了你,還要滅你全家。
在這個時代,歷史上第一句“政治隱語”被制造出來。那就是民眾對夏朝末年暴君桀的那句耳熟能詳的詛咒:“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決心和太陽同歸于盡。
沒有什么比這句話更能表現出民眾對自己領導者的極度憎惡了。但這句話最巧妙的地方是,它不僅恰當地使用了比喻,將人間的主宰君主比作天空的主宰太陽,更是一語雙關,因為在上古時,“日”與“帝”的發音是相似的。只要別有用心的人把舌頭稍微拐一拐,“時日曷喪”就變成“時帝曷喪”。
為何人們一定要采取這種隱語的方式去詛咒君主,卻不像以前一樣直言不諱地批評君主的過失?原因只有一個,直言進諫付出的代價只有死亡,所以人們只能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小心地包裹起來,用隱晦的語言將其道出——政治隱語是被恐懼和憤怒逼出來的無可奈何的“藝術”。
不能明說:諷諫與避諱
語言和文字原本是為了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直觀而明晰,但最后卻用來將真實的看法和觀點包裹起來,沒有什么比這一矛盾更具諷刺性的了。但也恰恰是從這句話開始,人們發現隱語有時比直言更有力量。
伊尹一定諳熟個中之道,這位輔佐成湯滅夏建立商朝基業的賢臣,正是使用政治隱語贏得了成湯的信任。史籍記載,在第一次拜見成湯時,伊尹扛著一只烹飪用的大鼎,用食物的滋味作喻向成湯陳道自己的政治主張。
這種用諷喻來表達自己主張的方法,也就是所謂的“諷諫”。這種“不能明說”的語言藝術是一種思維工具。但政治隱語另一個重要功能卻是禁止思考,它就是“避諱”。
避諱,顧名思義,就是被禁止的話語。在夏商兩代,只有遇到桀紂這樣的殘暴君主,直話直說才會面臨危機轉而用諱語,但進入禮樂文明的周代后,避諱成為了一種常態。
首先出現也是最重要的避諱,就是君主的名字。第一個被避諱的名字可能就是周代開國之君周武王的名字“發”。在提到武王的名字時,不能說“發”,只能用“某”來代替。這一趨勢到了后來,甚至發展成假使有別的名字和君主的名字相同,都要避諱。
一般來說,避諱有時不僅避本字,還會避與這個字音同形近的字,被稱為“避嫌名”。“嫌名”一般規定并不嚴格,但宋代對“嫌名”避諱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的地步,根據《禮部韻略》所記,宋高宗名諱“構”延及的嫌名多達“遘、購、媾、篝、傋、冓、夠”等55個字,可謂前無古人,人們只能期盼皇帝能體恤民情,起個無論是讀音還是字形都罕見的名字。
與“避諱”的茁壯成長相比,政治隱語真正的嫡子哲嗣——“諷諫”卻日漸萎靡,一蹶不振。
在戰國時代,假如諷諫出格激怒了一位國君,游士至少還可以轉投他國;而競爭下的列國諸侯,即使是為了好賢養士的名聲也會容忍士人過分的話語。但普天之下的帝王卻不會輕易寬容不敬的行為,秦始皇“以古非今者族”的嚴令使膽敢借古人故事諷諫今日政事的士人膽戰心驚,當“大不敬”在漢代成為一項重罪時,諷諫就只能黯然退場了。
漢代的東方朔是最后一位在諷諫史上留下名字的臣僚,他之所以能全身而退也是因為他“時觀察顏色”,而漢武帝也只是把他當成一個倡優小丑之類蓄養。
“雍乾之際,避諱甚嚴”,再沒有哪個朝代比活在全盛時期的清代更讓人感到恐怖的了,避諱的地雷處處皆是,很多時候甚至莫名其妙。
康熙時代的文壇祭酒王士禎,死了已十年,卻因新即位的雍正皇帝名胤禛,所以被迫改成“王士正”,后來又被欽命改回“王士楨”;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變成了“趙匡允”,就連前明的崇禎皇帝都成了“崇正皇帝”。
諷諫也同樣遭受摧折,當乾隆皇帝的寵臣、被視為清代東方朔的紀曉嵐委婉地向皇帝勸諫東南財力竭盡懇請救濟時,得到的卻是皇帝的斥責:“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館,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這是一個開不起也開不得政治玩笑的時代,即使是倡優也不行。
“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文字何以成獄?
“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這是康雍年間的文士張貴勝編纂的笑話集《遣愁集》中收錄的故事里的一句話。這句話的背景是五代時期宰相馮道的一位門客在為馮道念《道德經》的首句“道可道,非常道”時,因為馮道的名字是“道”,而他的字又是“可道”,所以這位倒運的門客只得將所有的道,都改成“不敢說”。
像生活在康乾盛世的大多數文人一樣,談論古事或是嘲笑古人也許是為了滿足自己寫字癖比較保險的辦法,所以像張貴勝這樣從古書上將摘抄的古代名人軼事編輯成書出版,或許是再安全不過的了。但即使如此,也有可能背上借古諷今的罪名。
1787年,清代最大規模的文化工程《四庫全書》已經全部編纂完畢,進入復勘階段,但一位名叫祝堃的詳校官卻從一本品鑒歷代收藏畫作的小冊子《讀畫錄》中嗅到了可疑的氣息。
氣息來自于書中“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余”的詩句。這句詩在一般人看來沒有任何奇怪之處,不過是抒發一下作者周亮工追慕魏晉風度的情感,但在乾隆皇帝眼中,這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逆詩。所謂“義熙余”,乃是套用陶淵明一個相當冷僻的典故,義熙乃是東晉末年安帝的最后一個年號,據說陶淵明所著文章年月,在義熙之前,都用東晉年號,之后惟書甲子,不書劉宋年號。想那周亮工原是前明進士,后來入清為官,難保他不是借陶淵明的典故暗喻心懷前朝,于是周氏原先收入四庫的所有書籍全部抽出銷毀。
周算是這場康乾時期文化運動中的幸運兒,因為他死在一百多年前,倘使他活到乾隆時代,必定難逃誅戮族滅之災。在這場由皇帝親自策劃發動的文化清剿運動中,很少有人能夠逃脫成為漏網之魚。
清代帝王對隱藏在字里行間的政治隱語如此地窮追猛打,讓人誤以為是罹染了偏執狂或是迫害狂的心理疾病,但事實卻遠沒有如此簡單,皇帝真正的目的是希望能殺雞儆猴,制造一種集體恐慌,使人們不敢輕易玩弄文字,挑戰最高權威。
皇帝的苛察一個直接后果是促使人們進行自我審查,因為沒有人能料到皇帝究竟會對哪一個字哪一句話發生“興趣”,所以文人只能無限地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將一切都視為可能觸犯避諱的地雷,沒有什么比自我審查更能徹底地驅趕不安分的思想,也正是通過這種方法,避諱深深地根植于人們的頭腦中,并且成為頭腦中支配所有思考和書寫活動的深層潛意識。就像乾隆在一道諭旨中所說的那樣,“俾愚眾知所炯戒”,讓這些愚民引以為戒。
最安全的方法,就是管住那雙不安分的手和不老實的嘴,也許就像馮道門客那句名言才是最保險的:“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摘自《今參考·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