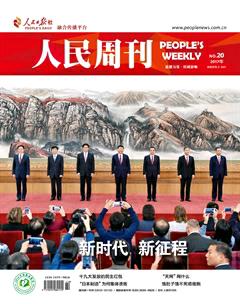通過原子看清生命的細節
付冰冰
隨著今年諾貝爾化學獎結果的塵埃落定,人們對生命科學的認知已經成功地從分子層面過渡到原子層面,對生命的本質又有了一個高分辨率的認知。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17年的諾貝爾化學獎授予雅克·杜邦內特、約阿希姆·弗蘭克,以及理查德·亨德森,以表彰他們“在開發用于溶液中生物分子高分辨率結構測定的冷凍電鏡技術方面的貢獻”。
這是一種呈現生物分子三維立體圖像的技術方法。使用冷凍電鏡技術,研究人員能夠將運動中的生物分子進行冷凍,并在原子層面上進行高分辨率成像。這項技術將生物化學帶入了一個嶄新時代。
“今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頒布后大家都覺得實至名歸。2010~2012年間,我曾在LMB工作,Richard是我們亦師亦友的朋友,他自己對拿不拿獎好像根本無所謂,倒是我們周圍的人一心盼著他拿諾獎。許多諾貝爾獎得主獲獎時都年紀很大早已退休了,但Richard在職期間就獲了諾獎,我們聽到這個消息后由衷的為他高興。”劍橋大學神經科學博士古春婧對本刊記者表示。
LMB:何以成為諾貝爾獎的“工廠”
分子生物學實驗室(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logy,LMB),是劍橋大學卡文迪許物理實驗室延伸出來的生物實驗室,如今是英國醫學委員會(MRC,Medical research council)旗下最重要的生命科學研究所。
“LMB是世界科學史上少有的一個非常成功的研究機構,被稱為諾貝爾獎的工廠。其成果包括DNA結構模型、蛋白質結構、基因測序等等,不光開創了分子生物學時代,而且推動了整個生命科學的發展。在LMB誕生的研究成果至今共有11項獲得了諾貝爾獎,作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基礎型科研的研究所,LMB基本上不做任何應用型科學研究。 ”
古春婧博士補充道:“這個實驗室在科學環境和管理上很特殊。這是一個精英管理的典型。20世紀40年代起,它的研究經費就充足到不需要實驗室內的研究人員考慮經費來源,每個實驗室的科研帶頭人都不需要自己申請自己的科研經費,而是由整個研究所整體申請核心經費,這樣所有研究人員可以把全部精力集中于科學研究。我在LMB工作的時候覺得這簡直是一個科研天堂,因為基本不用考慮經費的事情,因為資金充足,所以做實驗時事半功倍。”
基礎科研重于一切:淡泊名利造就匠心精神
“劍橋大學能走出這么多諾貝爾獎獲得者,并非偶然,這與體制是息息相關的。”
在古春婧博士看來,劍橋大學特別重視基礎科研的研發工作,絕大多數科研經費都撥給基礎科研。
“應用型的科研工作占比很小,也不是特別鼓勵和推崇。我博士后以后到劍橋大學技術轉化中心工作,專門負責劍橋大學商業轉化實驗室的知識產權工作。雖然每年我們都有很成功的商業轉化案例,但是技術商業化在劍橋大學的整體學術圈里并不是主流方向,也不會大力提倡。”
古春婧博士認為,所有高新技術、應用型的成果都建立在基礎科研上。基礎研究有成果了,商業轉化自然水到渠成,不能本末倒置。“我在 LMB工作的時候最大的感觸是這些科學家們對研究非常純粹,這種純粹表現在基本上和名利不掛鉤,很少有人利用自己的實驗室做橫向課題賺錢,做科研都有一種踏踏實實的匠心精神。”古春婧博士說。
跨界頒發諾貝爾化學獎:因開創性應用價值被認可
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包括物理學獎、化學獎和生物學獎。據資料顯示,自從1901年設立以來,百余年間,全世界范圍內共有近400位科學家在上述學科有重要發現和發明,為人類作出了卓越貢獻。
自1901年首次頒獎以來,諾貝爾化學獎被多次頒發給生物、生物化學、生物物理等領域,授予在這些領域對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的人。
這些成果在當時獲獎時大多都是基礎科研,在某項領域中起到開創性的作用,但當時并沒有直接的應用價值。“諾貝爾委員會以更高的標準更長的時間去驗證,到這些科學家獲獎可能需要好幾十年的時間。”古春婧博士強調。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成果被后來的科學家們進行進一步的研發工作,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人們對生命科學有了更進一步的認知,對相關領域有著快速推進的作用。
冷凍電鏡:解析疾病產生的導火索——膜蛋白
冷凍電鏡之所以能獲得諾貝爾獎是因為這項技術對生物化學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蛋白質結構的解析對于了解蛋白功能和設計藥物靶點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古春婧博士向本刊記者解釋道:“目前80%臨床使用藥物的靶點都集中在膜蛋白上。大多數藥物通過與膜蛋白結合而起作用,有的藥物活化膜蛋白,有的藥物使膜蛋白失活。”
絕大多數疾病都是由于某一特定的膜蛋白不足引起的。“盡管膜蛋白的作用非常重要,但膜蛋白結構卻非常難解析,原因是這些蛋白很難結晶,傳統的X射線晶體學方法無法對膜蛋白進行解析。”古春婧博士說。
“電子顯微鏡技術問世于1931年,但只適用于無生命樣品,因為電子顯微鏡需要在真空環境下工作,樣本中的水分需要被蒸發,加上其發射出破壞性的電子束都會破壞樣品中的生物分子。”古春婧博士補充道。
冷凍電鏡發明前:顯微鏡“進化”之路
1975~1986年,約阿希姆·弗蘭克發明出一種圖像處理方法,利用電子顯微鏡可以將模糊的二維圖像分析出來并以三維結構形式呈現出來,這種方法基于各個分散的全同顆粒(蛋白)的二維投影照片,經過對位平均分類,然后直接三維重構得到蛋白的三維結構,實現了無需結晶的蛋白質三維結構解析技術。
1982年,雅克·杜波內特讓使用電子顯微鏡觀測含水樣本成為可能。他成功將水溶液環境迅速冷卻轉變為玻璃態,將周圍的生物分子凍結,使生物分子能保持其天然結構狀態,以便于顯微鏡觀察。
1990年,理查德·亨德森在約阿希姆·弗蘭克的算法上提出實現原子分辨率冷凍電鏡技術的可行性,并成功的使用電子顯微鏡成功取得了蛋白質的三維結構原子級分辨率成像。
“到了2013年,電子顯微鏡的分辨率已經達到原子級別,給結構生物學領域帶來了一場完美的風暴,許多重要大型復合體及膜蛋白的原子分辨率結構,都一個個被迅速解析,其中也包括施一公博士、楊茂君博士的成果。如今,研究人員很輕松就能獲得生物分子的3D結構。這對設計藥物靶點上有著前所未有的幫助。”古春婧博士說。
放下“刻板偏見”:重新認識科學家們的“科學”生活
劍橋大學至今共有98位科技學獲得諾貝爾獎。當然,這些科研工作者并不是每天只有“兩點一線”的生活狀態,也有許多個人的興趣愛好,有的還特別專業。
“我認識的教授中就有很優秀的小提琴手、作曲師等等。他們對自己的科研極度認真,有極高的熱情。我在LMB做博士后的時候,從來都不是第一個來最后一個走的。”古春婧博士說:“如今在劍橋大學科研工作主力軍很多都是80后,他們跟傳統意義上刻板的科學家已經不再一樣,生活可以很豐富精彩。”
收起實驗器材,放下數據報告。科研之外的古春婧博士有著同樣多彩的生活,繁忙工作之余,彈得一曲肖邦是她,畫得一手好油畫是她,做得一手好飯菜也是她。今年四月,古春婧博士歷時一個月時間獨自穿越澳洲6000公里的無人區,路況復雜多變,這其中甚至包含一段長達2000多公里的沙漠無人區。巾幗紅顏綻放在異國異鄉,達成了無數須眉心向往之卻力所不及的人生經歷。
科學研究本來就是對未知領域的探索,或許正是基于這份勇敢與無畏,一代又一代的科學家們,一次又一次將人類文明推向嶄新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