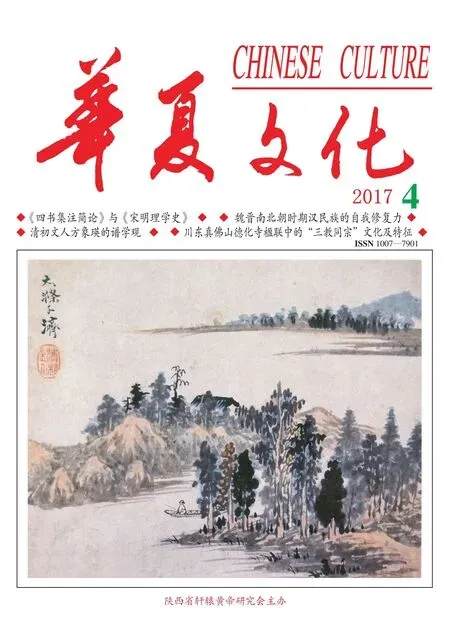試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學基礎
□王 巍
試析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學基礎
□王 巍

一、引言
西周時期,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就已經出現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如在《尚書》中就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周代的“天”已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必須以民意實之,演變為一種具象化的實體。“民為邦本”是《尚書》傳留下來的思想,成為“民本”思想的原始胚胎。在春秋時期,“民本”思想則表現為“德治”觀念,孔子對此有精辟的論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孔子注重禮樂教化,而禮的精神則在仁,正如孔子所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仁者的胸襟則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如此“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到了戰國時期,孟子提出“仁政”學說,區分了霸道與王道,積極提倡王道政治,反對霸道統治,并在《孟子·盡心下》中明確提出了“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孟子之后的先秦儒者如荀子,雖反對孟子性善論,但繼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說:“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荀子·正論》)。老子則講“慈、儉、不敢為天下先”,“損有余而補不足”,他厭惡專制君王對人民的剝削,圣人的境界應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圣人所立的榜樣應是“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道德經》第五十七章)。墨子也有類似的表述,只不過強調的重點不同,實施的方式也有差異。可見,自西周以來,“民本”思想一直為大多數思想家所繼承,成為先秦政治哲學的重要內容。
二、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學基礎
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是關注人民之“利”,重視人民的地位與價值,“保民而王,莫能御之也”。“民貴君輕”“重視民心”“問政于民”(政治維度),“制民之產”“輕徭薄賦”(經濟維度),“與民同樂”“保境安民”(社會維度),是孟子“民本”思想的核心內涵,而“性善論”“天命觀”“義利觀”則是孟子思想學說的價值命題,構成了孟子“民本”思想的哲學基礎。
(一)性善論
性善論不僅是孟子仁政學說的哲學基礎,也是孟子整個思想體系的哲學基礎。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在人的意識之中有先驗的善的萌芽(善性乃天所賦予),這是人之異于禽獸的本質特征。在人們心中有四種先驗的“善端”,即“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其中“惻隱之心”是最根本的(“仁”處于核心地位)。四心乃人們所共有,無論圣人還是一般人都是一樣的,這實際上承認了在人性層面人人平等。孟子為了論證人具有先天的善性提出了“良知良能”的概念,他說:“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孟子·盡心下》)當然,孟子認為只是在人的本性之中有善的萌芽,而不是說人生來就有完美的道德,每個人本性是善良的,但并不是說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其善性,發展自己的道德,順乎人性的本然。他說:“富歲,子弟多賴;兇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關于如何保存發展善性,擴充“善端”,孟子認為首先必須有向善的主觀愿望,其次通過“寡欲”和“養浩然之氣”兩種修身方法來實現。具體而言,孟子認為人的欲望越多,那么他的善性就越少,因此必須運用理智去減少欲望,克服外部世界和感受對心智的誘惑和干擾,即所謂的“養心莫善于寡欲”,主張通過思維的明辨來克制物欲以存善性,用理智來達到養心寡欲的目的,防止感官“蔽于物”而奪走善性。對于浩然之氣,孟子則認為就是人的主觀精神,是通過“集義”與“明道”培養出來的最偉大最剛強的氣。總而言之,由于性善具有普遍性,“先王”亦有“不忍人之心”,并能通過理智的思辨克制物欲,養心寡欲擴充自己的四端,發展自己的善性,然后“推恩”及民,行“不忍人之仁”,實施“王道”政治。這樣,孟子就把“仁政”的哲學與心理基礎歸結到人性之上,為“仁政”學說提供了合理依據。
(二)天命觀
孟子繼承與發展了孔子的天命觀,向天命觀注入了全新元素,給后世留下了嶄新命題,他的天命觀包含以下幾種含義:
1.天命即命運,承認命定論,將其看成是一種超驗的必然性,但同時也強調事在人為,注重發揮主體的積極性。他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梁惠王下》)自己不遇魯侯乃是命運決定的,是一種必然性。但同時,他又說:“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孟子·離婁下》)。又強調事在人為,反對自暴自棄。
2.天乃自然之天,并且是可以被認識的。他說:“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孟子·梁惠王上》)。“天之高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離婁下》)。天之“道”(規律)并非不可感知,而是可獲知、可體悟的。
3.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但同時強調人民的巨大作用。孟子在對堯舜禪讓的論述中說到天子傳位給下代不是由個人意志決定的,“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而是“天與之”,不過“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孟子·萬章上》)。新受任的“天子”如果能夠得到人民的擁戴,把國家治理好,就表明他的權力是“天”授予的,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這樣孟子就把民心看成是獲得政治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孟子引用《尚書》的話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甚至認為一切應以人民的意愿為準,天或天命可不在考慮之列。他對齊宣王說吞并燕國,如果燕國人民高興就去吞并,反之亦然。可見,雖然孟子是為“三王”作辯護(為堯、舜、禹帝位的傳承提供合理的依據),但對民心的重視,對人民主體地位的高揚這一點不容忽視。
根據以上“天命觀”的基本含義,再結合《孟子·萬章上》第六章中“益無法得天下”,以及伊尹、周公、孔子都無法得天下強調天命的必然性、不可違抗性,可以看出:一方面孟子強調天命不可違(客觀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強調遵從民意天命猶可違(主觀能動性)。從本質上看,“民心”“民意”構成了連接“天命”可違和不可違的價值紐帶,成為緩解“天命”可違和不可違內在張力的價值工具。
在天人關系上,孟子將天與人性合而為一。他認為天德寓于人性,人性與天是相通的,這樣就把仁、義、禮、智封建綱常倫理外化為天的法則,并提出了盡心、知性、知天的認識路線。他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人之“心”(思維能力)是天給予的,應該擴充、發現內心固有的“善端”,通過擴充心中的“善端”使自己的本性顯現出來(即仁、義、禮、智在人身上顯現),這就是盡其心而知其性。而天又與人性相通,即天也有與人的本性相通的“仁、義、禮、智”道德屬性,最后通過盡心知性就能夠“知天”。也就是說孟子的心性結構是:“仁、義、禮、智”根植于心(即心→性),具體表現為:天→心→性→天(天是心的形而上依據,心是性的基礎,而天德又寓于人性,天、心、性因此構成價值閉環)。同時,孟子強調認識是對自己內心和本性的探求,而不是從外物到感覺思維的過程(即從內→外而非外→內),通過“盡心”最終達到“知天”的目的(標志著認識的完成)。這表明他的認識論不僅注重“反求諸己”而且具有明顯的天人合一色彩,是對夏商以來天人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既然如此,每個人的認識路線大致相同,那么君主也不例外。君主也必須盡其心,努力擴充自己的善端而后知其性,使仁、義、禮、智在身上彰顯,而把這些擴充到政治上就體現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實施“王道”政治。
(三)義利觀
孟子的義利觀繼承了孔子重義輕利的思想,要求在處理義利關系時先義后利,義為重,利為輕。他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把義與利對立起來:只講利不講義就會引起爭奪,招致政權的顛覆;只講仁義不講利才能保證國家興旺。當利與義發生矛盾時,堅決要義而不要利,主張舍生取義。孟子一再反對言利,反對的本質是統治者的私利與貪欲。因為當時的大小統治者都在貪欲驅使下相互殺戮、爭權奪利,他們根本不顧及百姓利益和道德規范肆意妄為,這不但使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統治無法鞏固,而且也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所以,他反對當時統治階級過分追求私利不顧及百姓死活的做法,即反對“上下交征利”,而不是一般地反對言利。這在施政上表現為對人民給予一定的利益,減輕人民的負擔,改善和保障人民的生活,照顧人民的利益,主張“所欲與之聚之”“制民之產”“輕徭薄賦”,對統治階層則應該限制過分膨脹的私欲。敬民愛民、利民恤民在孟子看來已經成為緩和社會矛盾、推動社會整合的重要手段。
三、結語
在孟子“民本”思想中,肯定人民的價值與地位,提出“民貴君輕”,以人民的認同作為君主政治統治合法性的價值依據,反對犧牲人民的生命得天下,在一定程度上解構了至高無上的君權。雖然這與近代的民主觀念還存在一定差距,但卻為后世民主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可能的價值前提,尤其是作為孟子“民本”思想哲學基礎的“性善論”“天命觀”“義利觀”,為后世政治哲學的發展更是提供了豐富的價值資源。
(作者:四川省華鎣市中共華鎣市委黨校,郵編638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