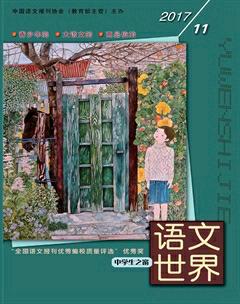歸來者北島:“我到處漂泊,永遠在失敗”
何可人
“讀者很少看我的《在天涯》。如果你明白它對我的意義的話——這么多年,我在到處漂泊。”
2016年7月2日,北京單向空間“文學之夜”,67歲的北島這樣形容自己的“去國之路”。
如今,漂泊者歸來。自從2012年中風以后,北島已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和開口。這一夜,北島卻仿佛打開了話匣子。曾留給當代文學史最具反抗姿態和獻身激情的詩人,如今已褪去時代賦予的英雄標簽,逐漸步入自己生命的老境,面目平靜,談吐緩慢。
盡管詩句被一代代人反復背誦,但他的生命經驗,卻被迫與中國隔絕多年。這一夜,歸來者北島,握著“時間的玫瑰”,徑直走向了自己的讀者,不再朦朧。
一
“像一顆彗星一樣”,這是詩人特朗斯特羅姆對人生的比喻。對北島而言,自己的人生星軌里最密集的頭部,是二十多歲的時光。那是一個可以為了一本書跑遍全城、可以為了一個想法爭得面紅耳赤的年代。20歲的北島成為建筑工人,進行地下寫作,搞翻譯,換工作,最后成為自由職業者。
20世紀80年代末,中年北島開始漂泊海外,編《今天》,寫作,教書。在散文集《藍房子》中,北島曾記敘了他和艾倫·金斯堡一起在詩歌節上朗誦的縱情片段,這樣短暫歡樂的時光,北島在當晚的講述中甚少提及。相反,隨著回憶的深入,陳年瑣碎的艱難和窘迫成為敘述的主體:迫于壓力寫散文,任職加州大學分校東亞系客座教授卻被“炒魷魚”,不斷搬家遷移,困難地學習外語……“永遠的失敗,不斷的失敗,我永遠在失敗,然后走向了滅亡。”北島說,然而,“那也無所謂了”。
1989年到1993年的四年間,北島在六個國家居住過。輾轉挪威、丹麥、瑞典時,北島想得更多的是自己能否過下去。“最難的是在北歐。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地方,當地的小語種,他們的日常生活……我在挪威待了三個月,在斯德哥爾摩待了八九個月,在丹麥待了兩年,這兩三年可以說是根本性地對自己的挑戰。我已經不是一個詩人,我只是一個普通人,能不能過下去?那時候家里人都不能來往。我一個人單獨生活,太難了。那時候,周圍都是富裕的人,而我是一個流浪者。”
北島口中的“流浪”,并不只是指經濟上的壓力,而多是自己身處的語境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這也是詩作《鄉音》創作的背景。
二
“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漂泊中不能用英語熟練寫作的北島,依然堅持對看不見的漢語讀者書寫“中國的經驗”。這是一種帶有悲劇意味的狀況:國內的讀者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不能讀到他,而他的“中國經驗”,也逐漸褪色、泛白。
帶著這樣的焦灼,北島在2007年輾轉到了香港,一生中終于有了自己的書房。他在香港中文大學出任教職,每年開授詩歌創作課程,創辦香港國際詩歌節。在香港推動詩歌活動,北島曾將其比喻為在水泥地上種花,“很長時間內,香港從未出過一本像樣的詩集。那我就要挑戰,我一定要把這個國際詩歌節做成”。從2011年開始,香港國際詩歌節堅持每一本詩集都以中英雙語出版。
2009年,北島60歲,決定寫作長詩《歧路行》。北島這樣解釋詩名:“歧路行,我永遠在迷路。我個人的命運和當代史,有一種類似對話的關系。我經歷過這些年,見過的詩人們、朋友們,還包括一些小人物……我覺得對于這么一段歷史,我一定要有個交代。”
北島將長詩《歧路行》的寫作視為挑戰。此前,北島只寫短詩,《白日夢》是個特例。北島笑著對讀者說:“你們還在朗誦《回答》《一切》,其實我需要自我證明,我還在寫作啊!我希望自己能70歲之前寫出來,要給自己一個生日禮物。70歲以后就真的退休了。”
三
長詩寫到500行,忽然被中風打斷。病發的4月8日,成為北島此后每年都紀念的歷劫日。
北島的朋友蔣一談,當晚講述了詩人病后的幾個片段。2016年4月8日,蔣一談和北島相約吃了一頓餃子。席間,北島用異于平時的眼神問:“一談,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嗎?今天是我中風的紀念日。”
2012年4月8日,北島陪家人劃船,他感覺船晃得厲害。上岸后,他的步子甚至不能成一條直線。在去往醫院的途中,人就已經昏迷了。
一生以寫作為事業的北島,在步入生命的老年時,驟然失去對文字和語言的控制能力。一段時期內他很少和人交談,也無法寫作。“我說話磕磕絆絆,朗誦一首詩,需要反復讀很多遍。”病情最嚴重的時候,北島需要由女兒陪著看圖識字,每天看一個小時的電視節目,進行語言認知訓練。“我變成了一個孩子,這是很大的挑戰。”
北島下決心一定要把病治好,把長詩寫完。為了盡快康復,他跑了五個城市,找了六七個大夫,努力嘗試西醫、中醫各種治療方法:針灸、電擊……有次蔣一談去看望北島,發現詩人一臉疲憊。北島說自己剛用了電擊療法,給四肢通上電——“我想用這種方法刺激我的神經,我希望我的語言能力能加速地‘重新發育”。蔣一談感慨,詩歌,是北島身體里最大的語言動力。
去年開始,北島的語言能力起色明顯,他開始重新寫作。演講的時候,北島幾度為自己語言的遲緩向讀者道歉。但他同時也引用了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的句子:“語言是與劊子手步調一致的,因而我們必須找到新的語言。”他對在座的讀者說:“我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遭遇了不同的問題。在座的朋友們,年輕的朋友們,你們也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我覺得這個時代,也面臨著很大的問題。你們要找到一個新的語言,找到一種新的可能性。”
(選摘自“鳳凰網”,有刪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