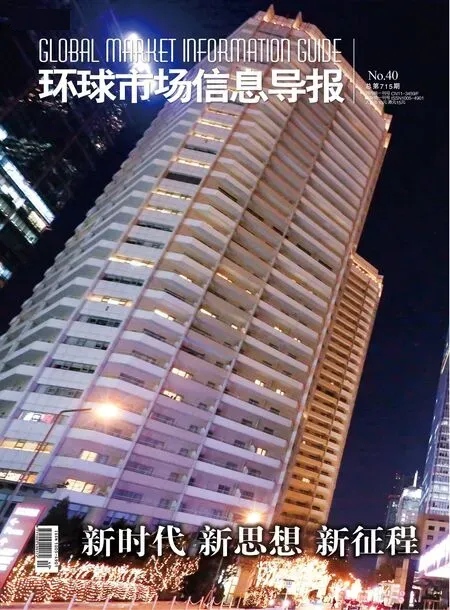特朗普熱衷“退群”背后
特朗普熱衷“退群”背后
10月12日,美國國務院宣布美國決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為何會在此時下定決心退出教科文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為一個教育文化機構,因何會在全球媒體引發軒然大波?
2017年10月12日,美國宣布決定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于明年正式生效。這是美國繼1984年后第二次退出這一聯合國機構。
分析人士認為,美國選擇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選舉之際宣布退出有多重考量,但退出并不意味著美國在該組織的影響力也隨之消失。
“深切遺憾”
當天,巴黎教科文組織總部前,各執委所在國的旗幟飄揚,其中包括美國國旗。不少得知消息的記者和游客紛紛在美國國旗下拍照留念。
在教科文組織執行局會議召開期間和下屆總干事換屆選舉投票最激烈的時候,美國退出的消息讓教科文組織總部大樓里充滿了失望的情緒。
會議廳前,剛結束會議的各國代表私下討論的大多是關于美國退出的新聞。現任總干事博科娃從會場走出,步履匆匆,臉上表情復雜。
博科娃12日下午發表長篇聲明,對美方的決定表示“深切遺憾”,認為這既是聯合國大家庭的損失也是國際多邊主義的損失。
博科娃說,與暴力極端主義斗爭需要努力促進教育和文化對話,十分遺憾在此時美國退出了負責這一斗爭的聯合國機構。全球各地沖突仍在肆虐,撕裂社會,十分遺憾在此時美國退出了負責推廣教育、促進和平與文化保護的聯合國機構。
博科娃還特別提到了教科文組織憲章開篇引用的美國詩人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的名言:“戰爭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務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衛和平之屏障。”這句話現在仍被鐫刻在教科文組織院內的石碑上。法國外交部12日發表公告說,國際社會的支持對教科文組織十分關鍵,法國對此時美國宣布退出該組織的決定表示“遺憾”。
美國《今日美國報》說,退出教科文組織顯示出特朗普政府對聯合國一貫秉持的懷疑態度。鑒于今年6月美國已宣布退出旨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美國外交學會會長理查德·哈斯在推特上發文稱:“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終于有了主題:‘退出’理論。”
為何退出
美國國務院12日發表聲明稱,美國決定退出的主要原因包括不斷增加的欠費、教科文組織需要根本性改革及對該組織“針對以色列的持續偏見”的關切。
1984年,美國政府曾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存在腐敗和管理混亂等問題為由,宣布退出該組織,但在2003年又重新加入。截至目前,美國中止向該組織繳納會費已有6年,欠費超過5億美元。
美國《外交政策》雜志認為,美國此次“退會”部分原因是為了消解拖欠巨額會費的壓力。
但有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兩次退出的背后都有一個不能明說的真正原因:與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不同,美國在教科文組織無法完全掌控局面。巴以問題就是一個例子。
教科文組織2011年接納巴勒斯坦為會員國,美國和以色列對此表示不滿,隨后停止繳納會費。美國稱,美國國內相關法律禁止向那些在巴以達成和平協議前就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家地位的聯合國機構提供經費。
今年5月,教科文組織不僅投票通過一項有關耶路撒冷的決議,稱以色列是“占領國”,還在7月將位于巴勒斯坦約旦河西岸的希伯倫老城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在美國宣布退出教科文組織后,以色列總理辦公室12日晚發表聲明說,以色列贊賞美國的決定,并已著手準備與美國同時退出該組織。
后續影響
據法國媒體披露,實際上早在今年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特朗普就向法國總統馬克龍透露了美國打算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信息。據說雙方當時達成協議,美方將在教科文組織總干事選舉結束之后再宣布退出。
教科文組織執行局12日就下屆總干事提名人選進行了第四輪投票。分別來自卡塔
分析人士認為,美國在教科文組織總干事即將誕生前夕宣布退出將對選舉結果產生微妙影響。爾、法國和埃及的三名候選人得票接近,他們將等待13日的最后一輪角逐,誰都有可能最終勝出。

而美國此時宣布退出明顯是在施壓,不希望繼續出現“對以色列有持續偏見”的候選人。
美國退出后是否就會對教科文組織失去影響力?分析人士認為,并不是這么簡單。過去幾年,即便美國因為拒交會費而失去了在該組織的投票權,卻仍擁有執委席位,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長期在教科文組織工作的內部人士認為,美國退出后仍會通過代理人和伙伴國家,或者以民間組織參與教科文組織活動的方式來發揮影響力,美國不會輕易放棄在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組織中發揮作用。
對于美國拖欠的巨額會費,分析人士認為,除非美國國內法律修改或巴以局勢發生變化,否則美國將會無限期拖欠,而這可能對教科文組織的運轉造成不利影響。
會費背后的美歐派系之爭
此次美國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方理由其一是認為其管理混亂,因此“該組織迫切需要改革”。而社會輿論多以為美國自2011年起便一直拖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會費,至今已達5億美金之巨,此時退會與賴賬無異,定然是特朗普節省經費,財政止血的考慮。
其實拖欠教科文組織會費者并非美國一家,不但以色列早在2011年便與美同步,以教科文組織偏袒巴勒斯坦為由拒繳會費,作為美國盟友的日本、英國也向來對會費繳納不甚積極,如果說近來日本的有意拖延在于讓教科文組織在慰安婦問題上做出讓步,而與教科文組織當下并無恩怨的英國亦有意為難,可見原因絕非一時決策分歧那么簡單。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其1946年11月4日正式成立以來,其總部一直設在法國巴黎豐特努瓦廣場(Place de Fontenoy)。長期身處法國政治中心,深受法國政治文化傳統影響的教科文組織,從其誕生以來可謂一直處于法國政府羽翼之下。
自印度支那戰爭以后,深感國力下降的法國歷屆政府面對美蘇爭霸的冷戰態勢,開始尋求“軟實力”維持法國的國際影響力,并以法蘭西文化輸出為主要的應對途徑,以求達到四兩撥千斤的效果。因此,處身巴黎的教科文組織便成了極為理想的文化宣傳工具。

與其他聯合國旗下機構駐地不同,法國非但從未怠慢教科文組織的會費義務(如聯合國理論上的最高機構聯合國大會處所,“聯合國總部大廈”所在地——美國便拖欠聯合國大會會費多年),還始終不渝地支持其發展,以至于法國市井流傳著這樣一個說法:“法國的教科文(UNESCO de la France)”,幾乎將其視為等同于法國政府教育部的存在(美國務卿將退出教科文組織的方案預先告知法國總統馬克龍,而非直接通告其總干事負責人,也正是這一現狀的體現)。
事實上,歷屆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也往往選擇有意傾向法國,特別是配合法國政府的教育文宣工作,幾乎成了傳播法國思想文化的急先鋒。
現任總干事伊蓮娜·博科娃女士便往往以討好法國社會輿論的形象面世,并且在聯合國議程中堅持以法語、英語兩種語言先后發言,可以說是把法國視為教科文組織的“母國”。而在法國影響力極大的歐洲合作組織(歐共體——歐盟)逐漸形成后,教科文組織也隨之成為了歐陸價值觀的傳聲筒,這使美英主導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圈極為不適(1984年美國退出教科文組織時,英國撒切爾政府也正因預算問題與歐共體發生激烈爭端,并于次年退出,這種“巧合”耐人尋味)。
在這種以歐陸文明價值觀為主的導向影響下,教科文組織往往違逆美國等大國的意志,在法國政府支持下,以特立獨行的態度政策應對問題;此外,由于該組織深受法國社會影響,往往主動將法國社會(尤其是巴黎)輿論、民眾趨向與價值判斷視為當務之急。
甚至有時會有意觸碰敏感問題,通過自己聯合國機構的這一平臺作用將一些教育文化上的事務放大為國際事件。2011年巴勒斯坦的教科文組織成員國身份事件便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特朗普“退群”梳理
退出這些國際性組織或全球協議,美國總統特朗普只有一個理由:它們“沒用”,甚至“擋了美國的道”。
一系列退出行動,勾勒出“特朗普主義”的部分輪廓。新官上任“三把火”,特朗普第一把火就燒到了TPP。
當地時間1月23日中午,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上任后的第一份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國退出跨太平洋貿易伙伴協定(TPP)。
早在競選期間,特朗普就表示,TPP是美國的一個潛在威脅,將“摧毀”美國制造業,并承諾當選后不再簽署大型區域貿易協定。
熟悉美國政壇的人大概了解,特朗普與前總統奧巴馬意見相左。TPP曾是前總統奧巴馬力推的一項計劃。當年,這一舉措被美國媒體解讀為,美國“轉向亞洲”戰略的支點。
遺憾的是,奧巴馬在任期間該計劃并未得到落實。12個成員國,歷時5年談判,在2016年2月簽署協議文本后,在特朗普的影響下一度停滯。
特朗普看來,退出TPP對美國工人來說才是件“大好事”。
為了展開公平的雙邊貿易協定談判,讓工作和工業重返美國,特朗普還決定放棄已有23年歷史的北美自貿協定,轉而注重雙邊貿易協定談判。TPP和北美自貿協定與經貿直接關聯,說“把我們國家……置于一個非常大的經濟劣勢”,還勉強說得通。但退出《巴黎協定》和科教文組織則更令人擔憂。
《巴黎協定》是由195個國家簽署,147個國家已正式批準的文件,旨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但對特朗普來說,想退出總有理由。特朗普表示,《巴黎協定》可能使美國失去多達270萬個就業崗位。
批評者的觀點認為,特朗普的理由站不住腳,因為清潔能源產業,包括太陽能和風力發電,在美國創造的新就業崗位超過煤炭行業的雇傭人數。
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應該和美國就業關系不大,特朗普卻也決定退出。毫無疑問,這一系列“退出”行動,會讓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形象大打折扣。
小伙伴力勸
特朗普逆勢而動,很多小伙伴有些“不高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各自豎“墻”的行為不能不稱為退步。
特朗普退出TPP對美國是否利好,現在還難以判斷,但顯然日本已經“不高興”了。在此之前,日本安倍政府期望TPP能幫助加速其長期承諾的結構改革,促進貿易和投資,實現經濟強勁增長。除了日本,TPP成員國中的新加坡、越南、澳大利亞等也透露了對美國退出后的擔憂。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特朗普政府的貿易政策,將削弱美國的競爭力,并可能導致美國與其他國家貿易摩擦增加。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則警告說,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風險將威脅全球經濟增長。
此外,重啟北美自貿協定談判,情形也并不樂觀。據外媒10月11日報道,墨西哥外交部長維德加里表示,廢除現行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能意味著美墨關系的崩潰。
對于特朗普總統而言,即便其有100個理由退出《巴黎協定》,也同樣有100個理由留在《巴黎協定》。退出《巴黎協定》將損害美歐關系,也將削弱美國全球領導地位。
歐洲一直是氣候變化的積極推動者,希望掌控氣候變化的主導權。特朗普訪問歐洲期間,很多歐洲領導人都勸說特朗普總統不要退出《巴黎協定》,這份盟友情,特朗普卻視而不見。
外交學院國際安全研究中心秘書長凌勝利分析認為,對于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而言,多邊主義是重要基礎。特朗普過于追求“美國優先”而淪落為毫無顧忌的自私自利,將削弱美國對多邊主義的參與,將有損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對于美國這樣的全球大國而言,絕不能只算經濟賬而不算權力賬。退出《巴黎協定》或許會減少一些美國企業的負擔,但也同時削弱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力。
中國成“穩定器”
特朗普一路“退退退”,人們不禁問,這是否意味著“退出主義”成為美政策主旋律?又將產生什么影響?
央視特約評論員蘇曉暉撰文指出,從美對TPP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政策中可以看出,特朗普正在加快貿易模式的轉變。特朗普認為美在雙邊協定中容易占據優勢,試圖以雙邊協議和地區化協議取代多邊協議。
退出《巴黎協定》則反映出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目標。特朗普在當選前就多次聲稱氣候變化是“騙局”,其能源政策旨在擴大國內化石能源的開采和生產規模。為落實《巴黎協定》自主貢獻承諾而設計的減排和清潔能源發展計劃成為特朗普落實目標的障礙,移除這些障礙成為必然選擇。
而針對伊核協議發難和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均展現特朗普政府正在調整中東政策,拉近與以色列關系,加強對伊朗的壓制。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認為,“美國退出TPP對中國來講也不完全是大好事,未來將面臨許多挑戰。”他指出,原來的TPP國家對中國的訴求會不斷加大,除了提升中國的貿易話語權,也增加了中國在全球在貿易體系中的責任與負擔。
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教授盛斌認為,中國可以成為全球化的“穩定器”,當然,這需要中國做一些角色轉換。
中國過去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為全球經濟治理改革與創新確立了新的坐標。近年來在發展新經濟方面的經驗,比如自主創新、互聯網、電商、綠色金融等,也為全球治理創新提供了新的思路與經驗。
從北京APEC到杭州G20,從達沃斯論壇到廈門金磚會晤,在世界舞臺上,更多中國理念、中國方案正在得到世界的廣泛認同。
在今年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國家主席習近平以“大海”妙喻經濟全球化。他指出,“世界經濟的大海,你要還是不要,都在那兒,是回避不了的。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