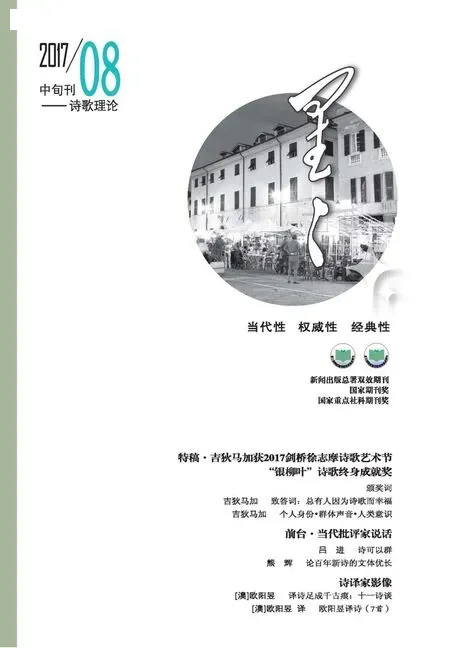聆聽生命
——你往何處去?
錢 剛
聆聽生命
——你往何處去?
錢 剛
本期三首詩屬于聆聽內(nèi)心和感悟生命的作品,伴隨著這種聆聽和感悟,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感傷與困惑,有的屬于生命底色,有的只是一時之感,“往何處去”的問題對于每個人意味著不同的答案。
余真的詩一貫纖細(xì)敏感,充滿著警惕、質(zhì)疑乃至絕望感。詩人的世界隨時破碎,悲觀才能讓人安全,純真過于虛假,樂觀則屬自投羅網(wǎng)。詩中的自我形象永遠(yuǎn)處于弱勢,甚至軟弱到不足以對世界報以敵意。這首《動搖》讓人讀到生之絕望,陣陣抽泣來自平靜的河底,這很能說明詩人的天賦,洞悉幽微,直覺精準(zhǔn)。第一句如咽喉之梗,一下堵住了我們的解讀之路,它像句悖論,一切的自由與遼闊仿佛觸手可及,但是……路卻自己斷了,成為自由和未來的斷頭路,暗示了悖論式的生存悲劇和荒謬之境。
秦嶺、密西西比河和死海在地理分布上相距甚遠(yuǎn),在詩里串成大雁的飛行路線,完成了碎片式拼貼。死海邊的母豹產(chǎn)子,繁衍生生不息的暴力,草原兒女——羊群永遠(yuǎn)被傷害和毀滅,這種宿命的悲劇充滿壓迫感。詩人將大雁設(shè)為“路過”,則顯示了其極度渴望逃逸的深層次心理。河岸廣闊而無路可逃,代表真正自由、輕盈的蘆葦和風(fēng)缺席,生命的恍惚包含無法脫釋的惶惑與驚憂,而生命的經(jīng)驗無法輕盈起來,無法跳脫出去,導(dǎo)致詩人無法分清自我,最后注定無法升華成對生命的敬畏,對生命意義的通透把握,這既是悲觀,也是反思。余真的悲觀有特殊性,它深存于幻象中,暗示生命經(jīng)歷現(xiàn)實的虛假可能后,意義和自由最終會撲空。這種終極悲觀陷入死循環(huán),反復(fù)念叨咒語——自由皆幻象,生命皆幻象……在詩人看來,自由的宿命就是自我否定的不自由,此刻難逃,未來難逃,一生難逃。細(xì)膩得密不透風(fēng)的不安全感、脆弱感通過詩歌的每個毛孔散發(fā)出來,恐懼與悲觀被悶在鐵屋子里,死死掐住讀者的咽喉。
代薇的《停頓》由“我記得”貫穿,從可感的身體到飄渺的火車,再到“你的眼睛”,最后到彼此感應(yīng)的“傷口”,結(jié)構(gòu)整齊,內(nèi)在句子卻連接松散,利落多變,加之漂亮的蒙太奇剪接,意象雖舊,但有老樹新芽的質(zhì)感。
這首詩的微修辭值得注意。第一個“我記得”中,金屬的堅硬對比肉體的柔軟,冰冷對應(yīng)體溫漸失,彎曲暗合內(nèi)心傷痛,它的冰冷沉默還暗合著夜晚的冰涼無言,對應(yīng)著哼哼唧唧的唱片,這些意象相互指涉,使意蘊微妙豐厚,夜晚與身體越發(fā)頹蕩。詩人見好就收,馬上關(guān)停這種久讀則生厭的場景,跳到第二個“我記得”。這次直接表明心跡——無能的力量,恰似那句“人的一切痛苦,本質(zhì)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執(zhí)迷又無能,進(jìn)而痛徹心扉,像移動的火車,一去不返地前進(jìn)。時間空間雖然前行,但車廂本身不為所動,似漂移懸浮,陷入自我的漫長停頓,同時也陷入漫長的無能和漫長的痛苦。火車意象表達(dá)犀利,如神來之筆。第三個“我記得”中,詩人重回至可感的身體,用喻新奇貼切,構(gòu)成了內(nèi)在節(jié)奏,不僅從身體出發(fā),回歸到身體,情感表露也越發(fā)直接和深切,形成情感勢能,最后的用喻一錘定音,耐人咀嚼。
窗戶的《身體里漸漸有木質(zhì)的東西》樸素馨香,讀詩感覺像聞到木匠的刨花香。它有著清晰明白的象征含義和情感表達(dá),這種“木質(zhì)的東西”是詩人精心選擇的意象,富于韌性,有厚重感,又具清新之美,如同詩尾揭示的大白話:“時光不能奪其芬芳/還會令其越久越堅硬”。詩人從一而終,將此意象用深用透,值得從修辭層面上細(xì)加體會。
木質(zhì)的東西在這里已是第一重意象,詩人又進(jìn)一步將其喻為皺紋和水紋,猶如意象的繁衍分叉,構(gòu)成二級意象與象征義,使得這首詩的意蘊更具層次感,形成了相對復(fù)雜的意義指涉。但同時,詩人沒有將象征物徹底實化,而是用了相對抽象的指稱——“木質(zhì)的東西”,讓意象擴(kuò)散而有了幽微感,無所不在又帶有不確定性,像在生命中尋找已得的對應(yīng)之物,有著更大的契合性與包容性,這是詩人在技巧上帶給我們的小小啟示。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