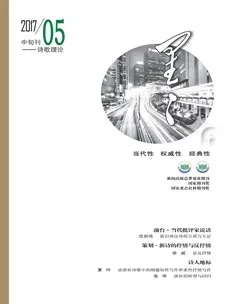論反抒情
“詩(shī)言志”到“詩(shī)緣情”,中國(guó)詩(shī)歌自古重抒情,甚至于認(rèn)為,詩(shī)無(wú)情而不立。“詩(shī)”與“非詩(shī)”的界限全在于“情”——“有情”則為“詩(shī)”,“人之所以靈者,情也。情之所以通者,言也。其或情之深,思之遠(yuǎn),郁積乎中。不可以言盡者,則發(fā)為詩(shī)”[1];“無(wú)情”則“非詩(shī)”也,“夫詩(shī)者,本發(fā)其喜怒哀樂(lè)之情,如使人讀之無(wú)所感動(dòng),非詩(shī)也”[2]。于是乎,抒情成為了中國(guó)詩(shī)歌最為重要的一種傳統(tǒng)。陳世驤先生說(shuō)“中國(guó)文學(xué)的榮耀并不在史詩(shī);它的光榮在別處,在抒情的傳統(tǒng)里”、“中國(guó)文學(xué)的道統(tǒng)是一種抒情的道統(tǒng)”[3]。這種傳統(tǒng)/道統(tǒng)從古典詩(shī)詞到現(xiàn)代新詩(shī),仍在延續(xù)著。周作人在評(píng)判現(xiàn)代新詩(shī)時(shí)認(rèn)為,“新詩(shī)的手法,我不很佩服白描,也不喜歡嘮叨的敘事,不必說(shuō)嘮叨的說(shuō)理,我只認(rèn)抒情是詩(shī)的本分。”[4]但是,我們也要意識(shí)到,抒情并非是一成不變的[5]。一時(shí)代有一時(shí)代之抒情,戴望舒在《詩(shī)論零扎》里提出“新詩(shī)最重要的是詩(shī)情上的nuance而不是字句上的nuance(法文:變異)”[6],其意即在此。除此之外,我們更應(yīng)當(dāng)注意到的是,除卻“詩(shī)情”(內(nèi)容)的變化,“如何抒情”(方式)也在不斷地嬗變,即一時(shí)代亦有一時(shí)代抒情之方式。在當(dāng)代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中,“反抒情”也成為了一種重要的抒情方式。
一
“反,覆也”,它往往意味著對(duì)立、抵抗、顛覆、叛離與解構(gòu)。在當(dāng)代文學(xué)批評(píng)術(shù)語(yǔ)之中,“反”有著相當(dāng)重要的美學(xué)意蘊(yùn),“文化”與“反文化”、“英雄”與“反英雄”、“神話”與“反神話”、“抒情”與“反抒情”等,它們都以一種二元對(duì)立的邏輯思維,作為我們批評(píng)、闡釋的重要路徑,進(jìn)入到批評(píng)的話語(yǔ)譜系當(dāng)中。當(dāng)我們說(shuō)“反”的時(shí)候,必然就存在了一個(gè)被“反”的對(duì)象。藝術(shù)的創(chuàng)新往往就在于“反”之中——當(dāng)絕大部分的人以相似的方式在創(chuàng)作時(shí),總會(huì)有另一小部分人選擇不一樣的或者相反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創(chuàng)作,而獨(dú)特性與創(chuàng)新性往往就產(chǎn)生于對(duì)秩序、對(duì)傳統(tǒng)、對(duì)同質(zhì)化、對(duì)大多數(shù)的反叛之中。譬如說(shuō),在政治抒情詩(shī)之后,詩(shī)人再次將目光聚焦于自身,抒發(fā)屬于自己的個(gè)人情感;在人人都在以抒情的方式在抒情之時(shí),有人則借用“反抒情”而抒情;在抒情泛濫成災(zāi)之時(shí),有人發(fā)出“拒絕抒情”的聲音:“詩(shī)不言志,不抒情”[7]。因此,我們談?wù)摲词闱椋冀K應(yīng)當(dāng)將其放置在具體的時(shí)代語(yǔ)境中展開(kāi),它總是與它所要“反”的對(duì)象,即一時(shí)代之抒情緊密相連。
張松建在《抒情之外:論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論中的“反抒情主義”》一文中,詳盡分析抒情與反抒情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復(fù)雜關(guān)系,認(rèn)為“抒情主義與反抒情主義構(gòu)成了中國(guó)新詩(shī)理論的內(nèi)在張力”,并提出“抒情主義與反抒情主義的沖突實(shí)質(zhì)上不是‘對(duì)與錯(cuò)’的沖突而是‘對(duì)與對(duì)’的沖突”[8]。以我看來(lái),這種“對(duì)與對(duì)”的沖突性質(zhì)同樣可以用來(lái)描述當(dāng)代詩(shī)歌中反抒情與抒情之間的關(guān)系。
1979年北島《回答》的發(fā)表,正式拉開(kāi)了朦朧詩(shī)革命的帷幕。在這首作品中,詩(shī)歌的抒情主體不再是紅色詩(shī)篇中宏大而寬泛的“人民”與“我們”,而是一個(gè)鮮明、冷峻、決yhS5gb+Jbb7TdsNtSjShH9cuu12lKGDn1fNX8OBds+k=絕的“我”: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zhàn)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lán)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mèng)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wú)報(bào)應(yīng)。
一個(gè)又一個(gè)“我”的出現(xiàn),飽含著詩(shī)人對(duì)世界的懷疑、對(duì)時(shí)代的憤懣以及詩(shī)人敢于獻(xiàn)身抗?fàn)幍挠⑿蹥飧拧T谶@里,“我”的回歸,讓詩(shī)情飽滿而有力。朦朧詩(shī)的出場(chǎng)顯然是對(duì)五六十年代政治抒情詩(shī)的一種“反叛”,讓抒情主題由“我們”回歸到一個(gè)具體的、內(nèi)在的“我”。然而,很快地,“第三代”詩(shī)人又舉起了反叛朦朧詩(shī)的大旗,甚至提出 “PASS北島”的口號(hào)。朦朧詩(shī)努力呈現(xiàn)內(nèi)在的“我思”與“我感”,“第三代”詩(shī)人則將日常生活移至詩(shī)中;朦朧詩(shī)在紛繁的意象中傳達(dá)情緒,“第三代”詩(shī)人則在口語(yǔ)中呈現(xiàn)世界;朦朧詩(shī)對(duì)崇高、對(duì)英雄、對(duì)世界抱有極大的書(shū)寫(xiě)熱情,“第三代”詩(shī)人則反崇高、反英雄、反抒情,在凡俗與丑陋中挖掘詩(shī)歌新的生命力。概而言之,“‘第三代’既在告別朦朧詩(shī)的內(nèi)容,也在告別朦朧詩(shī)的形式,他們是在意味與形式的雙向破壞中創(chuàng)造著自己的詩(shī)美學(xué)。”[9]
從朦朧詩(shī)到“第三代”,我們清楚地看到,當(dāng)代詩(shī)歌一次次的反叛與突破。從抒情的角度來(lái)說(shuō),朦朧詩(shī)人在是詩(shī)歌中有著強(qiáng)烈的主動(dòng)的抒情意識(shí),作品中的情感飽滿、熾熱且明確。北島寫(xiě)下“我不相信”(《回答》),寫(xiě)下“即使明天早上/槍口和血淋淋的太陽(yáng)/讓我交出青春、自由和筆/我也決不會(huì)交出這個(gè)夜晚/我決不會(huì)交出你”(《雨夜》),寫(xiě)下“在沒(méi)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個(gè)人。”(《宣告——獻(xiàn)給遇羅克》)。舒婷深情高呼“那就從我的血肉之軀上/去取得你的富饒,你的榮光,你的自由/—— 祖國(guó)啊/我親愛(ài)的祖國(guó)”(《祖國(guó)啊,我的祖國(guó)》),她向世界宣告“我必須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為樹(shù)的形象和你站立在一起”(《致橡樹(shù)》),她對(duì)同代人呼吁“為開(kāi)拓心靈的處女地/走入禁區(qū),也許——/就在那里犧牲/留下歪歪斜斜的腳印/給后來(lái)者/簽署通行證”(《獻(xiàn)給我的同代人》)……在這些詩(shī)歌中,個(gè)體的“我”從“人民”、“人們”和“我們”等群體中突圍而出,成為新的抒情主體。
而在“第三代”詩(shī)歌中,這種熾熱的情感,這種充滿個(gè)性的“我”又迅速消失不見(jiàn)。面對(duì)同樣的事物,詩(shī)人的情感以及抒發(fā)情感的方式顯然都已大變——從熾熱到冰冷,從抒情到冷抒情,甚至反抒情。我們?cè)嚺e一例:同樣是書(shū)寫(xiě)大海,在舒婷那兒,詩(shī)人對(duì)大海的情感奔涌而出——“讓你的颶風(fēng)把我煉成你的歌喉/讓你的狂濤把我塑成你的性格/我絕不猶豫/絕不后退/絕不發(fā)抖”(《海濱晨曲》)。而在韓東的筆下,“你見(jiàn)過(guò)大海/你也想象過(guò)大海/你不情愿/讓大海給淹死/就是這樣/人人都這樣”(《你見(jiàn)過(guò)大海》);在尚仲敏眼中,“你看你看/無(wú)論如何得去見(jiàn)見(jiàn)海/見(jiàn)了海/這輩子也就/不想見(jiàn)其他東西了/其他東西就不是什么東西了”(《海》)。
在這具體的語(yǔ)境與具體的詩(shī)歌文本中,我們清晰地看到,當(dāng)代詩(shī)歌顯露出的抒情與反抒情二者巨大的差異。它并不是“對(duì)”“錯(cuò)”之別,而是詩(shī)歌理念與抒情策略的一種嬗變與突圍。抒情與反抒情的對(duì)立與轉(zhuǎn)變,在朦朧詩(shī)與“第三代”詩(shī)歌、在世紀(jì)末的知識(shí)分子的智性寫(xiě)作與民間詩(shī)歌立場(chǎng)的口語(yǔ)寫(xiě)作之爭(zhēng)中、在新世紀(jì)初期的“下半身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以及新世紀(jì)以來(lái)的網(wǎng)絡(luò)詩(shī)歌的出場(chǎng)與生成過(guò)程中都有出現(xiàn)。甚至于,每一次詩(shī)歌運(yùn)動(dòng)與變革,都必然地、或多或少地牽涉到抒什么樣的情、如何抒情的問(wèn)題。也就是說(shuō),反抒情既在內(nèi)容上,也在形式上,顯示出特定時(shí)間段里詩(shī)歌創(chuàng)作的新變與力量。
二
因而我們說(shuō),反抒情的背后實(shí)則隱含著一種新的詩(shī)歌理念,一種新的創(chuàng)作姿態(tài)。
朦朧詩(shī)以降,當(dāng)代詩(shī)歌創(chuàng)作在內(nèi)容與形式上變化愈來(lái)愈大,甚至出現(xiàn)了許多以“非詩(shī)歌”、“反詩(shī)歌”為詩(shī)的文本實(shí)驗(yàn)與探索。在這些“非詩(shī)”、“反詩(shī)”中,抒情消失不見(jiàn),取而代之的是反抒情姿態(tài)。從朦朧詩(shī)到告別優(yōu)雅的“第三代”,從追求思想深度與智性修辭的知識(shí)分子寫(xiě)作,到代表平民姿態(tài)、民間立場(chǎng)的口語(yǔ)化寫(xiě)作,每一次反抒情的提出,都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抒情的懷疑與反叛,都代表著一次當(dāng)代詩(shī)歌的新突圍。
1998年,詩(shī)人侯馬在題為《抒情導(dǎo)致一首詩(shī)的失敗》文章里寫(xiě)道:“詩(shī)歌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是絕對(duì)無(wú)用的。如果硬要說(shuō)有點(diǎn)用,應(yīng)該是指它能‘抒抒情’,但指望這一點(diǎn)是很危險(xiǎn)的,抒情導(dǎo)致一首詩(shī)的失敗,抒情產(chǎn)生一大批千篇一律、面目不清的詩(shī)作。如果一個(gè)人想抒情,他決定寫(xiě)一首詩(shī),我無(wú)法相信他能寫(xiě)出一首‘詩(shī)’,洋溢的情感通常掩蓋的是心靈的枯燥。”緊接著,他作出判斷:“如果你想把情抒了,在詩(shī)中‘反抒情’可能是必要的,也是唯一行得通的。”[10]在這里,侯馬對(duì)抒情的否定與對(duì)反抒情的高度認(rèn)可,直指當(dāng)時(shí)抒情泛濫、無(wú)力等病癥。同樣,2001年《詩(shī)潮》第5期刊發(fā)《當(dāng)代詩(shī)歌:抒情,還是反抒情?》研究專輯,其中輯錄徐江《善待詩(shī)歌,正視抒情》、世賓《詩(shī)歌是抒情的藝術(shù)》、沈奇《反對(duì)濫抒情》、謝有順《過(guò)度抒情是一種矯情》、于堅(jiān)《詩(shī)言體》[11]五篇探討抒情與反抒情的短文,其鋒芒同樣指向時(shí)代的濫化抒情傾向。在這些探討中,我們發(fā)現(xiàn),抒情與抒情傳統(tǒng)始終是詩(shī)歌寫(xiě)作者與研究者最為關(guān)注的核心問(wèn)題之一。徐江提出“反抒情也是一種抒情”;世賓呼吁應(yīng)當(dāng)警惕一種人為的抒情,即刻意的、生硬的抒情;沈奇認(rèn)為,從惟抒情到冷抒情到反抒情,這是現(xiàn)代詩(shī)必然發(fā)展過(guò)程,而反抒情能夠有效地對(duì)偽抒情進(jìn)行證偽;謝有順對(duì)迂腐的抒情提出批評(píng),指出應(yīng)當(dāng)書(shū)寫(xiě)內(nèi)心的真實(shí)情感;而于堅(jiān)則堅(jiān)持詩(shī)歌不是抒情言志的工具,而是有生命的、獨(dú)立的語(yǔ)體。凡此種種,我們看到,無(wú)論在何時(shí),抒情問(wèn)題仍是最受關(guān)注的問(wèn)題。
然而,我們也發(fā)現(xiàn),我們?cè)谛率兰o(jì)之初大部分人對(duì)于抒情的理解,實(shí)際上仍然沒(méi)有超脫出數(shù)十年前新詩(shī)始興之時(shí)現(xiàn)代詩(shī)人們對(duì)抒情的探討與爭(zhēng)論。比如,在1926年梁實(shí)秋就對(duì)抒情的尺度進(jìn)行批評(píng),認(rèn)為“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到處彌漫著抒情主義。……‘抒情主義’的自身并無(wú)什么壞處,我們要考察情感的質(zhì)是否純正,及其量是否有度”[12];宗白華說(shuō)“詩(shī)忌無(wú)病呻吟,但有病呻吟也還不是詩(shī)。詩(shī)要從病痛中提煉出意,味,聲,色,詩(shī)心與詩(shī)境。詩(shī)出于病痛,超脫于病痛。”[13]由此,我們不禁猜測(cè),詩(shī)歌在抒情與反抒情之中的重心遷移,是否是一個(gè)螺旋式或者回環(huán)式的發(fā)展過(guò)程?換而言之,現(xiàn)代新詩(shī)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在不同的時(shí)間段里總會(huì)發(fā)生關(guān)于抒情與反抒情的碰撞與爭(zhēng)論——情為詩(shī)之本,這被絕大多數(shù)的人所認(rèn)可,然而,論爭(zhēng)的關(guān)鍵在于如何抒情。抒情的方式在時(shí)間的長(zhǎng)河中不斷在變化。一方面,在詩(shī)情盡失時(shí)總有人在提醒大家,抒情才是詩(shī)歌的本分;另一方面,在抒情成為大多數(shù)之時(shí),或者說(shuō),在抒情泛濫無(wú)力之時(shí),又總會(huì)有人以反抒情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抒情。每一次從抒情到反抒情的變化,都是一次對(duì)多數(shù)的反叛與突破。詩(shī)人借反抒情向外界傳遞出自己的詩(shī)歌理念與創(chuàng)作姿態(tài),詩(shī)人也由此呈現(xiàn)出自己作為詩(shī)人的獨(dú)特價(jià)值。這樣的變化,自中國(guó)新詩(shī)出場(chǎng)以來(lái),一直持續(xù)到現(xiàn)在。并且,我也相信,只要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不死,詩(shī)人在抒情與反抒情之間側(cè)重何者的選擇也永遠(yuǎn)不會(huì)停止。
三
然而,僅僅看到反抒情作為一種理念的呈現(xiàn)是遠(yuǎn)遠(yuǎn)不夠的。我們還必須從書(shū)寫(xiě)策略的角度,看到反抒情同時(shí)還作為一種方法受到相當(dāng)多詩(shī)人的青睞。反抒情是當(dāng)代詩(shī)歌抒情的方式之一,它與敘事、戲劇性、零度情感、口語(yǔ)化等緊密相關(guān)。詩(shī)人或是在敘事中以戲劇性沖突完成一次講述;或者,詩(shī)人完全將自我從詩(shī)歌中抽離出來(lái),以零度情感完成冷靜的陳述;再或者,詩(shī)人在口語(yǔ)化風(fēng)格中完成對(duì)一現(xiàn)象的調(diào)侃或解構(gòu)……凡此種種,它們可以獨(dú)立運(yùn)用,也可以綜合在一起形成合力,都是以反抒情的方式抒情。
當(dāng)代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中,既有抒情傳統(tǒng),也有敘事傳統(tǒng)。陳世驤先生在論述中國(guó)古代小說(shuō)與戲曲時(shí)指出,在小說(shuō)與戲曲等敘事性作品中,打動(dòng)人心的仍然是抒情的力量:“……抒情體仍舊聲勢(shì)逼人,各路滲透,或者你可說(shuō)仍舊使戲劇小說(shuō)不能立足。元朝的小說(shuō),明朝的傳奇,甚至清朝的昆曲。試問(wèn),不是名家抒情詩(shī)品的堆砌,是什么?”[14]然而,在當(dāng)代詩(shī)歌創(chuàng)作之中,敘事業(yè)已成為情感抒發(fā)的重要途徑——用陳述、敘事的方式補(bǔ)充甚至替代傳統(tǒng)抒情方式中的直抒胸臆,同樣也能傳達(dá)詩(shī)人心中的情懷。敘事抒情與“我要……”、“我不……”、“我想……”等傳統(tǒng)抒情樣式相比較,它往往采用第三人稱視角,也就是說(shuō),詩(shī)人的情懷并不直接、明了地顯現(xiàn),因而,它的詩(shī)情顯地更加地冷靜,更加地內(nèi)斂,也更加地隱秘。同時(shí),敘事抒情使用第一人稱時(shí),“我”大多也是旁觀者,或者說(shuō)是零度情感主體。羅蘭·巴爾特在《寫(xiě)作的零度》中提出一種“零度的寫(xiě)作”,這種寫(xiě)作方式“根本上是一種直陳式寫(xiě)作”[15],作者在寫(xiě)作中不摻雜任何的個(gè)人想法與情緒,不介入小說(shuō)而以零度情感機(jī)械地描述事件。
詩(shī)人情感在敘事抒情中表面看來(lái)是缺席的、離場(chǎng)的,那么,詩(shī)歌所要呈現(xiàn)的情感從何處獲得力量?此刻,我們應(yīng)當(dāng)重視動(dòng)作性書(shū)寫(xiě)的力量。敘事抒情大多以行動(dòng)者(人)的動(dòng)作替代內(nèi)心的情感波動(dòng),以動(dòng)作指向傳遞詩(shī)情而非直接書(shū)寫(xiě)人物的情感變化。一個(gè)動(dòng)作,或者一系列動(dòng)作的組合,可以比直言我思、直抒我意更加具有力量。更重要的是,詩(shī)人呈現(xiàn)他的世界,任由讀者感受,往往也能夠給予讀者更廣闊更深入的想象空間。我們以雷平陽(yáng)的作品《殺狗的過(guò)程》為例:
這應(yīng)該是殺狗的
惟一方式。今天早上10點(diǎn)25分
在金鼎山農(nóng)貿(mào)市場(chǎng)3單元
靠南的最后一個(gè)鋪面前的空地上
一條狗依偎在主人的腳邊,它抬著頭
望著繁忙的交易區(qū),偶爾,伸出
長(zhǎng)長(zhǎng)的舌頭,舔一下主人的褲管
主人也用手撫摸著它的頭
仿佛在為遠(yuǎn)行的孩子理順衣領(lǐng)
可是,這溫暖的場(chǎng)景并沒(méi)有持續(xù)多久
主人將它的頭攬進(jìn)懷里
一張長(zhǎng)長(zhǎng)的刀葉就送進(jìn)了
它的脖子。它叫著,脖子上
像系上了一條紅領(lǐng)巾,迅速地
竄到了店鋪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來(lái)
繼續(xù)依偎在主人的腳邊,身體
有些抖。主人又摸了摸它的頭
仿佛為受傷的孩子,清洗疤痕
但是,這也是一瞬而逝的溫情
主人的刀,再一次戳進(jìn)了它的脖子
力道和位置,與前次毫無(wú)區(qū)別
它叫著,脖子上像插上了
一桿紅顏色的小旗子,力不從心地
竄到了店鋪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他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來(lái)
——如此重復(fù)了5次,它才死在
爬向主人的路上。它的血跡
讓它體味到了消亡的魔力
11點(diǎn)20分,主人開(kāi)始叫賣(mài)
因?yàn)榈却S多圍觀的人
還在談?wù)撝淮伪纫淮螠p少
的抖,和它那痙攣的脊背
說(shuō)它像一個(gè)回家奔喪的游子
在這首短詩(shī)中,詩(shī)人通篇以陳述語(yǔ)句,將“我”及“我”的情感全部隱藏起來(lái),并不直接抒發(fā)其內(nèi)心情感流動(dòng),而是用“攬”、“送進(jìn)去”、“竄”、“招手”、“爬回”、“依偎”、“戳”、“叫賣(mài)”、“痙攣”等等一系列的動(dòng)作詞語(yǔ),以一種旁觀者的視角,將他所看到的反復(fù)多次的“殺狗過(guò)程”以轉(zhuǎn)述給讀者。在《殺狗的過(guò)程》中,雷平陽(yáng)將敘事、戲劇性、零度情感、口語(yǔ)化融為一體,以一種反抒情的方式抒發(fā)了他心中巨大的情感波動(dòng)——一面是狗對(duì)于主人一次次的信任與依賴,一面是一次次冷酷的對(duì)狗的欺騙與殺戮;如此反復(fù)五次,詩(shī)人內(nèi)心的憤怒與悲涼如火山般洶涌澎湃,然而,最為澎湃的情感,詩(shī)人卻選擇隱藏,他寫(xiě)下平靜如鏡的水面,而其中的洶涌暗流任由讀者去感受去體悟。由此,詩(shī)歌生成了多重張力,比起直抒憤怒更令人動(dòng)容。
從“反”的美學(xué)意蘊(yùn)及其功能屬性出發(fā),我們看到反抒情有著強(qiáng)大的藝術(shù)沖擊力。順著詩(shī)人在抒情與反抒情之間循環(huán)往復(fù)的抉擇以及兩者無(wú)法割裂的復(fù)雜關(guān)系,我們甚至可以梳理出當(dāng)代詩(shī)歌發(fā)展的大致脈絡(luò)。無(wú)論是作為理念的的反抒情,還是作為方法的反抒情,作為一個(gè)關(guān)鍵詞它都有著舉足輕重的意義。在當(dāng)代詩(shī)歌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中,它理應(yīng)得到更多的關(guān)注。
注 釋
1.【五代】徐鉉《肖庶子詩(shī)序》,見(jiàn)胡經(jīng)之主編;《中國(guó)古典美學(xué)叢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頁(yè)。
2.【元】劉祁《歸潛志》卷十三,見(jiàn)胡經(jīng)之主編;《中國(guó)古典美學(xué)叢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354頁(yè)。
3.陳世驤:《中國(guó)的抒情傳統(tǒng)》,《陳世驤文存》,沈陽(yáng):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yè)。
4.周作人:《揚(yáng)鞭集序》,《談龍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頁(yè)。
5.事實(shí)上,“抒情”這一個(gè)概念的范疇也在不斷變化,它的指向由最初的“直抒胸臆”開(kāi)始不斷在往外延伸。比如,王德威提出“抒情現(xiàn)代性”,將“抒情”從一個(gè)文學(xué)范疇延伸至一種可以無(wú)限放大的超級(jí)能指。“抒情的定義可以從一個(gè)文類開(kāi)始,作為我們看待詩(shī)歌,尤其是西方定義下的,以發(fā)揮個(gè)人主體情性是尚的詩(shī)歌這種文類的特別指稱,但是它可以推而廣之,成為一種言談?wù)撌龅姆绞剑灰环N審美愿景的呈現(xiàn);一種日常生活方式的實(shí)踐;乃至于最重要也最具有爭(zhēng)議性的,一種政治想象或政治對(duì)話的可能。”王德威:《抒情傳統(tǒng)與中國(guó)現(xiàn)代性》,北京:生活·讀書(shū)·新知三聯(lián)書(shū)店,2010年版,第72頁(yè)。
6.戴望舒:《詩(shī)論零扎》,《戴望舒詩(shī)集》,廈門(mén):鷺江出版社,2009年,第84頁(yè)。
7.于堅(jiān):《拒絕隱喻》,《于堅(jiān)詩(shī)學(xué)隨筆》,西安:陜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3頁(yè)。
8.張松建:《抒情之外:論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論中的“反抒情主義”》,《文學(xué)評(píng)論》,2010年第1期。
9.羅振亞:《20世紀(jì)中國(guó)先鋒詩(shī)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頁(yè)。
10.侯馬:《抒情導(dǎo)致一首詩(shī)的失敗》,《詩(shī)探索》,1998年第3期。
11.《當(dāng)代詩(shī)歌:抒情,還是反抒情?》,《詩(shī)潮》,2001年第5期。專輯內(nèi)這五篇文章選自《中外詩(shī)歌研究》2001年第1、2期。
12.梁實(shí)秋:《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之浪漫的趨勢(shì)》,轉(zhuǎn)引自張松建:《抒情之外:論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論中的“反抒情主義”》,《文學(xué)評(píng)論》,2010年第1期。
13.宗白華:《詩(shī)閑談》,轉(zhuǎn)引自張松建:《抒情之外:論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論中的“反抒情主義”》,《文學(xué)評(píng)論》,2010年第1期。
14.陳世驤:《中國(guó)的抒情傳統(tǒng)》,《陳世驤文存》,沈陽(yáng):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頁(yè)。
15.【法】羅蘭·巴爾特:《寫(xiě)作的零度》,李幼蒸譯,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頁(yè)。
- 星星·詩(shī)歌理論的其它文章
- 她
- 外婆和兩個(gè)姨媽
- 悲傷太奢侈了
- 那些生命中不動(dòng)聲色的震顫
- 愛(ài)與痛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