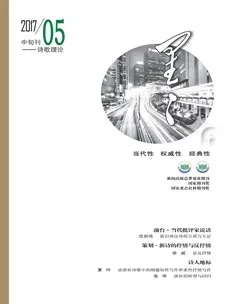唐祈的轉型與回歸
詩人唐祈,生于1920年。他的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936年至1949年,是他詩歌創作的第一個階段,從實踐到成熟,最終以“中國新詩派”或者“九葉派”的命名方式,寫入文學史。1950年至1960年,出于歷史的原因和個人抒情的需要,唐祈逐漸走出了現代主義的詩歌寫作方式。1981年至1989年,是唐祈寫作的最后10年,這個時期的唐祈是孤獨的,他的詩歌探索,既不屬于九葉派現代主義詩歌的延續,也無法融入新興的詩歌風潮——偏居蘭州,遙望草原與戈壁,他以最樸素最簡單的方式,完成了一生最后的抒情。
時間與旗
唐祈最初的創作,以感性見長。他是這樣評價自己早期的詩作的,“這些早年詩中,我比較注重抒情、色彩和情調。我溶浸于無拘無束的生活里,我用畫家的眼睛觀看草原風景,體味一種單純柔和的美,尋找清麗新鮮的牧歌風格,即使是令人悲傷的歌。”[1]這首《游牧人》,很能代表他前期抒情詩的特色:“游牧人愛草原,愛陽光,愛水,/帳幕里你有先知一樣遨游的智慧,/原始的笛孔里熱情是流不盡的乳汁,/月光下你比牝羊更愛溫柔地睡。”[2]
后來,唐祈以“中國新詩派”的身份走進中國文學史,主要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早期清麗柔美的抒情,需要尋求一種表達的力,意象、意境的色彩與情調,在潛意識地尋求一種更加厚重的質地。意識到這個問題,他便主動地對自己的詩歌思維進行更新,從感性的抒情走向知性的凝視。“在大學的幾年和離開學校以后,我閱讀了許多關于思考人類社會和探索人生命運的書,哲學、歷史、宗教、文學 (尤其西方現代哲學和文藝思潮之類)……使我對人生產生了從未有過的困惑、迷惘,和對于真理的探求”[3],這種思想的探索,改變了詩歌的寫作方式,“我不像早年詩里那樣只注重抒情,我認識到了人生現實的復雜和深邃,我應該尋找各種新的視角、許多不同的途徑來寫;我擺脫了現實主義的反映論,和對生活現象簡單的摹寫,把象征和現實揉合在一起,打破通常的時空觀念,注重詩的藝術邏輯和藝術時空,運用思想知覺化,通過感覺來表現內心經驗”[4]。可以看出,從早期清麗新鮮的牧歌風格,走向現代主義的詩藝探索,是唐祈個人的自覺。另一方面,這種現代主義的轉化,得益于志趣相投的詩友們的聲援與切磋,具體而言,就是“中國新詩派”(新時期以來,因為《九葉集》的出版,始用九葉派命名)的內部交流。1948年,唐祈與杭約赫、陳敬容、唐湜等編《中國新詩》叢刊,對于唐祈個人而言,除了和中國新詩派的主要成員進行詩藝探討之外,他還主動地對中國現代主義詩歌的發展,形成了個人的理解,對戴望舒、艾青與馮至等人的現代主義詩歌實踐,做出了梳理與評估。同時,潛心研究里爾克、艾略特等人的詩歌創作,把他們的詩歌理念,進行了個人化的理解與吸收。這在《唐祈詩選·后記》)中,都有明確的敘述。這個時期的代表作有《夜歌》《嚴肅的時辰》《時間與旗》《老妓女》《女犯監獄》等等。
所以說,唐祈“中國新詩派”的文學史身份,既是對他個人參與現代文學思潮的認定,更是對他經過漫長探索、逐漸成型的詩歌旨趣的總結。這種認定與總結,成為詩人唐祈的歷史標簽,而這時期他的《時間與旗》,也是“中國新詩派”的代表作。
“中國新詩派”成員唐湜認為,《時間與旗》“直接受到了艾略特的長詩的影響,也可以說,是在艾略特的‘時間’的哲理框子里填上了當時上海的現實生活與斗爭的各個層面,只是貼得過于近,在瀟灑的抒情氣氛中嵌入了些戰爭的火藥氣,顯得有些生硬”[5]。客觀地講,唐湜的評價,顯得過于苛刻,因為他的評價是在辯解的語境中產生的——當時七月派詩人阿垅認為唐祈涉嫌抄襲艾略特的《燃燒了的諾頓》。現在,我們綜合唐湜和阿垅的看法,正好可以還原一個真實的中國現代主義詩人唐祈。阿垅的質疑,可以看出唐祈對艾略特的模仿,客觀地講,對艾略特、奧登、里爾克等西方現代主義詩人的模仿,在“中國新詩派”的詩人中普遍存在,不限于唐祈。而之所以不是抄襲,是因為他們把發源于西方哲學的現代經驗,轉化為個性化思考的中國經驗。對于《時間與旗》而言,便是在艾略特式的時間哲學框架內,“嵌入上海的現實生活與斗爭”。唐湜認為這種“嵌入”過于生硬,而同為九葉派成員的袁可嘉1980年為《九葉集》作序時,突出強調的正是這一點——在袁可嘉看來,現實主義精神,正是九葉派的現代主義與西方現代主義的區別[6]。
在《時間與旗》中,現實時間不是被“嵌入”的,而是與哲學的時間形成復調與對照,這種復調與對照,正是《時間與旗》的內部結構。在詩歌中,時間分為兩種形態:
第一,現實時間的情景化表達:在詩歌中,我總是走向“上海市中心的高岡”[7],在這個虛構的地方,看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光陰”、看見“資產階級的空虛的光陰”、看見“資本家和機器占有的地方”……時間的空間性轉化,濃縮了中國的現實,這是詩歌的主體內容。
第二,客觀時間被哲學化表達:“時間,回應著那聲鐘的遺忘,/過去的時間留在這里,這里/不完全是過去,現在也在內膨脹/又常是將來,包容了一切/無論歡樂與分裂,陰謀與求援/可卑的政權,無數個良心卻正在受它的宣判。”這種公正的、永恒的時間屬性,對僵死的、腐朽的社會時間,形成對照與審判。
在兩種時間之間,是忍耐苦難的人,是逐漸自覺的人,是走向斗爭的人——他們是火:“村莊圍繞著地主的縣和鄉,縣城孤立了/一個個都市,迄至資本社會最后的上海高岡。/每次黑夜會看見火焰,延續到/明日紅銅色的太陽。”在斗爭中,時間被“完成”,確切地講,被重新定義。定義它的,是“人民的旗”。于是,黑暗的苦難的現實時間被改造,客觀存在的哲學性的時間,轉化為理想的時間:“過去的時間留在這里,這里/不完全是過去,現在也在內膨脹/又常是將來;包容了一致的/方向,一個巨大的歷史形象完成于這面光輝的/人民底旗,炫耀的太陽光那樣閃熠/映照在我們空間前前后后/從這里到那里。”
《時間與旗》的出現,意味著詩人唐祈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主義詩人。他打破了現實主義詩歌摹寫時間的自然秩序,形成了文本內在的藝術邏輯,他用一種智性的充滿張力的語言控制情感運行,用冷峻的意象、反常規的語法、跳躍性的節奏,擾亂讀者的常規思維,引導讀者走向更有力更深刻的思想空間。
短 笛
相對與1949年前,在建國初的四五年里,唐祈發表的詩歌不多。1958年 4月,唐祈到北大荒密山農場、清河農場勞教,期間的創作了組詩《北大荒短笛》。其中的《短笛》,通過“我”講述了一個青年畫家的在“監牢”中的藝術人生:用七個夜晚,把廢棄的草鐮,磨成刻刀;把刨地揀來的樹根,刻成躍動的麋鹿和飛鳥的木雕;用一個老犯人臨死用過的竹棍,削成了一支短笛……“我的這些雕像、竹笛和刻刀/即使犯了天條,我一件也不上交”[8]。這個故事,成為唐祈的“自畫像”,對于他,詩歌的意義,正如同“監牢”中青年畫家的刻刀或者短笛——它們制造飛翔和歌聲,孕育美和自由。《北大荒短笛》中還有《黎明》《心靈的歌曲》《土地》《水鳥》《愛情》《曠野》《小湖崗的雨夜》《永不消歇的歌》《墳場》等9首詩歌,不管是即景生情還是托物言志,不管是抒發理想還是向遠方的“你”傳達情思,都和《短笛》具有同樣的主題,都以囚禁的肉身,傳達愛與美、自由與革命的信念。在中國新詩史上,唐祈的《北大荒短笛》,不該被遺忘,他展現了獲得個體意識與革命思想的現代詩人,在歷史的苦難與困境中,堅守的理想主義的信念:“我和同伴們白
雪上的腳印,/每個時辰都在證明,/這一群荒原上無罪的人,/頭顱里燃燒著信念和理想,/周身都是熾熱的火焰,/嚴冬的冰雪無法把它凍僵,/風的刀劍也不能把它砍光。”[9]《北大荒短笛》是唐祈在他人生中第二個創作階段的代表作,我們以此走近唐祈,不僅僅是為了凸顯詩歌的歷史內容以及詩人的精神姿態,更是為了審視唐祈的詩歌轉型。《北大荒的短笛》,意味著現代主義詩人唐祈,在具體的歷史境遇下,走向浪漫主義抒情,這種浪漫主義,不是感傷的個人情緒的抒發,而是強大的個體精神與革命理想主義的結合。《北大荒的短笛》的作者,仿佛不是“中國新詩派”的詩人,而更像一個“七月派”詩人,個體意識、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精神的融合,成就了詩歌的崇高美。
關于這種轉型,我們很容易從歷史現實、政治環境的層面尋求原因,當然,這種原因不可忽略。但是我覺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唐祈意識到了自己的詩歌危機。對于唐祈而言,“中國新詩派”的現代主義詩歌實踐,是他前期詩歌旨趣的綜合與定型,使他擁有了清晰的詩歌理念,但是,這種成型的詩歌理念與詩歌技法,卻成為他繼續寫作的障礙——對于熱愛詩歌的人而言,內在理念與寫作技法的定型,比外在的社會壓力更可怕。因為,它讓詩歌寫作失去了引發情思的驅動機制、它讓詩歌寫作失去了安排情思的藝術秩序。在《詩歌回憶片斷》中,唐祈追憶了自己編輯《中國新詩》時的感受:“這個階段,創作熱情很高,寫得也比較多。我更多地學習和運用西方現代主義的表現方法,受到里爾克、艾略特較深的影響。但感受最深的已不是作品的得失,卻是愈來愈深的發表之前的恐懼感,不是害怕特務的追捕和搜査,而是由衷地害怕讀者對我的詩作感到枯燥乏味。覺得讀者花費了時間讀一首詩,總應該得到一點新東西,一點思想上的收獲或者是藝術享受,結果作者給予的卻是一塊硬蠟或者是一坨棉花,那為什么要白白浪費讀者寶貴的時間去咀嚼它們呢?”[10]這段追憶表明,在1949年之前,在“中國新詩派”的詩歌理念還沒有受到主流意識形態壓制的時候,唐祈已經對自己業已定型詩歌理念產生了懷疑。
編輯《中國新詩》時的感受,影響了建國初期唐祈的詩歌創作。1951年2月,唐祈到《人民文學》編輯部工作,從1951年到1956年,沒有發表作品。在唐祈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看出,其中原因和政治無關,而和他對自己以及“中國新詩派”同仁的詩歌理念的質疑相關。他對現代主義附加在詩歌之上的思想密度、技法迷障感到厭倦,他希望獲得一種更加明朗新鮮的表達方式,1950年代的現實遭際成全了他。
1958年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對唐祈個人而言,是冤屈與苦難,對唐祈的詩歌創作而言,卻成為契機與動力——在與苦難的肉搏中,詩人唐祈失去了1940年代進行現代主義詩歌寫作的“距離”——貼身的苦難打破了審美的哲學性的沉思,技法的迷戀讓位于抒情的需要。在此情況下,唐祈選擇了一種更加熟悉的寫作方式,這種寫作方式是中國古代憂憤抒情的傳統,是屈原、杜甫的傳統,也是中國現代個體意識與革命信念融合的理想主義傳統——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北大荒短笛》的作者,逐漸離開了“中國新詩派”,而與他們曾近的論爭對手——七月派走向共鳴。
牧 歌
唐祈生于江西南昌。父親唐宜南,1931年調到甘肅郵務局工作,1938年,舉家遷至蘭州。自此,蘭州成為唐祈的第二故鄉,或者說,成為他真正的故鄉。剛到一年,唐祈便寫下《蒙海》《游牧人》《拉伯底》《回教徒》《穆罕穆德》《倉央嘉措的比喻(四)》《倉央嘉措的情歌(九)》《倉央嘉措的死亡(十四)》《故事》等詩歌,都是與西北相關的觀感與遐想。從這些詩歌可以看出,西北的風物、宗教與民俗等,對唐祈影響很大。在這些詩歌中,現實的苦難、宗教的思考、民族的記憶等,全部銘刻在西北地域高遠而蒼涼的底色上,唐祈用憂傷而節制的抒情筆調,點亮了它們。
“蒙海”是唐祈在甘肅興隆山遇見的蒙古婦人,她和幾十個蒙族人在山上守成吉思汗的靈柩,抗戰時期,他們把成吉思汗的棺槨、盔甲、長矛等遺物,從內蒙遷放到興隆山。唐祈通過描述“蒙海”這個女性形象,把一個民族的歷史變遷、現實苦難,凝聚在悠長、柔美而蒼涼的歌聲里:“蒙海,一個蒙古女人,/三十歲了,還像少女一樣年輕,/她說一串難懂的言語,/告訴我來自遙遠的沙布尼林。//她穿著舊日的馬靴和羊皮衣,/頭套上的珠子夸著衰落貴族的富麗,/她唱一支牧羊女的謠曲,/說是成吉思汗的后裔。”[11]
1978年,唐祈再次回到蘭州。先是在甘肅師范大學(現西北師范大學)工作,1981年到西北民族學院(現西北民族大學)工作,直到1990年逝世。西北高原點亮了唐祈的青春期創作,而他在經過生活的輾轉、歷史的苦難之后,最后依然選擇扎根西北,用西北的風物與歌聲,喂養自己的詩神。
對于唐祈而言,西北是他精神療傷的地方,也是他的生命再次飛翔的地方。這種飛翔,和自由相關,和信仰相關,和青春相關——最貧瘠的地方,以最高遠的姿態,闡釋著這些神秘的名詞。 唐祈這樣講述他生命中的西北:“西北高原,那是個賦予人以想象力的地方,草原上珍珠般滾動的馬群、羊群,黑色的戈壁風暴,金光刺眼的大沙漠,沙漠深處金碧輝煌的廟宇,尤其是在草原的帳幕中,我從來沒有度過那樣美好的夜晚,也從來沒有歌唱和笑得那樣歡暢過。從蒙族、藏族婦女的歌聲中,我感到一種粗獷的充滿青春的力量,正是這種青春力量,強化了我年輕時的歡樂和哀愁,賦予了我為追獵自己理想從不知退卻的膽量,使我在相隔若干年以后,仍然要在西北十四行詩里抒唱它們。”[12]
縱觀唐祈的晚期創作,主要表現為兩種類型,一是現代主義詩風的余蓄,二是西北地域、尤其是少數民族風情的牧歌式吟唱。后者的意義,遠遠大于前者。從唐祈最后10年的詩歌中可以看出,“中國新詩派”的現代主義,對他而言僅僅成為一種微觀的詞句修辭,而不是一種整體的詩歌觀念,甚至不是一種詩歌風格。而對西北的牧歌式吟唱,卻成為他恢復“青春力量”的生命途徑。他聽到一個維吾爾族青年的冬不拉彈唱,于是寫到:“漸漸地消失了十年的憂傷/歡樂的血液重新在周身流蕩/你無形的手指按撫在我心上/打開了我收摺的翅膀”[13];他讓葡萄開口自白:“我愛滋潤沙漠旅行者的饑渴/我愛把濃酒變成人間的歡樂/我愛獻給人類珍寶的收獲”[14];他從獵手的身上,看到不老的青春:“他的棕褐色面孔像巖石刻成,/深深的皺紋里隱藏著青春,粗獷的力,/在閉鎖的渾身肌肉中隆起”[15]……
西北高原喚起了他對自由、信仰、青春的神往,這一切不是通過現代主義的知性的方式去展現,不是通過晦澀的象征、繁復的技巧去展現……這一切對于此時的唐祈而言,已經成為多余。就像西北高原刪除了多余的過渡與渲染,用草原和戈壁的方式解釋天空的神秘,唐祈最后選擇了最元初的最樸素的抒情方式,詮釋自己剩下的生命。唐祈從“中國新詩派”抽象抒情的詩歌觀念中走出來,從“九葉派”的沉重晦暗的政治記憶中走出來,從漢文化溫文爾雅的禮義規訓中走出來,走向“草原”——自由與愛情:
在草原的月光下
我站在翠綠的夜里了
銀鈴一樣熟悉的
蒙古少女的牧歌
從我心靈的曠野流淌
像一片溫柔的風的手掌
撫摸在滴落露水的草葉上
沙山那邊:薩仁高娃呵
小小的褐色的篷帳里
藏著我青春的幻想
鮮嫩紅潤的面龐
一束烈火似的目光
我從你的瞳仁里
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今夜,我用滾燙的愛情
把自己灌得醉意酩酊
我的靈魂
像馬頭琴的弦子
被看不見的手指撥響
愿我們同在一支彩色的歌里
如同云和霞光融合在一起
愿你是風,我奔向你
感動著震顫如風中的馬尾
呵,呵,唯有你知道這支歌
聽者是誰[16]
從西北高原尋求精神資源,在1980年代的中國詩歌中并不罕見。楊煉、海子、昌耀等詩人,都有代表性的作品。尤其是昌耀,像一只流放日久的禿鷹,呼號騰躍于高原雪峰,孤獨執拗地表達著觸及天空的終極性天問。但是他們的詩歌,從本質上講,都是1940年代“中國新詩派”詩歌觀念的延續,西北對于他們,成為新時期以來逃避政治中心、逃避文化中心的“陌生化”高地,成為他們建構某種哲學性思考的象征性符號。這種詩歌寫作方式,卻正是唐祈復出之后,企圖告別的東西。
在1940年代,西北對于唐祈,是一種沒有充分展開的生命訴求,是被現代主義的抽象思維所遮蔽、所壓抑的青春期想象,現代主義的遠距離審視與哲學化表達,凝固了青年唐祈的青春期抒情。1950年代到1980年代,漫長的政治苦難與生活磨難,延續了這種遮蔽與壓抑,他必須以理想主義的意識形態抒情,對抗現實性的意識形態禁錮,而把自我的青春緬想,擱置一旁。到了1980年代,對于恢復自由之身的唐祈而言,補償自己的青春抒情,顯然比延續現代主義的詩歌實驗更加緊迫,因為這是生命治愈的需要,也是藝術調整的需要。他卸下思想附加在詩歌上的累累重荷,他拋棄技巧附加在抒情上的重重遮障,回歸到1938年、1939年未竟的青春期抒情。對他而言,這是生命意義上的重回故鄉,也是詩歌意義上的回到原初。
1980年代中期之后,模式化的現代主義的詩歌技法逐漸受到有些詩人的反對,密集的意象、晦澀的象征所造成的詩歌負累,讓更年輕的詩人感到厭倦,“第三代”詩歌應運而生。其實,第三代詩人對朦朧詩的革命,在唐祈淡出“九葉派”的藝術實踐中早就發生了。所不同者,第三代詩人是為了建構一種新的詩歌理念,而對唐祈而言,這些都是身外之物——他只愿在自己的晚年,煥然年輕,遙望草原與戈壁……詩歌于他而言,僅僅是歌唱而已,歌唱遲到的自由、歌唱遲到的愛情。
注 釋
1.唐祈:《唐祈詩選·后記》,《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頁。
2.唐祈:《游牧人》,《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頁。
3.唐祈:《唐祈詩選·后記》,《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頁。
4.同上,182頁。
5.唐湜:《九葉在閃光》,《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4期,第149頁。
6.袁可嘉:《九葉集·序》,《九葉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2頁。
7.唐祈:《時間與旗》,《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0頁。
8.唐祈:《短笛》,《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2頁。
9.唐祈:《永不消歇的歌》,《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頁。
10.唐祈:《詩歌回憶片斷》,《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頁。
11.唐祈:《蒙海》,《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5頁。
12.唐祈:《唐祈詩選·后記》,《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頁。
13.唐祈:《冬不拉的歌》,《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頁。
14.唐祈:《葡萄》,《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39頁。
15.唐祈:《獵手》,《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頁。
16.唐祈:《給薩仁高娃的抒情詩》,《唐祈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頁。